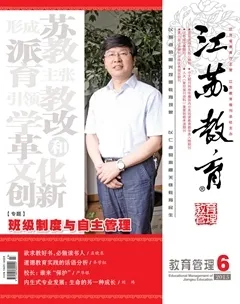子張:將孔子教誨“書諸紳”的弟子

【摘 要】子張是孔門私學(xué)中將孔子教誨“書諸紳”的弟子。孔子對(duì)子張的教育體現(xiàn)了高超精湛的教育藝術(shù):一是孔門問對(duì)——孔子對(duì)子張的個(gè)別化教學(xué)藝術(shù);二是相師之道——孔子對(duì)子張的身教藝術(shù)。此外,子張與同門“相觀而善”的真實(shí)關(guān)系,也值得重新審視其所具有的教育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子張;孔子;教學(xué)藝術(shù);問對(duì);身教;相觀而善
【中圖分類號(hào)】G52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6009(2015)23-0040-05
【作者簡介】李如密,南京師范大學(xué)課程與教學(xué)研究所(江蘇南京,210097)教授,教育學(xué)博士,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教學(xué)論、教學(xué)藝術(shù)論的研究。
子張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他年輕志高、容儀堂堂。孔子對(duì)這位弟子,既有循循善誘的“言教”,又有細(xì)致入微的“身教”,在其成長道路上不斷地以各種方式為之指點(diǎn)迷津。子張對(duì)孔子的教誨非常重視,甚至將之寫到衣帶上以日夜提醒、對(duì)照修行。子張氣象宏大、交友廣泛,但性情偏激、堅(jiān)持己見,同門對(duì)其褒貶不一。我們?cè)诮裉旒?xì)致分析孔子對(duì)子張的教學(xué)藝術(shù),客觀還原子張與同門的真實(shí)關(guān)系,對(duì)于教師思考現(xiàn)實(shí)的教育教學(xué)問題仍然不乏有益的啟示。
一、子張的生活史、形象及成就
子張為春秋末年陳國(即今河南省淮陽)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也有說他是魯國人的。
子張出身微賤。《呂氏春秋·尊師》載:“子張,魯之鄙家也。”這里的“鄙”即小,“鄙家”即小戶人家,地位相當(dāng)?shù)臀ⅰ?zhàn)國《尸子》卷上載:“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駔”指馬市上的經(jīng)紀(j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