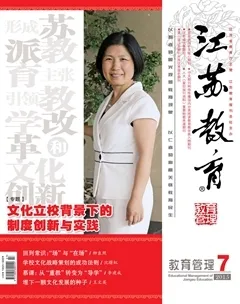用最柔軟的方式表達(dá)教育
【摘 要】教育應(yīng)該是濕的,是平的,是活的,是細(xì)心的、溫柔的,需要培養(yǎng)一份情感——一份學(xué)生、家長對學(xué)校持續(xù)的情感,要用最柔軟的方式來表達(dá)教育。基于信任的,而非懷疑的;基于理解的,而非誤解的;基于對話的,而非獨(dú)白的;基于民主的,而非粗暴的;基于發(fā)展的,而非不變的;基于開放的,而非封閉的。教育是從溫暖人心開始的。對一所學(xué)校而言,教師是溫暖的守護(hù),學(xué)校是溫暖的田園,校長是溫暖的符號,教育是溫暖的期待。
【關(guān)鍵詞】柔軟;理解;信任;民主
【中圖分類號】G471.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27-0077-04
【作者簡介】李建華,南京市蓮花實(shí)驗(yàn)學(xué)校(江蘇南京,210041)校長。
“教育的理想國在哪里,學(xué)校的存在感在哪里,校長的價(jià)值觀在哪里”,這是我對教育的追問;“做有故事的教育,辦有溫度的學(xué)校”,“給每一個(gè)孩子一張溫暖的書桌”,“讓每一個(gè)孩子看得見分?jǐn)?shù),想得起童年,記得起恩師,憶得起母校。在校時(shí),留下的是熱愛;離校后,留下的是眷念”,這是我對教育“真善美”的追求。教育應(yīng)該是濕的,是平的,是活的,是細(xì)心的、溫柔的,需要培養(yǎng)一份情感——一份學(xué)生、家長對學(xué)校持續(xù)的情感,要用最柔軟的方式來表達(dá)教育。基于信任的,而非懷疑的;基于理解的,而非誤解的;基于對話的,而非獨(dú)白的;基于民主的,而非粗暴的;基于發(fā)展的,而非不變的;基于開放的,而非封閉的。我以為,教育是從溫暖人心開始的。對一所學(xué)校而言,教師是溫暖的守護(hù),學(xué)校是溫暖的田園,校長是溫暖的符號,教育是溫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