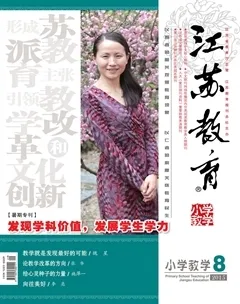給心靈種子的力量
2015-04-12 00:00:00施萍一
江蘇教育
2015年15期
【摘要】“小橘燈”故事課程,以正式課程與活動課程相結合,致力于給師生創造全新的課程空間,為課程創設活潑生動的故事情境。師生充分發揮主體性,共同開發課程,逐步推進課程的創生和實施。
【關鍵詞】故事元素;課程開發;課程事件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29-0016-03
【作者簡介】施萍一,江蘇省無錫市隆亭實驗小學(江蘇無錫,214101),高級教師,無錫市語文教學能手。
四年前我參加無錫市青年教師優質課評比,執教孫友田的《月光啟蒙》,那是一堂給予我寶貴教學啟蒙的課。給予孫友田文學啟蒙的,卻是不識字的母親在他幼年時吟的歌謠、講的故事、猜的謎語。更重要的是他白天礦上工作,晚上燈下寫詩,母親的啟蒙為他植下積極生活的精神良種。驀地一個念頭:語文故事多,讓語文教學成為故事課程,讓兒童與教師在課程光輝中經歷體驗,共同建構,獲得語文思想和精神的啟蒙與孕育。這抹課程光輝,我和老師們喜歡稱之為“小橘燈”故事課程。
“小橘燈”故事課程,以正式課程與活動課程相結合,積極創設活潑生動的故事情境,充分發揮教師、學生、環境等因素持續交互的動態作用,致力于給師生創造全新的課程空間,是學生自主學習、師生交互作用不斷生成建構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關鍵事件,逐步推進課程的開發、創生、實施。四年來,“小橘燈”溫暖明潔的燈光,照亮我和老師們的語文課程之路。
一、“故事元素”在兒童心田“串串生”
蘇教版小語教材中,有大量故事文體課文,童話、神話、寓言、民間故事,在各冊教材中占據一定比例和地位,其他文體如詩歌、散文,敘述方式也大多體現兒童喜聞樂見的故事性。……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