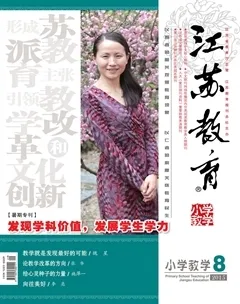向往美好
2015-04-12 00:00:00李亮
江蘇教育
2015年15期
【摘要】帶領學生走向美好是語文課程永恒的價值追求,它指向語文學科能力的發(fā)展:對漢字及母語的熱愛,對生活整體性的領悟能力,對語言文字直覺的感受力以及開掘語言文字資源的能力,如此才能更好地發(fā)揮語文的學科價值。語文教學需要引導學生發(fā)現并體驗母語的文化與精神,形成正確的思想方法、學科能力及重要的價值觀,設計有效的教與學的活動,提升教學的過程價值,如此方能落實自身的學科價值。當下的語文教學可沿此方向探尋改革的路徑。
【關鍵詞】美好;語文;學科價值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29-0071-03
【作者簡介】李亮,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南京,210013),江蘇省中小學教研室小學語文教研員,教育學博士。
《江蘇教育》(小學教學版)邀我就本次江蘇省“杏壇杯”蘇派青年教師課堂展評活動的主題“發(fā)現學科價值,發(fā)展學生學力”,談些對語文學科價值和學生學力發(fā)展的看法,我沒有參與學習此次活動,恐沒什么發(fā)言權,但深感這一命題確是切中了語文教學的要害,且與近來一些零星的思考頗有些關聯,所以寫些想法,與各位老師探討。
認識語文的學科價值需要融合“變”與“不變”兩種視角。學科價值總是當下時代的價值,它隨著學科邊界的變化與發(fā)展、學科社會責任的或簡化或豐富、教育對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的目的變遷而變化。但作為傳承民族文化精神的語文學科來說,變化之中又總有永恒性的傳承。找到這種永恒價值的當代體現,才能使學科價值的理解更貼近歷史與現實。……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