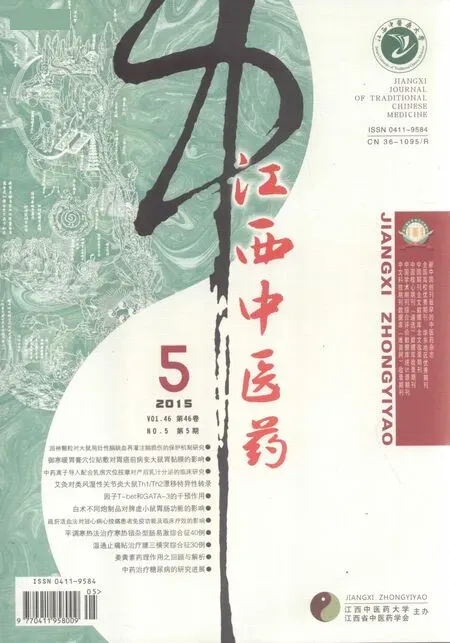吳鞠通“意療”心法摭拾
★ 吳劍浩 熊為國 (1.南昌市第六醫院 南昌330000;2.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內科 南昌330000)
“意療”,又稱為“心療”,也就是中醫的心理療法,是指不用藥物、針灸、手術等“有形”的治療手段,而借助于語言、行為以及特意安排的場景等來影響患者的心理活動,喚起患者防治疾病的積極因素,促進或調整機體的功能活動,從而達到治療或康復作用的方法[1]。
吳鞠通,名瑭(1758—1836年),江蘇淮陰人,是清代著名醫學家,創立溫病三焦辨證理論體系,被后世譽為溫病四大家之一。然今人唯在其溫病學理論上闡述頗多,而在其運用意療方面探索甚少。其實吳氏不僅精通溫病,同時又是善于運用意療治療沉疴痼疾的大師。在《吳鞠通醫案》中,記載了吳氏藥療和意療相結合的諸多驗案,療效卓著,頗具特色。筆者不揣固陋,擇選《吳鞠通醫案》中的典型案例作簡要探討,俾后學得窺其意療思想之一斑。
1 勸說開導,承于《內經》
勸說開導是針對患者的病情及其心理狀態﹑情感障礙等,采取語言交談的方式進行疏導,以消除其致病心因,糾正其不良情緒和情感活動等的一種意療方法。《靈樞·師傳》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吳氏很好的繼承了《內經》的意療思想,并且在臨床實踐中運用嫻熟。
郭氏案:先是郭氏喪夫于二百里外其祖墓之側,郭氏攜子奔喪,饑不欲食,寒不欲衣,悲痛太過,葬后廬墓百日,席地而臥,哭泣不休,食少衣薄,回家后致成單腹脹……余思無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必得開其愚蒙,使情志暢遂,方可冀見效于萬一。因問曰:“汝之痛心疾首十倍于常人者何故?”伊答曰:“夫死不可復生,所遺二子,恐難成立。”余曰:“汝何不明之甚也……汝子之父已死,汝子已失其萌,汝再死,汝子豈不更無所賴乎?汝之死,汝之病,不惟無益于夫,而反重害其子。害其子,不惟無益于子,而且大失夫心。汝此刻欲盡婦人之道,必體亡夫之心,盡教子之職,汝必不可死也。不可死,且不可病。不可病,必得開懷暢遂而后可愈。”伊聞余言,大笑。余曰:“笑則生矣。”伊云:“自此之后,吾不惟不哭,并不敢憂思,一味以喜樂從事,但求其得生以育吾兒而已。”余曰:“汝自欲生則生矣。”于是為之立開郁方,十數劑而收全功[2]。
按:郭氏喪夫,悲傷過度,加之饑寒交迫,而致單腹脹。吳氏察脈辨證,分析病情后,認為“必得開其愚蒙,使情志暢遂,方可冀見效于萬一。”于是用言語說理的方式,對患者進行勸說開導。設身處地的分析了郭氏所處的境遇,巧妙地將患者的痛苦,轉變為戰勝疾病,恢復健康的動力,變消極心理為積極心理,使患者心悅誠服,增強了抗病的信心,從此“不惟不哭,并不敢憂思,一味以喜樂從事。”在有效運用意療的基礎上,配合開郁方,而收全功。正所謂“善醫著,必先醫其心,而后醫其身”。
《素問·湯液醪醴論》云:“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吳氏深得《內經》奧義,十分重視勸說開導在治療疾病過程中的作用。他曾深有體會地指出:“難治之人,難治之病,須憑三寸不爛之舌以治之。”“必細體變風變雅,曲察勞人思婦之隱情,婉言以開導之,莊言以振驚之,危言以悚懼之,必使之心悅情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吳氏的深刻見解和豐富的意療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發掘整理,并與今天的中醫通道共研。
2 移情易性勝于藥餌
移情易性,也就是轉移注意,是通過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或通過精神轉移,改變患者內心慮戀的指向性,從而排遣情思,改變心態,以治療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疾病的一種意療方法。歷代醫家皆十分重視移情易性的治療方法。《續名醫類案》云:“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遣性情不可”,“慮投其所好以移之,則病自愈”。葉天士更是在《臨證指南醫案》中明確指出“郁證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而吳鞠通運用移情易性之法,亦是得心應手。
陳氏案:酒客不戒于怒,致成噎食,其勢已成,非急急離家,玩游山水,開懷暢遂,斷不為功。蓋無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與進退黃連湯法[2]。
按:噎食,屬中醫“風、勞、鼓、膈”四大證之一。本病的形成,情志因素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此案患者嗜酒,且不戒惱怒,而成噎食之證。吳鞠通分析病情以情志障礙為主,認為“無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治療上采取心藥結合的療法,“急急離家,玩游山水,開懷暢遂”并配合黃連湯等藥物以取效。吳氏這種通過游山玩水來舒暢情志,祛邪除疾的方法,屬中醫移情易性的意療方法。清代吳師機在《理瀹駢文》中曾對這種意療方法作出了很好的詮釋:“七情之病也,看花解悶,聽曲消愁,有勝于服藥也。人無不在外治調攝中,持習焉不察耳。”在心身疾病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影響疾病的境遇或情感因素常成為患者心身機能的刺激灶,使心身機能日趨紊亂,而這種紊亂又強化著這類刺激作用,形成惡性循環使病癥遷延難愈。對此,可借助移情易性轉移注意的療法,有意識地轉移患者的注意中心,以消除或減弱它的劣性刺激作用。患者縱情于山水,丟掉了思想包袱,則病自向愈。由是觀之,“玩游山水”猶如一劑良方妙藥,它轉移人的情性,使心身得到調養。
3 行為療法根于文化
中醫把各種心理疾病和軀體癥狀看成是異常行為,認為可以通過中醫治療手段來調整和改造,以建立新的健康行為。中醫行為療法與現代行為療法有相似之處,同時又帶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吳氏對行為療法具有獨到的見解,堪稱運用行為療法之典范,后學若能隅反,必將受益匪淺。
章氏案:先是二月間病神識恍惚,誤服肉桂、熟地等補藥,因而大狂。余于三月間用極苦以折其上盛之威,間服芳香開心包,醫治三十日而愈。但脈仍洪數,余囑其戒酒肉……至午節大開酒肉,于是狂不可當,足臭遠聞至鄰,不時脫凈衣褲,上大街,一二男子不能搏之使回。……延至六月十六日午刻,復自撕碎其褲,人不及防,而出大門矣。……此癥非打之使極痛,令其自著褲不可。蓋羞惡之心,亦統于仁,能仁則不忍,忍則不仁,不仁之至,羞惡全喪。打之極痛,則不能忍,不忍而仁心復,仁心復,而羞惡之心亦復矣。……于是以小竹板責其腿,令著褲,彼知痛后而自著衣,著后稍明。次月十七日立秋,余與大劑苦藥一帖而全愈。蓋責打之功,與天時秋金之氣,藥之力,相須而成功也。后以專翕大生膏而收全功[2]。
按:此案吳鞠通成功運用于中醫行為療法中的責打法。責打法是指發病之時,用棍痛責,或掌其面與嘴,目的是“使之思痛而失欲也”,即以痛苦的刺激矯正變態行為。章姓患者病狂,吳氏用極苦寒之劑,愈而又發,“狂不可當,足臭運聞至鄰,不時脫凈衣褲子大街”。吳氏認為“羞惡之心,亦統于仁”,故必須使其“仁心復而羞惡之心亦復矣”。于是用小竹板責打其腿使極痛,患者知痛后自著衣,然后神志漸明。再配合大劑苦藥一劑而愈。吳氏從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出發,運用樸素辯證法,對患者施以適當的懲罰,把癥狀和不愉快的體驗結合起來,使患者產生強烈的躲避傾向及明顯的身體不適感覺,從而使病態行為得以矯正。這一生動的案例提示我們,要做好中醫的心理治療,不僅需要具備深厚的中醫功底,還要注意地域文化背景、倫理道德觀念的差異,對祖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入的了解。
4 結語
吳鞠通以擅長溫病而著稱于世,后世在研究吳氏學術思想時,多評論其溫病學方面的成就,而較少提及他對中醫心理學的貢獻。其實吳氏博通諸科,尤其善用意療療法。吳氏認為,在診治過程中,“凡治內傷者,必先祝由。詳告以病之所由來,使病人知之”。若不先告之病由,曉以利害,暢其情志,戒其酒色,調其飲食,則藥物很難奏功。所以然者,“無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因此,他常囑咐病人“調情志,切戒惱怒”,倘“不能寬懷消怒,不必服藥”。此外,在心理治療的具體運用中,吳鞠通善于意療與藥療相結合,故治療難治之人,難治之病,每見奇效。他曾深有感觸的說:“余一生得力于此不少。”可見,吳氏之所以臨證療效卓著,與其重視意療療法,采用綜合的整體治療是分不開的。
中醫學早在《內經》時代就建立了以古典哲學為基礎的類似“生物—心理—社會”的醫學模式。《素問·寶命全形論》云:“一曰治神,二曰知養生,三曰知毒藥為真。”把心理療法放在比藥物療法還要重要的位置,認為治心重于治疾,重視心理因素,社會因素,自然因素在致病中的作用。《醫方考》曰:“情志過極,非藥可愈,須以情勝,《內經》一言,百代宗之,是無形之藥也。”吳氏深明《內經》之旨,在長期的診療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意療經驗。盡管這些心理療法有著較為明顯的自發性和經驗性,還不夠系統完整,但仍存在著許多合理的方面,值得現代心理治療借鑒和吸收。深入研究吳鞠通的意療思想,對于豐富中醫的治療手段,建立更適合中國人的心理療法及完善現代心理治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董湘玉,李琳.中醫心理學基礎[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103.
[2]吳鞠通.吳鞠通醫案//李劉坤.吳鞠通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270,292,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