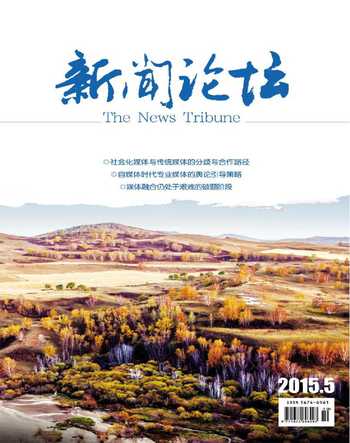論電視媒介普及對甘南藏區農牧民生計與生活方式的影響
王曉紅 張碩勛 梁爽
【內容提要】 大眾媒介在甘南藏區的快速進入與普及,正在緩慢而堅定地解構著藏區的生計方式。同時,在電視和網絡媒介的引導下,大眾媒介實現著對藏區社會環境和農牧民日常生活、社會慣習和生計方式的重新定義,新的生計方式被逐漸建構起來。本文選取甘南藏區5個代表性的村莊開展田野調查,在系統調查與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電視媒介與甘南藏區傳統生計方式的解構與生活方式的重構問題。
【關鍵詞】電視媒介 甘南藏區 生計方式 影響
每一種媒介技術的出現,都必然在與周圍現實關系的互動中獲得新的涵義,這種新的涵義關系到生活在這種媒介環境中的大眾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大眾媒介在甘南藏區的快速進入與普及,正在改變著農牧民千百年來形成的思考與行為方式,緩慢而堅定地解構著藏區的生計方式。同時,在電視和網絡媒介的引導下,大眾媒介實現著對藏區社會環境和農牧民日常生活、社會慣習和生計方式的重新定義,新的生計方式也被逐漸建構起來。正如波德里亞所說,“鐵路所帶來的‘信息,并非它運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新的結合狀態,電視帶來的‘信息,非它所傳送的畫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關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①
“每個民族在其生存的過程中都有一種主要的用以維持其生活的方式,以實現其基本的生存以及更進一步的發展。某個民族生計模式的變化是導致該民族文化變遷的基本因素。”②為了解大眾媒介普及對于甘南藏區農牧民生計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響,2009年7月-2014年9月,筆者帶領調查小分隊先后4次進入甘南州,開展了“甘南藏區大眾媒介傳播現狀與社會發展”的專題調查活動。調查采用問卷、座談、訪談、參與式觀察等多種方式,并配合有影像記錄。發放調查問卷總計540份,訪談49人,訪談錄像257段,回收有效問卷516份。期望通過系統的調查與分析,力爭準確反映大眾傳播背景下甘南藏區農牧民生計方式和生活方式轉變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態勢,為甘南大眾傳播事業與藏區社會的良性互動提出對策與建議。
一、電視普及與甘南藏區傳統生計方式的解構
“生計方式是對謀生手段的體現,它不僅能明確標示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向,同時也能容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所包括的涵義,生計方式包括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及物質文化。”③生計方式取決于架構在一定社會經濟形態上的生產方式,同時生計方式的改變也推動著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是社會經濟形態轉變的直接表現。
1.大眾媒介“助推”甘南藏區生產方式轉型
藏族在長期的游牧活動中,形成了“游牧文化”的一整套規則體系和價值觀念、財富觀念、消費行為、宗教信仰以及夾雜其中的神靈崇拜、兩性分工、親屬關系、婚姻及性行為等一系列生活內容。在傳統的生計方式下,牧民把財富理解為實物形態的牛群或羊群,牛羊群規模越大,不但表示財富占有越多,還有一種莫大的心理滿足感和幸福感,“惜售”是牧民普遍的行為。
除農牧業生產之外,甘南州由于地處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過渡帶上,當地回族、藏族等民族雜處,歷史上商業活動十分頻繁。“牛馬喧騰百貨饒,每旬交易不須招。酉陽市散人歸去,流水荒煙剩板橋。”④宋金對峙之時,金朝在臨潭3次設立榷場。明政府先后在舊城和新城設立了茶馬司。明代的洮州衛,基本上成為了漢人和諸番交易中心。“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地商旅來往者聽從其便,今隴各衛番人來洮,買賣交易,亦聽其便。”⑤當然,這種零散的商業活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甘南藏區生產方式的落后。“農民是永恒的人,它是一種無言的動物,一代又一代地使自己繁殖下去,局限于受土地束縛的職業和技能。農業是一種自然的生存方式,一種自然性的文化。”⑥
廣播電視進入甘南藏區后,攝影機擊碎了古老鄉村的懷舊神韻,電視節目的超級吸引力促使千百年來游牧的牧民越來越有定居的渴望。電視媒介的“大眾窗口”好比希臘神話中的普洛克洛斯忒床,它不斷地對窗口這邊的觀看者和窗口那邊的世界施行著“平均化”的強權,它按照公共尺度截去人和世界的頭和腳,再給人和世界安上假頭和假肢。“電視所表現的城市化的媒介文化極易在中國當代廣大農村中流行,現代文化觀念向農村的大舉滲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認同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挾帶著巨大經濟利益的都市文化,在農村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接受者。”⑦在與媒介的頻繁接觸當中,甘南藏區農牧民的價值建構方式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新的價值判斷很快滲透到農牧民對于生計方式的改變上。在梳理藏區廣播事業發展時,筆者注意到,甘南藏區社會游牧部落制(20世紀50年代末之前)階段基本上處于前大眾傳播時期,這一時期媒介的信息傳播使得社會處在“部落化”(麥克盧漢)階段,也就是人體、器物等媒介的使用將藏區社會分割為一個個小小的、自給自足的、相互隔絕的“部落”。 人民公社制(20世紀50年代末——80年代初)時期,正是藏區廣播發展的黃金時期,廣播全面參與了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活動。家庭“牲畜承包制”(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和“草畜雙承包制”(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時期,也是電視媒介進入藏區的歷史時期,如果說人民公社時期是藏區“非部落化”的鋪墊階段的話,那么,“牲畜承包制”和其后“草畜雙承包制”時期正是電視媒介加速推進藏區社會“非部落化”的重要時期。甘南藏區傳統生計方式在這一時期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傳統畜牧業開始向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現代畜牧業轉變,商業、手工業、旅游業、服務業等產業逐漸興起,原來依靠單純的農業、牧業、林業活動為生的農牧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大眾媒介每時每刻為農牧民提供著外部世界的新信息和身邊世界的新變化。同時,通過信息傳播把各個產業連成一個網格,大眾媒介把生計方式轉變的“骰子”擲了出去,農牧民的生計方式在這個網格中開始了多彩的跳躍。
2010年,筆者在甘南5村莊的調查顯示,有50%的樣本表示他們的日常種植、養殖活動借助電視媒介傳播的市場信息和技能。2009年,在甘南5村莊家庭經濟收入中,51.8%的收入來自外出打工,8.9%的來自運輸、采集等。而種植業的收入僅占17.9%,養殖業為家庭創造的收入最低,僅為3.6%。調查說明,甘南藏區傳統的以種植、養殖、畜牧活動為主要生計方式的格局開始裂解,現代第三產業逐漸成為甘南農牧民生計方式轉變的主要方向。
2.大眾媒介作為主導力量之一,引導牧民走向半定居與定居
宋蜀華先生在談到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的關系時認為,文化是人類對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適應性的一種表現,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生態環境會形成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即使在同一地域,自然和人文生態環境或者其中的一方的改變也會引起文化相應的改變,而文化對環境的調適又會反過來影響自然和人文生態環境,兩者的作用是相互的。⑧甘南藏區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濃厚的游牧文化,而游牧文化又進一步強化著農牧民的居住方式與日常生活。
甘南州牧區在20世紀50年代末之前,農牧民家庭分屬于各個部落組織,牧民個人沒有長期固定的草場和居住地點,大部分牧民常年過著“一年四季一頂帳篷”、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甘南牧區社會經濟制度由“部落游牧制”向“人民公社制”轉變,政府積極倡導牧民定居,甘南牧區在政府主導下正式實施牧民定居政策,至1982年實行家庭承包制之前,夏河縣和碌曲縣70%左右的牧業村和瑪曲縣的部分牧業鄉建立了以村落為單位的牧民定居點。20世紀80年代以后,甘南牧區開始逐步實行以“牲畜歸戶、私有私養”為主要內容的牧業生產家庭承包制,牧民居住模式由“村落集中定居”向“牧場散居游牧”轉變,很多牧民遷出了村落集中定居點,牧民居住方式趨于分散化,部分家庭在牧場分散建房、半定居游牧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甘南州牧區實行“牲畜承包制”和其后“草畜雙承包制”將原來公用的草場分割為零碎的“自留地”,牧民用“鐵絲網”將自己的“屬地”圈起來,原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據甘南州畜牧局提供的資料,截至2005年末,甘南牧區共有13595戶牧民,其中己定居的牧民6909戶,占甘南州牧民總戶數的51%。常年游牧未定居的牧民6686戶,占甘南州牧民總戶數的49%。⑨
在實現藏區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改變的施加者必須時刻掌握韋伯的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假設: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背后都存在著一種支撐這一事業,并維系這一事業成敗的無形的時代精神。在遷徙流動向定居半定居轉型過程中,電視正源源不斷地向改變中的牧民提供者這種“無形的時代精神”,成為支撐這一轉變事業的原料和基石。同時,電視拓寬了創業基礎,各種科教節目讓牧民在定居點有更多的就業選擇,電視為拓展創業的農牧民做出了貢獻,一視同仁地為所有人提供關于市場的觀點和方法。電視劇讓牧民更愿意享受家庭的溫馨與快樂,每天短短幾個小時的“電視時光”,是牧民一天的希望和意義。正如福柯所言,電視使我們成為“囚徒”,每天傍晚當你“囚室”的小窗戶被打開的半個小時的時間里,你趴在窗前,貪婪地看著小窗外的風景。荒草,斜陽,暮歸的畜群、歸巢的鳥兒……。在視野的盡頭,隱隱約約有農舍升起的炊煙,你似乎猛然明白在暮色降臨的時候能回到自己家中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二、電視媒介引導下的藏區社會生活方式的重構
“電視正在襲擊鄉村的生活和精神,占據統治地位幾千年的社會風尚正在經歷一場緩慢但平穩堅定的變革。滲透在傳統生活方式中的社區、宗教和性別的屏障正在發生顯而易見的坍塌”(Malik, 1989)。筆者對甘南藏區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日常活動的調查,從一個側面證實了Malik的結論是真實的,電視在甘南藏區的出現與普及己經戲劇性地改變了藏區鄉村中家庭的結構和日常生活。
1.勞動工具變化
麥克盧漢提出“一切技術都是身體增加速度和力量的延伸” ⑩在媒介技術決定論者眼里,日常生活的各種技術和媒介,不論其實際內容如何,它們重塑了時空結構,加強了文化間的傳播,改變了人類感知和體驗世界的方式與結構,從而導致文化變遷。從哈羅德·英尼斯,經馬歇爾·麥克盧漢、再發展到沃特爾·翁和喬舒亞·梅羅維茨,這些學者都堅持認為“技術對人類的感受能力以及社會結構具有改變作用”?輥?輯?訛,而這一切改變首先在人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中表現出來。
在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甘南藏區無論是純粹的畜牧業方式還是半農半牧的方式,由于地處高原山區、生存空間的局限與約束,道路交通十分不便,因而騾馬就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夏河關山重疊,道路崎嶇,交通不便,……皆因交通梗塞之故,夏河不通水行,惟藉馱工之力,以維交通,自拉卜楞至臨夏,為商人馱夫絡繹不絕,……本縣一切出口貨物,皆馱運至永靖口,用皮筏裝載直駛鄰省或鄰縣,……”?輥?輰?訛農牧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一直保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新技術很難獲得意見領袖的認可而進入推廣普及階段。
進入大眾傳播階段后,大眾媒介既提高了農牧民創新和使用勞動工具的積極性,又不斷地培養農牧民的勞動效率意識。筆者調查中看到,在甘南5村莊,機械化、電氣化的勞動工具已經逐漸替代了傳統的勞動工具,比如摩托車取代馬匹,拖拉機耕作替代“二牛抬杠”,電動打奶機、剪毛機替代手工操作。
2.家庭勞動分工的變化
現代家庭文化的構建是以現代文明為背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這種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文明使甘南藏區傳統家庭文化與現代工業文明在不斷碰撞中逐步調適。長期以來,藏族存在“女勞男逸”的傳統社會文化現象,它是藏族的“游牧文化”以及由此種生計模式和文化產生出的兩性社會分工造成的。在藏族傳統社會中,由于藏族傳統社會是以父系血緣氏族和農牧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在藏族此種社會經濟模式中產生的藏族男女兩性的社會分工,男性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主角,社會管理事務則基本上由男性一統天下,社會財富掌握在男性手里,由男性來支配。作為男性的附庸,女性只充當配角或邊緣性角色,女性主要承擔生育和照顧家務的責任,她們所承擔的是輔助性勞動。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電視逐漸在甘南藏區普及,農牧民接觸電視的時間逐步增加,農牧民家庭的性別分工有了明顯的變化。男人早晨將牲畜驅趕到牧場后,不再呆在牧場消磨無聊的時光,電視連續劇的牽掛使他們很快騎著摩托車趕回家中,一邊看電視,一邊幫妻子干家務活。筆者在甘南5村莊的調查表明,電視在家庭中的存在正在影響藏區農牧民家庭的性別角色,與家里沒有電視機的男人相比,家里有電視機的男人們傾向于做更多的家務。女人們同樣更清楚,要想在晚上享受電視所帶來的“幸福時光”,就必須盡可能早點幫丈夫完成一天的勞作。
另外,電視不斷傳播的新觀念,也改變了藏區“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傳統,與男性逐漸“戀家”、更多參與家務勞動一樣,甘南藏區的許多女性開始陪伴丈夫一起放牧、挖藥材或外出打工,勞動的性別界限逐漸模糊。筆者在七車村調查時,李建華老人告訴筆者,七車村為半農半牧區,村中大部分青年男女都不在家,一部分進山挖藥材,一部分去了縣城做生意,家里的農活和家務活都有老人們打理。在牧區上浪坎上村,許多女性隨丈夫去牧場,兩個人完成牧場的勞動后便趕回家中,一起做飯、洗衣、看電視。
從幾個村莊的調查看,隨著電視的普及和商品觀念的增強,甘南藏區傳統的兩性分工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原來“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已被打破。同時,電視的進入逐漸弱小了藏區男女兩性之間的性別不平等。筆者調查顯示,電視媒介在藏區的普及縮小了甘南藏區男女在諸如食物、金錢和時間等有價值的社會資源領域享用權的差距,女性扮演表達性的(expressive)角色(負責照料孩子并為其提供安全和情感支撐)和男性則扮演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角色(負責養家糊口)(安東尼·吉登斯)之間的界限明顯模糊,個人和群體的性別分工帶來了性別秩序的改變,處于等級頂端的“霸權的男性氣質”(安東尼·吉登斯)面臨危機,“家長制紅利”逐漸縮小。正如法拉蒂所說,“在傳統的忠誠、守信和責任正逐漸被滋長的消費文化和消費水平侵蝕的時候,男人們正在經歷一場質疑他們的自我價值和有用性的危機。”?輥?輱?訛在電視節目的不斷熏染下,藏區女性逐漸認為離婚并不總是不幸的反映,那么,愛情、性、子女、婚姻、家庭收支、家庭責任等世俗的和精神的話題都需要協商,男性在家庭中“一言九鼎”的“好日子”似乎走到了盡頭。
3.勞動時間的重新規劃
電視進入藏區之前,藏區農牧民傳統的日常生活由每天4個主要時段組成:早晨6點左右,婦女首先起床、收拾房屋和庭院、為外出放牧的男人準備洗漱熱水和早餐,牧場的婦女還要到牲口圈擠奶,男人比婦女起床稍遲一點,洗漱完后匆匆用點早飯就趕著牛羊上牧場或到田間勞作。整個白天都是勞作時間,沒有閑暇,一天的辛勞在黃昏時結束。晚上,是放松休息和發展人際關系的時間。
電視帶來的最明顯的影響之一就是電視戲劇化地改變傳統的勞動時間劃分,人們開始通過電視節目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根據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來判斷時間。在甘南藏區,農牧民的睡眠時間并沒有因為晚上看電視而減少,但電視確實推遲了農牧民晚間上床休息的時間。筆者調查時看到,晚上10點左右,大部分農牧民家里的電視熒屏依然閃爍著,而在以前,這個時間段農牧民早已進入夢鄉。由于晚上看電視,農牧民新的一天一般從早上8點開始。隨著勞動工具、交通工具的機械化和電氣化,農牧民的勞動時間明顯壓縮,牧場上的男人回家的時間比以前早了許多,夜晚的休閑時間也比過去開始得早了許多。在上浪坎上村,下午5點多,許多家庭在匆忙中用完了晚餐,電視熒屏閃爍的光彩阻止了他們外出開展人際交流的腳步,婦女在電燈下干著手邊的零碎活,不時瞄上一眼電視節目,小孩子在家長的呵斥聲中怏怏不快地去學習,但很明顯,他們的“靈魂”禁不住從門后的角落里張望著電視熒屏上的“花花綠綠”。當成人都不能抵擋“電子鴉片”的誘惑時,你怎么能指望小孩“心無旁騖”?許多農牧民收看電視節目直到凌晨,過去用作重要的人際交流的時間,現在被輾轉于遙控器指揮下的“國內頻道博覽”上了。雖然很多電視節目傳播的內容對于他們來說陌生而遙遠,但電視“勾”起了他們的欲望,欲望很容易培養,但很難滿足,因此上浪坎上村夜晚燈光綿延的時間越來越長。其他村莊的情況也是一樣,新奇世界的“窗戶”被打開,誰都想在“窗口”多呆一會。
三、結 論
電視進入甘南藏區后,也不聲不響地改變著農牧民千百年來所遵守的日常慣習、性別分工和勞動時間,媒介既是人的延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截除,電視媒介對藏區生活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大眾媒介影響下的勞動工具變更、勞動性別分工和勞動時間變化,標志著甘南農牧區民眾的生活節奏由以前的慢速低效向快速高效轉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優哉游哉,聊以永日”?輥?輲?訛逐漸遠去。大眾媒介帶給藏區農牧民對“新世界”愉悅的體驗的同時,也不斷膨脹著人們的欲望,欲望的滿足需要立足現世和高效率、快節奏的穿梭、合作與奔波。筆者不能想象,當正在進入的網絡媒介“陽光普照”的時候,藏區社會生活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骰子”已經擲出、“魔盒”已經打開,改變將無法回避,信息社會的車輪將沖破所有阻礙變遷的“土墻”,適應新媒介技術勾畫的生活藍圖將是農牧民最好、也是最理性的選擇。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媒介融合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區重大突發事件中的輿論引導與博弈策略研究”(15BXW043)與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5LZUJBWZX018)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讓·波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譯:《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②秦紅增、唐劍玲:《定居與流動:布努瑤作物、生計與文化的共變》,《思想戰線》,2006年第5期。
③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6, 87頁。
④政協臨潭縣委員會:《臨潭簡史》,1991年版,第173頁。
⑤政協臨潭縣委員會:《臨潭簡史》,1991年版,第131頁。
⑥[德]斯賓格勒著,韓炯譯:《西方的沒落》(上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98-208頁。
⑦單世聯:《現代性與文化工業》,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7頁。
⑧宋蜀華:《人類學研究與中國民族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關系》,《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⑨高永久:《藏族游牧民定居與新牧區建設——甘南藏族自治州調查報告》,《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⑩[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27頁。
編輯:邰山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