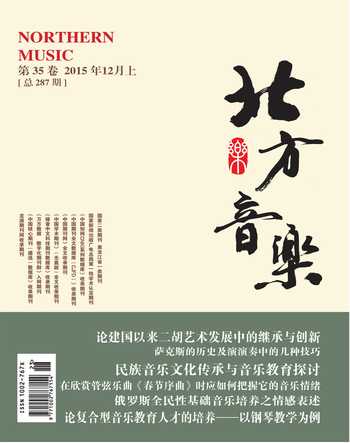內蒙古西部民歌的語音色彩分析
【摘要】本文運用現代發音語音學的理論與方法,并結合傳統聲韻學的分析方法,從方言的形態解析入手,針對地方歌唱風格形成中,內蒙古西部方言這一特定的語言“特化”系統在歌唱的行腔與運聲中所呈現出的特殊語音音響色彩,進行一一對應性分析闡釋。
【關鍵詞】內蒙古西部方言 ;語音音響;歌唱位置
漢語擁有眾多的方言,各方言之間語音差異,使民間歌唱,特別是較少經過專業藝人加工、較少與外界音樂交流的民間歌唱,更多地受到方言的自然語音的束縛,使方音的特征成為構成民間歌唱的地方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內蒙古西部地區的民間歌唱藝術有二人臺、漫瀚調、爬山調、小調等等。目前,爬山調、漫瀚調、二人臺都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它們共同的特點,也是最大的特點,就是使用本地區方言。明代王驥得在《曲律》一文中談到:“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為聲亦異。”每一種語言都有它固定的音色、頓挫、腔型、運用習慣等等,總之,有它自己的音樂。對于音樂中音色的理解,人們會更多地想到各種樂器所擁有的不同音響色彩,如琵琶、簫、二胡等樂器,它們給人帶來的聽感迥然不同,但各具神韻。
一、聲母特點及音響色彩
漢語音韻學中,將漢字音節分為字頭、字腹和字尾三個部分,而在唱曲中又相應地講為出字、歸韻、收聲三個步驟。所謂出字,即是要注意字頭的發音,而字頭往往是輔音聲母,個別時候是聲母加介音。
(一)內蒙古西部方言聲母在不同地區有所差異
東、中片絕大部分地區共有20個(不包括零聲母)。西片地區主要是鄂爾多斯、巴彥淖爾部分地區,以及與這些地區相鄰的包頭的小部分村落,發音中有zh、ch、sh、r四個聲母,因而這部分地區的聲母有24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地理位置上與晉、陜北部相鄰,受其影響較大。除此之外,其他字母發音情況東、西片基本一致。
z、c、s,[z]是舌尖前音, zh、ch 、sh、r是舌尖后音,和普通話的聲母系統相比,內蒙古西部方言聲母的舌尖音更多,即上下齒尖與舌尖作用下的一個聲音點,最靠近面部。因而無論是講話還是歌唱,都有出聲(出字)靠前的特點。同時,這個特點會連帶跟隨其后的韻母發音位置發生前移,如“zhao” (召)讀成“zao” (遭),“chai”(拆)讀作“cai”(猜)
(二)[v]:普通話中沒有這個音
普通話中所有以u作韻頭的零聲母,在內蒙古西部方言中均發音為[v]。[v]是唇齒濁擦音。如,王(wang),問(wen)會讀成“vang”和“veng”。
從普通話的[w]到方言的[v],出聲的位置和方法都變得不一樣。普通話[w]的是雙唇音,且因其具有半元音性質而口腔內無阻礙, 因此發音效果圓潤、通暢;而方言[v]是唇齒擦音,氣流通過下唇與上齒之間狹窄的縫隙而摩擦出音,且同時聲帶顫動。因此,內蒙古西部方言中的這部分語音,與普通話語音中的對應部分相比,移低了位置,拉平了口腔,口形呈唇齒閉合,嘴角向兩邊拉伸,口腔空間的立體性隨之下降,所以出聲有低而橫咧的特點;同時還因摩擦出音和聲帶顫動的特點,所需氣流的量與強度均要增加,因而產生的聲音效果就有了生澀、蒼勁的感覺。
(三)[]是舌根鼻音,普通話中只作后鼻輔音韻尾,內蒙古西部方言中還作為聲母字頭來用
普通話中以開口呼a、o、e為韻腹的零聲母音節,在方言中均冠以[]為聲母字頭(極少數的幾個感嘆詞和語氣詞除外)。如:“恩愛”讀作[],“安全”讀作[qy]等等。
由于普通話的零聲母音節是開口無阻的,發音中心在口腔中部,音響有明亮、飽滿、圓潤的色彩。而在方言中,這幾個單韻母以及以它們打頭所組成的復韻母,發音時都需用[]作字頭。[]是舌根與軟腭的成阻爆破,位置靠后,并且它會連帶其后的韻母發音也相應后移,使得口腔后部的音響色彩更濃重。同時由于對[]字頭的除阻,需要比普通話零聲母更多的力量和氣息,使得發音更有爆發力。
二、 韻母特點及音響色彩
(一)內蒙古西部區方言中保留大量入聲字
內蒙古西部區方言中保留著大量入聲字,其韻母有8個,分別是[a]、[ia]、[ua]、[ya]、[]、[i]、[u]、[y],全部為喉塞音。如黑、沒、活、鐵、吃等。
“喉塞音”,顧名思義就是發生在喉部的塞音。塞音也叫爆發音或者破裂音,發音時,發音器官的某個部位完全閉合,使氣流通路暫時阻塞,然后突然張開,使氣流爆發而出成音。如雙唇塞音,唇齒塞音,這是普通話和方言中都有的。但內蒙古西部方言中的喉塞音卻是普通話語音中所沒有的。它的阻礙與爆破發生在喉部,產生鮮明而獨特的喉音色彩。因此在外地人聽來,內蒙古西部人歌唱似乎是從喉嚨里發音。
(二)內蒙古西部方言中沒有o韻
普通話中與o相拼的字大部分歸入聲韻,部分歸e韻。如:伯、摸、脖、握;我、波、破、落等。
如此一來,普通話中的這部分語音在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中口腔的立體性和音響的圓潤色彩減弱,而且歸到入聲韻的部分更被推向靠后靠下的喉部,因而音響效果變的更低沉、直硬一些。
(三)舌尖鼻音與舌根鼻音不分,通俗說就是前后鼻音不分
內蒙古西部方言中,有en[n]、in[in]、uen[un]、ün[yn]、ian[ian]、üan[yan]這幾個韻一母。普通話中的前鼻音韻母en、in、uen、ün一律讀成后鼻音韻母eng、ing、ueng、iong;ian、üan讀作ie[i]、e[y]。
在內蒙古西部方言中,舌尖鼻音(前鼻音)的缺少,減弱了語音中親昵、嫵媚、輕巧的色彩。但這種色彩又通過語音的重疊等方式得到了彌補,呈現出獨特鮮明的地域性;然而舌根鼻音(后鼻音)分量的增加,又大大強化了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靠后的特點和高亢、憨直的聽覺效果。
在眾多的漢語方言中,四川話也有前后鼻音不分的特點。但與內蒙古西部方言相反,四川話沒有舌根鼻音。普通話中的舌根鼻音在四川話中都變為舌尖鼻音,因此四川話語音的整體感覺就是比較靠前、靠上的,在四川民歌的演唱中,能明顯地感覺到。
前面羅列和分析的幾個關于聲、韻的特點,是在與標準語(普通話)相互比較中差異突出的幾個方面。事實上,即使在表格中標注相同音標的音,其實際發音的效果也是不完全一樣的。他們分屬不同的音體系,不同音體系的發音重心也必不相同。即便是某兩個音用同一個國際音標標記,但在不同音系重心的牽引與各音素相互作用之下,也會產生色彩的差別。
三、歌唱語音位置
語言界常提一種“特化”現象,即任何一種人類語言都是一種特化了的聲音系統,聲音的特化,需要一套特化了的語言發音器官。即長期使用一種語言,會使發聲器官的相關神經和肌肉發生習慣性反應,創造出獨特的音響。產生了這樣的現象:意大利人都擅長發舌尖中顫音(俗稱“打嘟嚕”),法國人都擅長發小舌顫音;閩南人因舌面前高元音的鼻化音用得多而鼻音亮麗;彝族人因濁音用得多而低音渾厚。
這種語言的特化現象同時造就了各地域人群歌唱的特殊能力。因此,不同的語言造就了不一樣語音發聲系統,地域性唱詞的語音位置,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歌唱咬字的位置。誠然,歌唱不是說話,歌唱時的咬字發音當然與說話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它們畢竟同屬于一個語言特化系統。
方言在歌唱語音上僅僅是相對于普通話或另一體系的語言在聲母、韻母和聲調等方面的差異,并不影響方言和其他語音所依賴的高品質聲音載體,即科學的歌唱聲音。有成熟的科學歌唱發聲法,千變萬化的聲、韻組合與聲調變化,都能夠產生優美、漂亮,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的聲音來。
方言和科學的發聲在歌唱中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發聲是歌唱的載體,方言是歌唱中語音的個性表現因素。因此,如果用位置去限制語言,必然會導致唱詞語音的變異,聽起來“非驢非馬”,唱起來既不自然自如,也難以達到“字正腔圓”。進而也無法準確表達歌詞的內容和意境。
元音本是通過舌位和唇形的改變來變幻音響的。元音也稱母音,它是語言里最響亮的聲音,是樂音。聲波通過時,由于口腔形狀的變化,也就是共鳴器形狀的改變,導致形成各種不同的元音。而口腔形狀的變化是由舌頭的高低(相應地也就是口腔開闊度的大小)、舌頭的前后伸縮、以及嘴唇的圓、扁這三項條件所決定的。口型和舌的位置都通過影響共鳴體的大小直接影響共鳴效果。美聲唱法的聲音有種“豎起來”的感覺,這與其產生地意大利的語言是相適應的。與漢語普通話相比,意大利語音的特點之一,就是元音的發音中心圈位于口腔中部偏后,且口腔內立體空間更高更開闊(比較上面三個舌位圖可以明顯地看出);再者,意大利語很少用輔音韻尾。輔音發音是有阻的,不同的輔音有不同的發音阻礙。這樣,意大利語元音飽滿且少有阻礙,具有高、滿、通的特征,大概這就是美聲唱法給人“聲音豎起來”的重要原因。當我們采用這兩種不同的發聲方式時,自然會產生不同的音響效果,所以如果用漢語的發音習慣和方法去發意大利的語音,就會改變意大利語元音的共鳴狀態,從而失去意大利語元音明亮圓潤的色彩。反之,用發意大利元音的音位來唱漢語的相對應元音,就會失去漢語元音的松弛感。
基于意大利語言的聲樂品種,有一種可稱得上“輝煌”的美,這一點我們絲毫不能否認。但是意大利歌唱的美,絕不是世上唯一的聲樂美。以各種母語為基礎的聲樂品種,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地域性魅力。
內蒙古西部語音,有自己獨特的發音位置。首先,通過內蒙古西部方言舌位圖可以看出,它比普通話更靠后一些,這一點與意大利語相似,但意大利語是立足于這一偏后的核心點后,向著立體高闊的要求開拓空間;而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卻是向后、向下,有向咽腔、喉腔開拓空間的趨向,方言語音中大量的喉塞音和舌根音即是佐證。其次,造成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位置偏后、偏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聲母[]的使用,[]是舌根鼻音,是舌根與軟腭的合作成阻而后爆破發音。它做聲母時,會將其后的韻母發音連帶推后。還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口形或唇形的“扁、咧”的特征。前面在語音特點的分析中知道,普通話中[w]、[o]等圓唇音,在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中基本消失。[w]的發音在方言中變為[v],由圓唇音變成唇齒濁擦音,由高圓無阻變為低扁摩擦。[o]的發音在方言中變為[e],唇形由圓變為橫咧。上面所講的幾點只是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具有突出特征的幾個方面,事實上,內蒙古西部方言語音獨特的發音位置和音響面貌,是由組成整個方言發音體系的所有音素相互作用、共同造就的。
如此,內蒙古西部的民間歌唱首先在語音色彩上樹立了自己的格調,彰顯了獨特的地域性價值。色彩本無關雅俗,雅俗只是鑒定者的偏見而已,是文化認識上不成熟、不寬容的表現。“土音土韻土腔調”顯示了它獨特的文化歷史和存活樣態,莫要等到真正理解了它的價值的時候,它已經面目全非甚至不復存在了。
參考文獻
[1]周青青.漢語語音的聲韻因素在漢族民間歌唱中的作用[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7.4
[2]章鳴.語言音樂學綱要[M].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1).
[3]張應斌.漢語樂音語言論[M].長沙:岳麓書社,2006.
[4]楊春暉.論方言在歌唱語音中的運用{J}.寧波大學學報,2003.
[5]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
作者簡介:孫麗娟(1975—),女,內蒙古包頭人,漢族,包頭師范學院音樂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聲樂理論與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