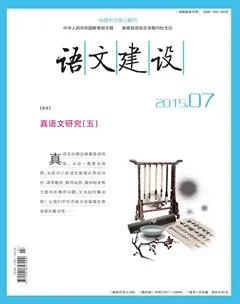高考作文:最欠缺的是思維
寫作的本質目的是表達和交流。交流的前提有兩個:一是作者有表達交流的愿望,即寫作的內在動機;二是作者有表達交流的內容,即作者有豐富的傳輸信息。
高考作文的命題一般都會在這兩方面做出努力,目的是讓廣大考生有寫作的內在驅動力,題目能激發考生思考,讓考生想說話;且能在考生的表達中顯示其思考的針對性、準確性和深刻性。本文不對今年十多道作文題一一臧否,因為語文學科內外的許多專家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和個人興奮點出發,對高考作文題進行點評,得出的結論千差萬別,這對高考作文命題和中學寫作教學實踐意義不大。因此,本文僅以上海卷作文為例,探討高考寫作的目的和現實困惑,并提出一些建議。
一、考試大綱:預設的目標并不高遠
高考寫作要求考生能寫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和常用的應用文。上海卷《考試手冊》從“思想內容”“結構布局”“語言表達”三方面做出了詳細規定。全國卷及其他省市卷的考試說明評判寫作分為基礎等級和發展等級兩類要求,發展等級強調深刻、豐富、有文采、有創新。簡而言之,高考寫作主要是檢測高中學生審題立意、布局謀篇和語言表達的能力。
1.與法國高考作文的比較
法國高中畢業會考的哲學作文題,相當于中國高考的語文作文題。根據法國教育部頒發的教學大綱,哲學課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標,以領悟時代的意義”。法國國民教育督察官馬克·謝林姆說,教育對于構建哲學的“文化與思辨”基礎至關重要;而哲學教育的主要目標在于發展個體的“自我省察能力”。哲學課的設置旨在培養具有“智性批評能力”的啟蒙公民。哲學的思考方式教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反省,如何深入思考問題。
與法國作文相比較,我們的檢測指標傾向于寫作的技術性要求。我們的哲學課程不屬于母語教育范疇,我們所謂的思辨性被簡單地理解為“一分為二”看問題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思辨強調的是在不同層面上對同一個問題展開有條理的分析,下文將對此展開討論。
從思想層面看,我們的高考作文主要檢測學生能否讀懂語料(包括材料作文、話題作文和命題作文),能否從語料中抽繹出主旨,并選擇自己熟悉的領域確定文章主旨,然后選用合適的材料演繹主旨。——這很大程度上是對命題者設題意思的解讀和回答,與啟蒙公民的“智性批評能力”關系不大,離“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標”還很遙遠。
下面是法國的作文題,可能會令考生和語文教師驚詫。
尊重一切生命是一種道德義務嗎?
現在的我是我所經歷的一切造就的嗎?
個人意識僅僅是其所屬社會的反映嗎?
藝術家是否在其作品中刻意留下讓人意會的內容?
藝術品是否一定具有某種意義?
政治無須講求真理嗎?
所有信仰都與理性相悖嗎?
工作僅僅是為做個有用的人嗎?
我們的語文高考作文目前無法與法國作文相比,也不好簡單比較。我們的試題一般是給定語言材料,且語料隱含了題旨,在此情境下,考生的作文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高考作文暴露了考生的思維空間狹小,也暴露了寫作技術層面上的困境,由此折射出的語文教育問題值得深思。
2.與科舉時代寫作比較
回溯過去,科舉時代的寫作是替圣人立言,在立言過程中可以見出考生的襟懷抱負,考官據此選拔才俊,目的是選取和儲備治國安邦的行政官員。命題和閱卷都由主考官操持,命題的目的和選拔的標準更加明確。現在的高考作文命題,雖然有人詬病其政治正確的呆板,一方面可能是批評者的過分解讀;另一方面,即使有政治性,也是作文命題的題中應有之義。問題是,讓考生思考這些政治正確的空泛論題,與選拔人才的關系并不密切。今天閱卷者與考生的關系,與科舉時代考官與考生的關系早就不可同日而語。這種背景下,即使命題者煞費苦心,考生的寫作與哲學思辨、社會政治、國計民生的關系還是無限遙遠。考生的襟懷抱負還是難以窺見。
因此,現在的高考作文,總體上只是讓考生在命題者設置的話題范疇內,表達大家心知肚明的正確的看法。命題者、考生和閱卷者相互敷衍,高分考生貢獻的也不過是行云流水的符合主旨的故事,爐火純青的起承轉合。具有深刻見識者極為鮮見。
二、考場現狀:思維的平庸和表達的混亂
我們來看2015年高考上海卷作文題:
根據以下材料,自選角度,自擬題目,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不要寫成詩歌)。
人的心中總有一些堅硬的東西,也有一些柔軟的東西,如何對待它們,將關系到能否造就和諧的自我。-
這道題目繼承了上海卷近幾年的風格,即:在兩難困境中如何選擇才能趨于平衡。前幾年與此相似的題目有:“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不會過去”,“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的自由與必須穿越這片沙漠的不自由”,“生活中,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但世界上似乎總還有更重要的事”。
這些題目多少都揭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凡是揭示了人類生存困境這類永恒話題的作文題都是好題目。因為它超越了當下,又在當下被普通的生命經歷著。這些題目都需要考生有較高的思維水平。
從給定的材料中尋找并演繹主旨,相對于給定一個哲學話題要求考生闡釋自己的看法,難度要低得多。有人指出今年上海卷的這道題,最大的局限就在于答案已定——要做一個和諧的人,考生只要回答如何處置內心的柔軟和堅硬,就可以了。盡管如此,考生的作文仍然遠遠沒有達到讓人滿意的程度;就算是回答這樣的問題,也仍然沒有出現大量“觀點正確,表達流暢”的文字。
1.審題立意出現偏差,是思考能力薄弱的反映
從給定的語言材料中抽繹出主旨,看似簡單,實際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題目設置的情境是柔軟和堅硬同時存在于人的內心,讓人難以取舍決斷,要求考生面對這一困境思考如何達成和諧的自我;題目的核心旨意應是討論如何對待原則與人性,如何在堅硬的原則(道德、法律等)和柔軟的人性(情感、悲憫)之間達成平衡。考生作文中有以下立意:
堅硬的是原則,柔軟的是堅持原則時也不會冷血;即使是懲罰罪犯,也有一份對生命的原本的悲憫與同情,有一份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柔軟在。
鐵石心腸宣稱自己是正義的化身,罔顧人情豈不等同于機器人?過于柔軟為情所困,忽視道德倫理亦非正常合理之舉。
一個人做任何事都好像在執行法律,板上釘釘,那他周圍的人定會離他而去,因為他太絕情。但如果他有求必應,對任何請求都不愿意說出“不”,那他就可能為此疲于奔命,并且為自己無法滿足別人的要求而痛苦,甚至有可能為此踏入法律的禁區。
不少考生卻將立意悄悄改為“性格的堅硬與柔軟”或者“俠肝義膽,鐵漢柔情”。例如,一些考生在文章中討論堅硬和柔軟的關系,進而提出“因為人的外部堅硬,內部柔軟,所以要用堅硬保護柔弱,增加堅強的比重,彌補柔軟之不足”之類似是而非的觀點。還有不少考生援引當下發生的新聞事件,認為某位搶險救難的英雄人物舍生取義,是因為他有堅強的內心;這位英雄的堅硬恰恰是因為他內心對受災受難群眾的熱愛(溫柔的軟)。——這些立意與原材料若即若離,實屬隔靴搔癢。
正確審讀材料,進而確定自己文章的主旨,能寫出“語言通順,觀點正確”的文章,就算是二類卷了(滿分70分,二類卷為52-62分),這樣的考生遠沒有半數。至于觀點深刻、立意創新、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文章,更是鳳毛麟角。
盡管命題者的初衷是不在審題立意上為難考生,讓不同層次的考生都有話可寫,但高考作文的命題很少有那種一望即知的材料,每年都有不少考生在審題立意這一關就基本被淘汰出局了。這也是選拔性考試應該具有的功能。對于寫作教學來說,教師還是應該訓練考生分析材料的能力,讓考生在審讀材料時有精準的針對性,不能提煉太過,如上文列舉的“度”“現象與本質”“心態最重要”等。這類母題凌駕于任何作文題之上,只是提供了思考的范疇,絕不能代替思考本身,考生往往不明就里,簡單套擬,最后寫出了不倫不類的文章;也不能不做提煉,僅就事論事;還要嚴防偏離題旨,若即若離的立論。
2.文章結構單一,是說理能力薄弱的反映
不少作文在舉例分析時,一例寫堅守信仰的堅硬,一例寫溫情脈脈的柔軟,兩者毫無關系。常見的模式是:先寫張三性格堅硬,再寫李四性格柔軟,最后提供正確的案例——王五軟硬適中,所以他和諧了。這樣的作文,錯誤的根源還在審題立意上,思考沒有針對性——原材料討論的軟硬不是分屬于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而是一個人如何面對自己內心的柔軟和堅硬。單獨討論堅硬和柔軟的優缺點,對這個作文題而言,有什么意義?
不少考場作文在確定主旨之后,通篇采用例證,形式單一,缺少議論和分析,實際上這也是思維單調和膚淺的表現。為什么考生習慣于以敘代議?因為相對于艱難的說理,敘事總要簡單些。說理的第一要義是要有針對性,要和命題者給定的材料語境在同一層面上討論問題;這對不少考生來說,是要“踮起腳尖的事”,很困難。而敘事則可以用現象代替議論(高明的說理也會用到形象,我們不否認形象說理的必要性和優越性),遺憾的是大部分考生因為對題旨本身就理解得不夠準確,列舉出來的現象就更加模棱兩可。因此,考場上產生了大量這種審題立意不清晰,以敘代議、結構單一的“偽文章”。嚴格來說,它根本就不是文章,沒有明確清晰的主旨,通篇堆砌了一些前后不相銜接的例子,就像一堆雜木棒子橫七豎八地摞在一起。
我們缺少布局謀篇方面的訓練。教師習慣的是教給考生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一些模式化的結構。下面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針對材料提供的信息,考生與命題者在同一層面進行思考了嗎?
考生能用一句話,清楚明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嗎?
考生在表達自己的思考時,有沒有讓讀者順著他的思路逐漸抵達問題的核心?
如果這些問題在寫作教學中得不到落實,考場上的作文肯定還是讓閱卷者覺得乏善可陳。更嚴重的是,考生沒有思考的習慣,個體的“自我省察能力”“智性批評能力”永遠得不到培養,這樣的公民將來也就很難在日常生活中反省,很難有針對性地思考社會問題。
由此反觀我們的寫作教學,的確許多地方有待改進。教師提供給學生的往往是作文結構的模式,如起承轉合、并列層進等,學生習慣的是記住這些模式,至于概念辨析、邏輯推理等能力則很少得到訓練。下面我們引用上世紀末曾在四川任“外教”的美國人何偉(彼得-海斯勒)的故事,對于其中的細節,我們一定會覺得很熟悉。
這是一篇典型的五段式文章,文章的開篇講述了人們反對三峽工程修建的幾大風險:自然風景和歷史名勝被淹,所危及的物種可能面臨滅絕,縱深四百英里的水庫大壩容易招致地震、滑坡和戰爭破壞的威脅。文章的第二段總結道,“該工程所面臨的風險太大,很難說有什么益處”。緊隨其后的兩個句子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中的擔憂和風險不無道理”,文章繼續寫道,“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接下來,文章的作者對其中的益處進行了描述——發電量增加、航運條件改善、洪水得到控制——最后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利大于弊。
那個學期剩下的時間里,我因為學生在作文中大肆應用那種承上啟下句而備受折磨。他們習慣了用死記硬背的方式進行學習,也經常性地套用這樣的范例,甚至到了抄襲的程度。很難真正意識到這樣的做法是錯的——全校上下的學生得到的教誨就是模仿范文、抄抄寫寫、不加質疑地接受,他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后來,我布置學生就哈姆萊特的格格特點寫一篇議論文,他們在開篇部分列舉了哈姆萊特的弱點——優柔寡斷、對奧菲莉婭太冷酷——到此為止,很多學生的作文似乎都寫得相當不錯,可那個討厭的句子不知從哪里又一下子冒了出來:“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開始感到厭惡,反復跟學生講,這是個令人反感的轉折句,但它仍舊不斷地在學生的作文里露面。
很多學生只會簡單地模仿,所以不能只簡單地教給他們一些結構方法和典型句式,要開啟學生的大腦,讓他們主動思考。
我們耐心地查看三類卷、四類卷作文,希望從混亂的敘事和說理中理清頭緒,極力還原考生的思考過程,可惜的是,最后也被他們給繞了進去,不知所云,無功而返。由此,我設想,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很重要,高中三年的寫作教學一定要教會學生讓思維聚焦于一個核心原點,教會學生針對主要問題發表看法的好習慣,至于觀點是否深刻,倒在其次。
3.語言表達華美空虛,是思維混亂的反映
請看下面一些美妙而奇怪的句子:
反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一書中主人公薩比娜酷愛創作,她能從虛假的廣告牌背后直面淋漓的真相。真正的勇士以堅定的信念面對慘淡的人生,你又怎能說他們沒有一顆溫暖柔軟的心呢?
枕以柔席,筑以磐石。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面對浮躁的塵世鉛華,我們能做好的,不就是內心建造一所靈魂的居所,盛放我們疲憊的靈魂嗎?
冷漠無情的人心中盡是堅硬的磐石,貼近他們的內心不過是寒冷如冰;阿諛奉承的人心中盡是柔軟的枕席子,讓人無法心生好感。
海子說,我有一棟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淡淡的海鹽香味撲面而來,幽幽的花的芬芳……這不僅是海子心中的柔軟,也是億萬兒女心中的柔軟。這是一種愛,對生活和生命的愛。
這類文風在全國各省市的作文里并不鮮見。文風華麗當然可以,前提是有真實的內容。有些見解深刻的文章,文采斐然,文質彬彬,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優秀范例。我想說的是,上面列舉的這些纏夾不清的句子,絕大部分是作者認識混亂的表現。有的是對援引的原著不了解(或者根本沒讀過,或者讀了但似懂非懂,或者完全錯解),有的是對文章要討論的核心概念在確認時游移不定,有的是對一些流行語句的簡單模仿。——凡此種種,皆由思維不清晰造成。慶幸的是,上海卷閱卷主事者嚴厲抵制了這種文風。
三、建議: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和題目可能抵達的深度
這些年一談到高考作文,大家都知道要學會“思辨”,但“思辨”到底是什么意思,卻很難說清楚。一般人理解高考作文的“思辨”就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分析堅硬和柔軟的矛盾統一關系,認為柔軟和堅硬二者的完美統一就是和諧。將這道寫作題變成了一道庸俗的、簡單的哲學問答題。
詞典上的解釋是——思辨:哲學名詞,純粹的思考,相對于經驗思考而言。也指思考辨析。
詳細論之,思辨指的是運用邏輯推導進行純理論、純概念的思考。思辨能力主要表現在分析問題時能將思考的層面區分開,能講究層次、清楚準確、明白有力地進行說理。
不是所有的問題都需要純粹的理論思考,或者說,許多問題僅靠經驗思考就足夠了。需要思辨的問題往往是將人置于一種兩難處境,如上文列舉的近幾年的上海卷作文題,我們很難就此斬釘截鐵地給出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有時候,命題者未必是讓考生給出答案,因為能檢測考生語文能力的往往是思考的深度,而不是結論本身。對于人類永恒的困境,有些結論太簡明,有些結論早就眾所周知,寫作檢測的是考生面對這一困境時怎樣進入思考空間,怎樣條分縷析、有層次地表現自己的困惑,并不追求考生有自己嶄新的回答。
循此審視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題,要求考生在準確解讀堅硬和柔軟之后,討論如何使二者和諧。題目規定了話題指向,一定程度上也就縮小了論辯空間。大多數考生在規定的區域里老老實實答題。很少有考生思考:給出如何達成和諧的答案不是重點,思考這兩者的矛盾才是正經。展示思考的過程,表現自己的困惑,也許更能顯示思考的深度。
我們的教育總是告訴學生,今天的文明處于人類歷史上最輝煌最偉大的時刻,學生常常自豪地站在人類歷史的制高點,輕描淡寫地說:從宋朝開始,人們就已經知道要做到堅硬與柔軟的和諧,那么我們今天還有什么難題不能攻克嗎?毫無理由地自信,自以為能解決人類歷史上出現的任何難題,對這些難題都能給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實際上,這完全忽視了人類永恒的困境。膚淺的答案阻止了思考應有的深度。如面對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毀滅”的經典之問,那些平庸的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大腦會說:哈姆萊特,你不要憂郁,不要猶豫,做人嘛,就是要挺身而出!面對叔本華的悲觀哲學,他會說:不要悲觀,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要對生活充滿信心嘛!——說的都對,但請注意,哈姆萊特、叔本華是在什么情境下說出這番話的?對話之先,要懂得別人到底說了什么,因何說了這些。所謂思辨,還指論說者要和原材料同處一個層面,有針對性地進行對話。
一切好的作文題都指向人類生存的永恒困境。如果對這一困境有自己的思考,甚至只是困惑體驗,就已經在拓展命題者原來設定的空間了。不必責怪試題空間小,要讓自己的腦洞大開。不要簡單質疑前賢,或者粗暴地回答前賢留下的永恒問題。譬如說,當我們遭遇到原則之硬和人性之軟的矛盾難以自處時,不要簡單地談什么和諧統一,談什么巧妙結合,不如談我們遭逢這些問題時的苦楚、矛盾與煎熬,對前賢提出的如今降臨在我們身上的問題繼續思考,體驗那一份取舍的艱難,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維。
參考文獻
[1][2]韓梁.法國“高考”為何偏愛哲學[N].文匯報,2015—6—20.
[3][美]彼得·海斯勒.江城[M].李雪順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