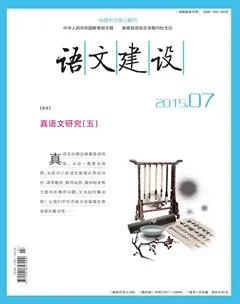赤子情懷與人性光輝
退休十余載的吳國韜先生的回憶錄《雨打芭蕉》(語文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不久前獲得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提名獎。此作品亦可歸于時下較流行的個人生活史寫作。它記錄的時間自1958年至1980年,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件,比如說“大躍進”、大饑餓、十年“文革”、改革開放最初決定性的幾年等,作為底層親歷者的寫實性回憶,顯然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
雖然是回憶錄,但其文學及精神文化價值不可低估。看過《雨打芭蕉》的讀者,都會為作者出色的敘事、刻畫與描述能力所吸引。作品中,一個個人物躍然紙上,豐滿而鮮活,自然山水也活了起來,生機盎然,仿佛回到了歷史的境遇。不過,作為先生當年親自教過的弟子,并且還是這部作品中的一個角色,我更為看重的,還是作品中表現的真實而光輝的人性。《雨打芭蕉》在語言及修辭上的功夫,實是作者之人格魅力及精神超越性的顯現,所謂“修辭立其誠”,支撐作者杰出敘事能力的,實際上是其赤子般的情懷,是其對家園、對國家的情懷。
作品很感人。作者對家庭、對親人的眷顧是感人的、真實的,對自己作為美少年的那些浪漫故事的敘述也同樣感人。作者的愛戀中透出了純潔,乃是處子的心境及情懷,真實而令人回味。特別是讀到作者年少身患重病時的心境,讀到艱難歲月時親人間的相依為命,那份牽掛,好男兒的細膩與柔腸,使人生出心痛與凄惶,聯想到當時的境遇——一介書生本無力承擔而又必須承擔的命運,更是讓人悲從中來。作品傳達的顯然不是悲情,正如作者的人生觀里沒有悲觀主義一樣,當人們在可能已經陷入某種負面或怨恨的情緒時,作品筆鋒一轉,不經意且確定性地把人帶到一種樂天逍遙且隨遇而安的境遇中。作品并沒有讓某種悲情或者文藝的元素侵蝕日常生活本身,而是轉而讓有可能軟弱的生命體驗服從于生命意志,并表現出積極通達的人生態度,表現為隨處可見的幽默,釋放出了浪漫與逍遙。生活中吃了那么多的苦頭,還能笑對、直面人生,顯然不只是一般的樂觀,而是境界上的達觀,這樣的大美感人至深。
作品寫的是一方鄉域,但呈現出來的儼然是一個大世界,精彩紛呈,層次多樣,那個地方并不偏僻,國家的興與難,都反映在社會生活中。作品布滿鄉土氣息,芭蕉系恩施下面的一個鄉鎮,時至今日,恩施還被外面視為神奇的土地。如果剝離風土人情及其習俗上的差異,它就是活脫脫中國生活的一個縮影。作者借助把握的當代中國圖景來觀照芭蕉,以芭蕉之小映國家之大,也以國家之氣概察芭蕉之實。在這背后,寄托的是作者的家國情懷。
讀《雨打芭蕉》時,我一直想著如何定位作者的形象。好像是書生,一種儒家與道家同時兼備的書生,一種生發于傳統而又總是在與時俱進的現代書生。作品描述了一種看上去“被拋”的命運——因政治境遇的變化而被下放到荒僻的戽口,然而,作者本人卻很快地融入了當地人的生活且有滋有味,不僅如此,也讓家里人活得有滋有味。在學會了很多當地人的“活路”與生存技能時,作者也把自己變成了能人。作者的感覺甚至讓人想到,即使不作為當地受人尊敬的民辦老師,作者也照樣活得有滋有味。在作者身上具有與周圍世界的非同尋常的協調與平衡能力。作者隨遇而安且不失豪邁地置身和融于百姓生活,但又憑借自己的毅力與才華不至于陷入碌碌無為的庸常(或者換句話說,使庸常無為的生活過得充滿活力、有滋有味),并有所作為、造福一方。這正是平凡人生中的偉大。
赤子之置于山野,照樣從容而精彩,照樣在其中培養家園情懷。這里,“被拋”也好,“沉淪”也罷,置身于戽口的作者及其家人,其實已經有了踏踏實實的家園感。作者及家人的眼里全是善良,將心比心,一個人從善如流,那么世界便愈加善良美好。籠罩在作品里的是禮樂有序的風氣與氛圍。這里面支撐的元素,還是融入日常人倫生活的人道主義精神,一種源于儒家所謂“仁者愛人”“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精神情懷。
時下的文學作品大都已沒有能力表達人道主義精神,概因其精神生活狀況已經喪失了勇氣。文學喪失于精神生活的實實在在的匱乏中,精神生活的匱乏實際上又因為其迷失于物化生活的空洞形式,文學本身也堂而皇之且振振有詞地宣布其終結。如此老掉牙的話語現今依然甚囂塵上,但還是無法掩飾骨子里的貧乏與無知,仿佛一提文學,便一定意味著“文藝”而全然沒有了自信。相比之下,《雨打芭蕉》不僅表達了那一個特定時代的精神狀況,那一方水土的風土人情,包括特定時代里人性可能的復雜及其難以泯滅的平凡而偉大的同情心,而且實際上由此映現和穿透了當今的時代天空。
《雨打芭蕉》注定是一部留得下來的作品。
(吳國韜著《雨打芭蕉:一個鄉村民辦教師的回憶錄》,語文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