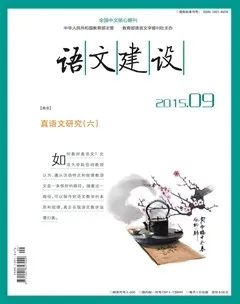抓住漢語的音樂性特點(diǎn)教語文
語文的基礎(chǔ)是語言,這毋庸置疑。《義務(wù)教育語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2011年版)》對語文課程“是一門學(xué)習(xí)語言文字運(yùn)用的綜合性、實(shí)踐性課程”的定義,就是在深刻認(rèn)識語文和語言的關(guān)系基礎(chǔ)上做出的正確判斷。漢語言是有個(gè)性特點(diǎn)的,這也無須爭論。語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強(qiáng)調(diào),“語文課程應(yīng)特別關(guān)注漢語言文字的特點(diǎn)對學(xué)生識字寫字、閱讀、寫作、口語交際和思維發(fā)展等方面的影響”。課標(biāo)對語文課程性質(zhì)的界定及特點(diǎn)提倡,其實(shí)已經(jīng)提出了當(dāng)下語文課程建設(shè)的兩大研究課題:漢語特點(diǎn)及其規(guī)律的研究,以及如何依據(jù)漢語特點(diǎn)和規(guī)律進(jìn)行教學(xué)的研究。不過可以想見,這兩個(gè)課題將是長期的、艱巨的、浩大的學(xué)術(shù)建設(shè)工程。筆者不揣鄙陋,試就漢語的特點(diǎn)之一——音樂性,結(jié)合語文教學(xué)實(shí)踐,談一談自己的認(rèn)識。
音樂性是漢語的一個(gè)突出特點(diǎn),這與其獨(dú)具特色的音節(jié)結(jié)構(gòu)及聲調(diào)系統(tǒng)有關(guān)。首先,漢語一字為一個(gè)音節(jié),音節(jié)時(shí)長大體相等。音節(jié)一般由聲母和韻母兩部分組成,其韻母主要以元音為主,而元音是樂音,“因此現(xiàn)代漢語的音節(jié)比較別的語言,讀起來最為響亮悅耳”[1]。其次,漢語每個(gè)音節(jié)都有一定的聲調(diào)。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有四個(gè)聲調(diào),即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這四個(gè)調(diào)類在韻文中則分為平聲和仄聲兩大類,平聲包括陰平和陽平,仄聲包括上聲和去聲。這種獨(dú)特的聲調(diào)決定了漢語音節(jié)自身的平曲抑揚(yáng),使由此匯成的語流呈現(xiàn)音響高低變化的狀貌。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漢語特別關(guān)注自身的語音層面,有時(shí)候?yàn)榱苏Z音上的美感,不惜破壞語法,扭曲詞性詞義”,“對音樂性的追求這一傳統(tǒng)已經(jīng)積淀為一種民族文化心理,以至在許多時(shí)候我們必須從形而上的角度去面對這一語言現(xiàn)象”。[2]因而,教師應(yīng)當(dāng)引領(lǐng)學(xué)生關(guān)注并利用漢語的音樂性特點(diǎn),提升學(xué)生語言的感悟及運(yùn)用能力。
一、關(guān)注平仄,追求唇諧
長期以來,漢語社會集團(tuán)形成了講究平仄的傳統(tǒng),好多熟語和習(xí)用的成句都是平仄和諧的。如大多數(shù)雙音節(jié)的縮寫詞,像枚馬(枚乘與司馬相如)、元白(元稹與白居易)、韋柳(韋應(yīng)物與柳宗元)等,詞序主要考慮的是先平后仄的順序,并非是按照兩個(gè)詞素所代表的人物的特征排列的;再如,在漢語四音節(jié)詞中,符合平平仄仄順序的詞最多(占隨機(jī)抽取的400例中的178例),符合仄平仄仄(最接近平平仄仄的語感)的詞占第二位(400例中的77例)[3]。也因?yàn)槿绱耍藗儾耪f“張三李四”,不說“李四張三”,說“油鹽醬醋”,不說“醬醋油鹽”。當(dāng)然,并列詞語的詞序排列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漢民族尊卑有序的民族心理等(如“父母”“大小”“干群”等),不過平仄關(guān)系顯然是其主要考慮因素。此外,古典詩歌就更是追求平仄和諧的代表性文字了。這就使人們形成了一種語感,一種心理定式:平仄不協(xié)調(diào),讀起來拗口,聽起來別扭;平仄有規(guī)律,讀起來上口,聽起來舒服熨帖。在語文教學(xué)中,教師要關(guān)注并充分利用這些內(nèi)容,讓學(xué)生多讀多體會,從而形成這樣的語感和心理定式。古人強(qiáng)調(diào)“讀書百遍”,不僅僅是“其義自見”,還有確保識記于心、諧于唇吻、永不會誤讀的功用。
二、關(guān)注聲韻。追求耳順
漢語獨(dú)特的音節(jié)結(jié)構(gòu)及音節(jié)多義性使得其聲韻組合的規(guī)律性很強(qiáng),“構(gòu)詞中的雙聲、疊韻、疊音,還有詞的重疊及押韻、反復(fù)、回文、頂針等辭格的運(yùn)用,都可形成漢語音列上音色上異同相間回環(huán)往復(fù)的聲韻美”[4]。如《再別康橋》,其艷美而凄惘情感,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聲韻傳遞出的,“《再別康橋》給人的第一個(gè)印象是語言的音樂美”[5]。首先,此詩首節(jié)三處使用了疊詞“輕輕”,末兩節(jié)三處用了“悄悄”。“輕”和“悄”本身就有柔和的音樂感,加上重疊,就更顯細(xì)膩纏綿。其次,整首詩大量使用雙聲疊韻,如艷影、榆蔭、清泉、蕩漾、青荇、招搖、斑斕、別離等,創(chuàng)造出紛至沓來的音樂效果,充分表現(xiàn)了作者的一腔柔情和不盡思念,渲染出全詩的情感基調(diào)。最后,這首詩每一節(jié)各自押韻。第一節(jié)押[al]韻,第二節(jié)押[ang]韻,第三節(jié)押[ao],第四節(jié)押[ong]韻,第五節(jié)押[e]韻,第六節(jié)押[lao]韻,第七節(jié)重復(fù)第一節(jié)[al]韻。每節(jié)首句不入韻,為次句換韻創(chuàng)造條件。節(jié)內(nèi)隔句押韻,每一節(jié)詩內(nèi)部韻律和諧,讀來有音樂美感,而每節(jié)換韻又造成一種參差錯落感,曲折地表達(dá)了詩人內(nèi)心溫馨而凄美、充實(shí)而失落的難以言傳的復(fù)雜情感。第一節(jié)和最后一節(jié)在用韻上的回環(huán)復(fù)沓,營構(gòu)了一種悠遠(yuǎn)、悵惘、醇厚的氛圍,表現(xiàn)了依依惜別的深情,增強(qiáng)了詩歌的表現(xiàn)力。
重聲疊韻詞在漢語中占有相當(dāng)大的數(shù)量,聲韻的和諧已經(jīng)成為漢語構(gòu)詞的一條十分重要的規(guī)則。“由聲韻律構(gòu)成的內(nèi)在和諧不僅是中國詩歌追求的效果,同時(shí)也已經(jīng)滲透到了漢語散文的節(jié)奏甚至是日常口語的節(jié)奏當(dāng)中。”[6]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其描寫月下荷塘景色的段落就堪稱重聲疊韻詞運(yùn)用的典范: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diǎn)綴著些白花,有裊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fēng)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yuǎn)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shí)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shí)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fēng)致了。
在這短短的二百多字中,作者一連使用了九個(gè)重聲疊韻詞(曲曲折折、田田、亭亭、層層、粒粒、星星、縷縷、密密、脈脈),三個(gè)重聲詞(裊娜、仿佛、渺茫),兩個(gè)疊韻詞(零星、宛然)。如此密集地使用重聲疊韻詞,不能不說是作者為追求音韻上的動聽而刻意為之。此外,從這些詞的聲音上來看,多為齊齒呼、撮口呼的詞,這也于聲音上造成了一種靜謐、欲吐又不能盡意的感覺。在語文教學(xué)中,碰到這樣的美文,教師除了引領(lǐng)學(xué)生通過文字的意義領(lǐng)略作者構(gòu)筑的物象世界美以外,還應(yīng)多引領(lǐng)學(xué)生通過文字的音韻體味作者構(gòu)筑的聲音氛圍美,否則學(xué)生只能是欣賞到一個(gè)“悄無聲息的物象或內(nèi)心世界”。
三、關(guān)注發(fā)音,追求意合
漢語的音樂性,不僅表現(xiàn)為悅耳動聽,還在于它的發(fā)音、節(jié)奏與發(fā)音者的心情相契合。《文心雕龍》說:“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dú)狻!贝笾乱馑紴椋袈稍揪褪歉鶕?jù)人的發(fā)聲,人的發(fā)聲符合五音,本于生理機(jī)構(gòu)。也正因?yàn)榇耍叭饲榈南才罚驃^或郁,為求宣情達(dá)意,在發(fā)音時(shí),借著喉牙(鄂)舌齒唇諸官能姿勢的輔助,造成發(fā)音氣流的委直通塞,表現(xiàn)出清濁、高下、疾徐不齊的聲音,賴此聲音,以宣達(dá)其奮郁驚喜的情緒。所以在五音之中,不同的音質(zhì),自能表現(xiàn)不同的情感”[7]。這一點(diǎn),古詩文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葉紹翁的《游園不值》,第一句“應(yīng)憐屐齒印蒼苔”,前五個(gè)字都屬齊齒呼,讀起來整句聲音纖細(xì),這正與園子靜謐的環(huán)境氛圍相契合;第二句“小扣柴扉久不開”,后面三個(gè)字中的“久”,發(fā)音時(shí)須先齊齒后撮口,頗為費(fèi)力,后面又緊跟著一個(gè)撮口呼的“不”,兩字連讀就更加蹇阻,這也正是柴門長時(shí)間不開,作者尋找春天的迫切心情受阻的心態(tài)寫照。
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中,這種例子也不少,如上面提到的《再別康橋》《荷塘月色》。下面再從中學(xué)教材中擷取兩個(gè)例子。如舒婷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我是你額上熏黑的礦燈,照你在歷史的隧洞里蝸行摸索”句中最后四字,“蝸”“摸”韻母為“o”,“索”韻母含有“o”,按照《文心雕龍》的觀點(diǎn),這當(dāng)屬于“疊韻雜句而必睽”(意思是說兩個(gè)疊韻字隔雜句中兩處,念起來一定別扭),這種聲音上的別扭造成的發(fā)音不暢,只有與祖國在“歷史的隧洞里”艱難前行的意象結(jié)合起來,才能予以合理的解釋。再如汪曾祺的《葡萄月令》,段落結(jié)尾的收字幾乎很少用開口呼,而多用合口呼、撮口呼與齊齒呼,如雪、音、里、了、的、綠、住、著、肺、呢、片、須、粒、面、色、子、禿、土等,“這種語音上的安靜,實(shí)際上正是作者對植物生長狀態(tài)的自然傳達(dá)”[8]。
聲音與情意的這種契合關(guān)系,逐漸積淀就會形成心理定式和語感,比如人們往往覺得細(xì)弱的發(fā)音比較婉約,宏大的發(fā)音比較豪放,像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和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就是典型的代表。這一點(diǎn),古人其實(shí)早有覺察:“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fēng)殘?jiān)隆粚W(xué)士詞,須關(guān)西大漢,(執(zhí))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俞文豹《吹劍錄》)[9]可惜后人多本末倒置,誤以為這是在談兩位詞人的風(fēng)格差異,從而忽略了它們音響差異的事實(shí)。《雨霖鈴》這首詞,去掉標(biāo)點(diǎn)共一百零三字,但其中有近四十字是由舌、齒、唇形成的氣流較細(xì)弱發(fā)音的字,如蟬、凄、切、驟、雨、歇、緒、處、舟、催、執(zhí)、競、語、噎、去、楚、情、自、清、秋、節(jié)、今、酒、醒、此、經(jīng)、是、辰、景、虛、設(shè)、與、說等。這樣的語音,“音細(xì)而若,細(xì)聲細(xì)調(diào),用之來表現(xiàn)離別時(shí)的情形,仿佛聽到了情人問的叮嚀的聲音,看到了離別之際的凄苦,離別后的寂寞與孤凄。齒音的運(yùn)用在此處簡直是再恰當(dāng)不過了,詩聲與諍情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了”[10]。《念奴嬌》則多用舌、鼻、喉形成的氣流較強(qiáng)洪亮發(fā)音的字,如大、東、浪、淘、古、風(fēng)、邊、道、國、郎、亂、空、濤、拍、岸、江、山、畫、豪、想、公、當(dāng)、年、談、故、多、華等。這樣的語音,用來展現(xiàn)長江非凡的氣象,英雄豪邁的氣概,作者豁達(dá)的胸懷,亦非常貼切。
以上三點(diǎn),基本都是筆者在中小學(xué)聽課時(shí)的一些思考和感悟。總體上感覺,大多數(shù)教師極其欠缺漢語的音樂性特點(diǎn)相關(guān)的知識。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筆者認(rèn)為不在于教師,主要在于語文課程的建設(shè)者。語文課標(biāo)雖然呼吁“特別注意漢語言文字的特點(diǎn)”,但對其特點(diǎn)和規(guī)律卻毫無闡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gè)嚴(yán)重的缺失。靠廣大一線教師個(gè)體自覺地去捕捉漢語言文字的特點(diǎn)和規(guī)律,這顯然是不應(yīng)該的,也是不可能的。語文課程建設(shè)者理應(yīng)承擔(dān)起這一重?fù)?dān)。這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不信請看我們的中小學(xué)語文教材,很多選文的語言文字并不典范,甚至是有問題的。隨便舉一例,某版本小學(xué)語文教材中有一篇課文叫《魚游到了紙上》,其第一段第一句話,“我喜歡花港,更喜歡‘泉白如玉’的玉泉”,從音樂性的角度來說,顯然不好:兩個(gè)“玉”字讀起來是多么的拗口。按照沈約的說法,這是典型的八病之中的“正紐”,即一句之中隔字同音。這種音韻的不協(xié)調(diào),從全文來看,顯然不是刻意為之,而是因?yàn)樽髡呷狈Ρ匾臐h語音樂性感覺。這樣的文章,無論是教材編者還是廣大一線教師,都還把它當(dāng)作典范的文章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可想而知我們對漢語音樂性的感覺已經(jīng)遲鈍到什么程度了。這一點(diǎn),古代的蒙學(xué)教材要比我們做得好,如“三百千”,可稱作利用漢語音樂性特點(diǎn)的典范。我們應(yīng)該好好研究,好好學(xué)習(xí)才是。
最后聲明一點(diǎn):漢語的音樂性特點(diǎn)肯定不止本文談的這些,但囿于筆者的學(xué)識只能談到這個(gè)程度,其中還尚且存有不妥之處。如能引起應(yīng)有的注意,那自當(dāng)是不勝欣喜。
參考文獻(xiàn)
[1]鄭福田,漢語新詩的形式美與現(xiàn)代漢語的特點(diǎn)[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文史哲版,1991(5)
[2][6]泓峻,漢語音樂性潛質(zhì)及其在現(xiàn)代文學(xué)語言中的失落[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漢文版,2006(3)
[3]賀國偉,漢語詞語的產(chǎn)生與定型[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219~227
[4]吳潔敏,論漢語節(jié)奏規(guī)律[M],廣播電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8(1)
[5]尤敏,讀徐志摩的《再別康橋》[J],名作欣賞,1980(1)
[7]黃永武,中國詩學(xué):設(shè)計(jì)篇[M],北京:新世紀(jì)出版社,2012:144
[8]汪政,何平,解放閱讀——文學(xué)批評與語文教育[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1:174
[9]轉(zhuǎn)引自唐圭璋等,唐宋詞鑒賞辭典:唐、五代、北宋[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322
[10]吳果恒,“形式美”在高中古詩文教學(xué)中的效用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xué),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