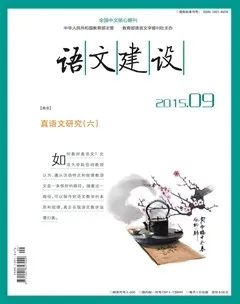曾國藩的語文教育思想
曾國藩(1811-1872)是晚清重臣,一生的主要工作是為政做官,沒有教過語文,但他語文修養(yǎng)深厚,詩和古文的水平很高。對此他非常自信:“吾作詩最短于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1]“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2]1908年,林舒(1852-1924)編出了當時影響最大、使用最廣的《中學國文讀本》,其中第二冊收本朝(清朝)文,全冊共有文章30篇,曾國藩的作品就占16篇。[3]人已離世,權力不復,當時學界這么認可,雖與個人偏好有關,但也確能說明曾氏語文造詣之深,成就之大。曾國藩雖沒有專門從事過語文教育工作,但他有科舉功名,是過來人,知道學習內容的輕重主次、學習方法的快慢巧拙、學習目標的遠近虛實,應該可以稱得上經驗豐富。在《曾國藩家書》中,充滿著語文教育的智慧。學習曾國藩的語文教育思想,對完善今天的語文教育內容和方法、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本文將從學習目的、學習內容、學習方法三個方面予以述評。
一、學習目的:進德修業(yè),學做圣賢
曾國藩說:“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4]讀書的目的在用,在有大用,完善自身,澤及黎民。不注重學以致用,即使能文善詩,亦不過牧豬之奴。只有達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能為國家人民造福,書才沒白讀。學習目的是學習的方向,它保證學習行為朝著既定的正確道路前進,不偏不倚。目的正確,在向目的奮斗時就不會浪費時間和精力,保證效率最大化。曾氏根據當時社會的環(huán)境和自身的條件,根據社會的要求和可能,根據自己對社會發(fā)展趨勢的分析和研判,給自己的子弟制定的讀書目的,近中期是進德修業(yè),最終目標是學做圣賢。
進德是要增進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只有道德修養(yǎng)達到一定境界的人,百姓才會擁護他,追隨他,支持他,保護他,為他服務,甚至為他犧牲。道德修養(yǎng)不高的人,很難取得群眾的信任。道德修養(yǎng)很差的人,百姓會敵對他,排斥他,避而遠之,甚至消滅他。因此,《大學》八條目中的“正心、誠意、修身”都是講進德的事。曾氏對這一點深有體會。他在創(chuàng)辦湘軍之初,軍隊餉銀需要地方政府配合與支持,但因為他當時的聲望不足以讓別人無條件地慷慨解囊,使他的練軍事業(yè)屢屢受挫,心情十分郁悶。曾氏深知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要性,在家書中常常談到進德的事。他說:“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佚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5]遠離奢、佚、驕,就可能家庭興旺、事業(yè)成功、受人歡迎。平時要嚴格要求,時刻警醒自己。他常常以自身成敗得失諄諄告誡子弟。他自己己亥年在外游歷,接受過別人的人情,深以為悔,自省以后絕“不肯輕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并告誡子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6]
修業(yè)是修習學業(yè),完善學業(yè),在古代主要指讀好圣賢之書。曾國藩認為精通了儒家經典,諳熟歷史,又懂文學,就是業(yè)已修好。業(yè)已修好之人是不愁食祿的。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里仁》)只要業(yè)務過硬、技術高超,這個社會自然有自己的位置。曾氏說:“業(yè)之精不精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yè)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士果能精其業(yè),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yè)之不精耳。”[7]“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系,榜后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后窮經讀史,二者迭進。”[8]考試結果不要太看重,重要的是讀書長知識,修習自己的本領,練就一身非凡武功,就是走遍天下也不用害怕。
學做圣賢是讀書治學的最終目的,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曾氏說:“人茍能立志,則圣賢豪杰何事不可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9]人生需要正確方向,學做圣賢重在品行德操,修習德行完全可以由自己把握,每天都可以做,每件事都可以做,只要時時想著去做,只要處處想著去做,只要心中常常有圣賢,常常按照圣賢的標準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就是學做圣賢。這是一種精神追求,完全超脫了物欲勢利。他說:“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圣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10]人生于世,要有自己的奮斗目標,要有自己的事業(yè)理想,這樣人生才有方向,工作才有動力,活著才有精神支柱。曾氏自己一生就是時時以圣賢為標準,偶有戲言戲動,則在日記中對自己大加撻伐,毫不留情。他平時勤苦努力,對自己要求極其嚴格,雖身居高位,依然勤勉不止,節(jié)儉如寒士。不僅如此,他帶兵“要求湘軍不染惡習”,“嚴禁偷盜、奸淫、搶掠、吸鴉片、賭博、造謠、搬弄是非,盡量不要飲酒”。[11]李鴻章愛睡懶覺,曾國藩競用“李鴻章不到,湘軍全體不許吃飯”的辦法來逼他,從而使李鴻章自此養(yǎng)成勤奮、規(guī)則的好習慣。[12]曾氏去處理“天津教案”,自感可能一死,遺囑兒子“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刻布”[13],對自己要求之嚴,可見一斑。他自己以圣賢的要求為準則,也教育子弟向圣賢看齊。他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yè),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14]做人要做君子,做完人,做偉人。關注天下,心憂萬民,不在意個人得失榮辱,這樣才算“不忝于父母之所生”,才算得上男子漢大丈夫。這是曾國藩自己的人生追求,也是對子弟的要求與希望。這種學做圣賢的思想應該是人生的大境界,足以使人去掉任何私心雜念。一個人如果有了這種人生信仰,即使沒有物質上的成功,他的人生也應該是充實而幸福的。
二、學習內容:重視科舉考試,更重視全面提高
科舉登第,是封建社會一般讀書人的奮斗目標。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上流社會,過著一種衣食無憂的體面生活,光宗耀祖,受人尊重,是古時學子們的理想人生。對讀書人而言,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比通過其他途徑如經商、行醫(yī)等獲得成功要容易,且更易得到社會肯定。曾國藩自己就是走的科舉之路,登第之后做官,然后攀升,如果沒有科舉,他也就不可能有這么巨大的成功。作為過來人和受益者,曾國藩是重視科舉考試的。他在家書中諄諄告誡子弟,要讀什么書,怎樣讀書,才能更好地贏得科舉,如“若夫為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15]。
曾國藩認為對科舉應該有一個正確的科學的態(tài)度,不要死死盯在科舉上。科舉一旦成功,就認為萬事大吉,不用再努力了,甚至喜極而瘋,成為笑話,自不足取;科舉失敗,就萬念俱灰,一蹶不振,甚至剃度為僧,或者自尋短見,當然更不好。曾氏主張眼光應該放高一點,應該看遠一點。科舉是謀生的一種手段,一種比較高級的手段;由科舉成功而做官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比較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科舉不是一切,除了科舉,人生還有很多事,還有很多謀生手段,也還有很多生活方式。人只能利用科舉,不能被科舉困死。他在家書中常常提醒子弟:“吾所望于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悌為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于進學也。”[16]“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fā)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17]“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汩其性靈。”[18]對科舉考試采取既重視又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是曾國藩的境界,也是他的智慧。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動機過于強烈,效果往往不佳;動機適當,效果最好。
曾國藩重視科舉,但不局限于科舉,表現出非同凡響的氣概與胸襟。曾氏認為,長知識、長學問更重要。知識淵博、能力高超,即使科舉落第,也不愁挨餓。他還認為,智商超群的人不應斤斤于科舉,應該有大視野,可以參加科舉,以為自己的奮斗提供便捷;但是科舉之外,還應想得更多,看得更多,讀得更多,做得更多,以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和家國夢想。智商一般的人雖然也應多讀書,但把最高目的放在科舉上也就算了,因為沒有更多能耐做其他事情。“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為有大志者言之。”[19]“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為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20]追求有分別,人生目標有不同,完全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定。
三、學習方法:先專后博,既巧且恒
為了使弟子學得正,學得快,學得好,曾國藩常常不厭其煩地對他們進行學習方法的教育。
1 先專后博,打基礎與廣視野相結合
曾國藩家書中很多地方都談到讀書做學問要專。“求業(yè)之精,別無他法,日專而已矣。”[21]“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并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22]
光有精專還不行,還應該廣博。只有在廣博基礎上的精專,才是有分量的。曾氏說:“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耽擱問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23]曾國藩把“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看作“為學四要事”之首[24],可見他對旁通博覽的重視程度。
2 既巧且恒,尊重規(guī)律和勤奮持恒相結合
巧是指巧妙的方法,恰當的方法;恒是指有恒心,有毅力。事物的發(fā)展都有自己的規(guī)律,掌握了事物的規(guī)律,并按規(guī)律辦事,就是巧。做事情刻苦努力,絕不輕言放棄,能夠堅持不懈,能夠奮斗到底,就是恒。
語文學習主要包括閱讀、寫作和書法等內容,在這幾方面曾國藩對子弟都有細致入微的教導,我們重點提一下他的閱讀方法。閱讀方法是曾國藩談得最多的語文學習方法。他非常重視精讀,指出:“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25]對摘錄記疑,曾國藩也特別重視。他認為讀書要認真用心,要做摘錄,記疑問,寫感想,談體會。這樣才能理解得深透,能出能人,形成自己的獨得之見,為自己今后做學問打基礎。曾氏認為,當朝大儒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讀書雜志》《經義述聞》就是用這種方法日積月累慢慢寫成的。[26]因此,他建議子弟也用這種方法。他說:“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宋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朱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為辯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于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27]葉圣陶先生也說過:“終身寫作讀書筆記,便將受用無窮,無論應付實務或研究學問,都可以從筆記方面得到許多助益。”[28]引可謂英雄所見相同。
曾國藩也非常重視勤奮持恒。他說:“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為主。”[29]“諸弟每日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須帶在身邊。”[30]“二十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31]“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恒,每日臨一百字,萬萬無問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32]蘇軾在《晁錯論》中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沒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沒有堅忍不拔的意志,是做不成事的。在正常情況下,非智力因素永遠比智力因素重要。意志力,不僅讀書干事業(yè)需要,日常生活也不可或缺。正因為此,曾國藩教子弟不忘一個“恒”字。
曾國藩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了,但他的語文教育思想并沒有過時,對我們今天的語文教學仍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2][5][6][7][8][10][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9][30][31][32]曾國藩,曾國藩家書[M],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67,245,153,273,49,22,82,52,64,74,230,245,64,64,49,49,138,98,67,23,77,58,60,67
[3]洪宗禮等,母語教材研究:10[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53
[4][9]曾國藩,曾國藩家書[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50,107
[11][12][13]馬東玉,曾國藩大傳[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15,90,91
[25]張隆華,曾仲珊,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401
[28]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