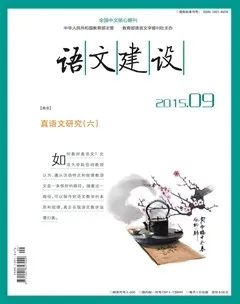從象形特點和構形規律看漢字教學策略
漢字和埃及圣書文字、古代蘇美爾文字、原始埃蘭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屬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都經歷了由圖畫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過程。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這些古老文字有的廢止,有的變成拼音文字,而唯有漢字沿用至今。
與拼音文字相比,漢字的基本特點是以象形為基礎的表意性。漢字的構形規律則以象形為基礎,繁衍出指事、會意、形聲。任何一種文字的教學都要遵循其自身特點和規律,漢字教學也如此。
現存最早的漢字是產生于殷商時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作為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漢字不僅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也是歷史文化信息的載體。
漢字教學的基本目標是掌握記錄漢語的文字符號,而宏觀目標應該是體認漢字文化。體認漢字文化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基本內容。
下面基于漢字象形特點和構形規律談談漢字教學策略。
一、從象形入手,理解漢字特征
漢字以象形為基礎,從象形入手是漢字啟蒙的鑰匙。傳統語文教學在這方面有成功經驗,例如,清代王筠提出正篆比照識字法:“識字,必裁方寸紙,依正體書之,背面寫篆;獨體非篆不可識,合體則可略。”(《教童子法》)正篆比照識字法強化了漢字象形特征。小篆基本保留了象形特征,可以由字形推知字義,這種做法有利于兒童體認漢字象形特征。從象形入手,增強了漢字教學的直觀性,符合兒童的心理特點,能夠引發兒童的學習興趣。
確立漢字象形意識,有助于正確理解字義,避免寫錯別字。形義聯系意識淡漠,缺乏根據字形推知字義的直覺,是寫別字的根本原因。
確立漢字象形意識,也有助于理解字的本義或基本義,區別古今義,這是學習古詩文要特別注意的。僅就偏旁而言,例如“月”除與月亮有關,還表示人體部位,是“肉”的變形,故“肢”“股”“腿”“腳”以“月”為意符;“阝”是“山”的變形,古代建筑依山而建,故“都”“郭”“陵”以“阝”為意符;“灬”是“火”的變形,故“然”是“燃”的本字,“蒸”“煮”“烹”以“灬”為意符,等等。“月字旁”“耳刀旁”“四點水”之類的稱謂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甚至“水火不相容”。這些常識在識字伊始就應該解釋清楚。據此連類而及,可進行字理識字、字族識字。
二、理解造字方法。掌握構形規律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規定的課程內容不包括漢字造字法和漢字形體演變常識,但教學中這兩項內容不可或缺。二者作為基本常識列入課程內容,并不會加重課業負擔,反而會提高教學效率。
前人將漢字造字方法總結為“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前四書為造字方法;轉注、假借屬用字方法,與造字無關。學界認為,造字法不是在造字之前就有的,而是后代文字學家歸納概括出來的。這種說法未必妥當,應該說造字法是在造字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體現著漢字構形規律。
造字方法作為啟蒙教育課程內容自古亦然。班固《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慎《說文解字·敘》:“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日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日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日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日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搠,武信是也。五日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這是漢代文獻記載,“六書”之說最早見于《周禮·地官》,從略。
古代啟蒙伊始教“六書”透露了兩點信息:一是掌握造字方法,二是分類識字。前者體現漢字構形規律,后者體現漢字學習規律,二位一體。
理解了漢字造字方法,就掌握了漢字構形規律;掌握了漢字構形規律,就具備了識字類推能力,從而實現批量識字。這就是漢字字理識字和字族識字的依據。
新加坡漢字教學有一種“造字游戲”,其依據當然是造字法。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漢字聽寫大賽”中,賽手憑借造字法臨場發揮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當前的漢字教學從中可以獲得啟發。
三、了解形體演變。獲取文化信息
上面提到《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規定的課程內容不包括漢字形體演變常識,但了解漢字形體演變常識對于理解漢字本義、獲取文化信息確有必要。
方塊漢字類似信息集成塊,是歷史文化的信息載體。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以形表意,幾乎可以“望文生義”;而占漢字絕大部分的形聲字又具有音義二元結構特點,其意符是信息儲存體,聲符是信息識別體。方塊漢字的信息載體功能是線性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19世紀末,甲骨文的出土為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便是佐證。
了解漢字形體演變的理由有三:強化漢字象形特征,有助于引導學生從字形推知字義;由漢字演變過程,了解漢字發展軌跡;從早期象形字體中窺見文化信息。漢字教學枯燥乏味,與漢字文化意識淡漠不無關系。
漢字形體演變大體分為七個階段:甲骨文,殷商時代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金文,周代鑄刻在銅器上的文字(又稱“鐘鼎文”);篆書,有“大篆”“小篆”之分,大篆始于周,小篆始于秦;隸書,始于秦,而盛于漢,故稱“漢隸”;草書,漢隸的潦草寫法;楷書,由隸書演變而來,取代隸書而通行,亦稱“真書”“正書”;行書,成于魏晉,介于楷書與草書。
在漢字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有兩次重要變革。第一次變革是大篆變小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字形體不一,“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朝統一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大篆由小篆“省改”而成,以省變為主,由繁到簡。第二次變革是小篆變隸書,稱為“隸變”。大篆變小篆仍保留了明顯的象形面貌,而“隸變”則拋棄了“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原則,象形面貌消失,變成了純粹的抽象文字符號。“隸變”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這兩次變革呈現了漢字發展軌跡:由繁到簡,由具象而抽象。
今天我們面對抽象符號系統的漢字時,仍需依據字形區分字義。因為漢字畢竟是以象形為基礎的表意文字,離開了這一點就會失去識寫漢字的根基,漢字文化的歷史信息也就不復存在了。
作為文化傳承,在漢字教學中,了解漢字形體演變,是體認漢字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其教學手段也未必如想象的那么繁難,現代傳媒技術已經可以提供較為豐富的課程資源,如字體轉換軟件、影視資料、圖片拓本等。字體比照可以增強漢字教學的形象性和直觀性,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四、從獨體到合體。遵循漢字學習規律
識字先獨體,后合體,先易后難,是傳統語文教學的成功經驗。例如,清代王筠編著的《文字蒙求》,利用漢字構形規律,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分類編排。漢字繁衍是以象形為基礎的,由獨體(象形、指事)到合體(會意、形聲)體現了漢字構形規律,漢字教學理應以此為基本途徑。
當代漢字教學,在此基礎上已有發展,例如字理識字、字族識字等。這些做法有利于理解漢字的象形特征以及構字規律,提高識字寫字效率。
2009年教育部、國家語委發布了《現代常用獨體字規范》。該規范制定的原則是:尊重字理、從形出發、立足現代、面向應用。確定現代常用獨體字的規則是:字形結構符合字理和獨體字定義的漢字;符合獨體字定義的草書楷化的簡化字;交重結構,不能拆分的漢字。依據以上規則,在現代漢字的范圍內確定了256個現代常用獨體字,形成了《現代常用獨體字表》。文件指出該規范適用于識字教育。教師可據此進行漢字教學。
五、認寫分離。遵循認知心理
古代識字教學與寫字教學分而治之,作為兩個相對獨立的教學系統。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不讓寫字影響識字的進度,并進而影響閱讀;二是強化書法教育。
古代蒙學課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計集中識字約2000個,這是大約一年的識字量。有了這個基礎,然后開始閱讀。讀物分為兩類:道德訓誡類,如《弟子規》《太公家教》《昔時賢文》等;掌故知識類,如《龍文鞭影》《幼學瓊林》《名物蒙求》等。接下來才是《四書》《五經》;配合讀經,閱讀散文故事,如《書言故事》;讀詩,如《千家詩》。此外練習屬對,則有《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由上述可見,古代大約用一年的時間集中識字,然后就開始閱讀。集中識字的目的顯然是盡快進入閱讀。
古代寫字與認字不僅不同步,甚至不統一,是兩個完全分離的系統。古代習字從“上大人孔乙己”寫起,由簡單到復雜,并且有嚴格的步驟:第一步寫大字,先描紅,描仿影,次寫“米”字格,最后才臨帖;在大字寫得有點基礎后,第二步才寫小字。對此,張志公先生評論道:“不讓識字和寫字互相干擾,互相牽制;教兒童寫字從有依傍(把腕、描紅、描影、臨帖)到無依傍;先大后小:這三條顯然是跟漢字的特點相結合的。”[1]
為什么識字和認字要分而治之?這是方塊字的認知心理決定的。記憶有兩個檢查指標,一個是再認,一個是再現。就文字而言,前者是認讀,即看到一個字能否把它識別出來;后者是聽寫,即聽到一個字能否把它復現出來。漢字是方塊字,一般說來,再認的難易和筆畫的多少沒有明顯的對應關系。識別一個字往往不需要看清所有筆畫,只要能抓住這個字的大致輪廓和特征就可以了。再現則不然,要求把字的結構和每個筆畫都準確地復現出來,頭腦中這個字的表象只是大致的輪廓和特征就不夠了。筆畫的多少會直接影響再現的難易。
換言之,以象形為基礎的方塊字,每一個字符就像一個“臉譜”,能分辨其大致輪廓和特征即可識別;而要畫出這個“臉譜”則必須再現所有的細節。漢字為什么可以難易混雜地“集中識字”,而寫字卻要由簡單到復雜?道理就在這里。
現行漢字教學采用隨文識字、認寫基本同步策略,是否切合漢字認知心理特點值得考量。僅僅“多認少寫”是不夠的。直到六年級才累計認識3000字,進度是否慢了些?
六、讀《水滸》,識字何止3500
傳統語文教學主張識字與寫字分而治之。如果把這一策略理解為化解識字與寫字難以同步的矛盾,還是不夠的。識字目的在于閱讀,閱讀目的在于拓展視野,拓展視野的目的在于精神成長。如果這樣推論起來,識字實在是啟蒙伊始。如果從“啟蒙”意義衡量識字的價值就非同小可了。識字價值直接指向閱讀,打開蒙童認知世界的窗口。盡快多認字,可以在兒童記憶的最佳“窗口期”打開閱讀窗口,滿足兒童學習興趣,豐富兒童精神生活。識字是閱讀的基礎,反過來想,閱讀是否可以促進識字呢?
如果把一本有趣的好書放在兒童面前,《格林童話》或《伊索寓言》,識字就會成為兒童主動的學習行為。如果是一本《魯濱孫漂流記》或《海底兩萬里》,識字3000自然不成問題。如果是一本《西游記》或《水滸》,識字量又何止35007(九年級累計識字量)一個二年級的學生在暑假讀一本《水滸》是不成問題的。
慣性思維是當識字量達到足夠積累時才可以閱讀,其實不然,閱讀是擴大識字量最迅捷、最有趣、最有效的識字方式。在兒童初步感知漢字構形(造字)規律后,識字已經近乎游戲心理,主動識字是兒童自發的心理需求。俗話有“不識文字讀半邊”,絕大多數漢字是形聲字,根據形聲特點猜讀是包括成人在內的一種識字經驗。據兒童學習經驗,經過一、二年級初步的識字體驗(而不是識字量),到三年級,兒童已經能夠借助工具書,在濃厚閱讀興趣的驅使下開始獨立閱讀。
七、學習書法。體認漢字文化
漢字以象形為基礎,故有“書畫同源”之說,虛實感、寫意性是其文化通約。盡管線性拼音文字也有書法,但與方塊漢字不可同日而語。漢字書法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在中國諸多藝術種類中,書法是最能體現漢族獨特人文氣質的藝術形式。
從古至今,中國書法對鄰國文化一直影響廣泛。日本大約有兩三千萬書法愛好者,也就是說五六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練書法的。能舉辦個人書法展覽、出作品集的人,全日本大約100萬人之多。書法的極大普及,與日本人重視書法教育密切相關。日本中小學校都開設書法課,小學三年級開始學書法,到初中畢業,六年時間足以打下書法知識和技法的堅實基礎。
有關數據表明,中國青少年字跡潦草,對書法興趣淡漠,不如日本青少年。日本書法學者西島慎一(專門出版書法類書籍的二玄社原主編)認為,其主要原因是文化斷代了重拾不易,另一個原因是電腦的普及嚴重沖擊了書法普及。現階段恢復書法教育,不僅是審美教育策略,更是民族文化傳承的迫切任務。《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對書法教學做出明確要求,從第二學段開始學寫毛筆字,到第四學段臨摹名家書法,體會書法的審美價值;2013年教育部又頒發了《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指出書法教育旨在“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書法被設置為一門相對獨立的課程。
參考文獻
[1]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