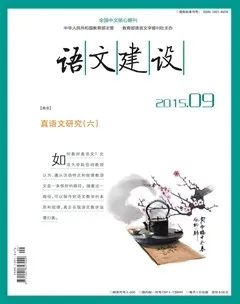《竇娥冤》的文本縫隙及文學意義
關漢卿的《竇娥冤》雜劇是中國古典戲曲的奠基之作。不過,這部雜劇在情節設置、人物塑造等方面也存在明顯疏漏。元代戲曲初創,雜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為之”[1]。作品中“遺漏的或者錯誤的地方”[2],新批評稱之為“文本縫隙”。“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背后一定有一個完整的世界——但是作家沒有能力把這個模型全部寫出來”[3],就形成了所謂的文本縫隙。文本縫隙里“隱藏了大量的密碼”,幫助我們“完善這個故事”[4]。《竇娥冤》的文本縫隙有哪些,它們的意義、功能何在?文本縫隙對《竇娥冤》的流傳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們的存在是否影響劇本的藝術表現?如何對文本縫隙進行有效解讀,是否該重新定義《竇娥冤》在中國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本文擬圍繞以上問題,進行再思考。
一、疏漏與瑕疵:《竇娥冤》雜劇的文本縫隙
1 情節設置的疏漏
《竇娥冤》的文本縫隙首先表現為情節設置的疏漏。為霸占竇娥,張驢兒在羊肚湯中下毒,不料張父誤食羊湯,毒發身亡;張驢兒欲與竇娥私了,竇娥不從,遂誣陷竇娥藥死公公,與竇娥對簿公堂;公堂之上,太守桃杌嚴刑拷打,為救婆婆,竇娥含冤認罪,被問斬刑;刑場上,竇娥發下三樁誓愿,爾后,三樁誓愿一一應驗。這是《竇娥冤》的核心情節。
一般認為,竇娥蒙冤的原因是桃杌受賄。這種看法有一定的依據。第一,桃杌出場即自稱“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見有人來打官司,他竟然跪拜,宣稱“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第二折),活脫脫一個貪官的形象。因此,推測桃杌收受張驢兒賄賂,有意冤殺竇娥,與他的出場形象相契合。第二,竇娥冤情昭雪后,曾控訴官府“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她還叮囑父親“從今后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第四折),這些唱詞都暗示桃杌等貪官污吏是致使她蒙冤的罪魁。第三,竇娥臨刑前指天罵地:“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第三折)由于桃杌這樣的貪官顛倒黑白,致使惡人橫行,好人命舛,因而竇娥責備天地“怕硬欺軟”,“順水推船”。這樣理解在情感上更有沖擊力和爆發力。
不過,劇本并沒有桃杌受賄的細節,劇中還有些情節與以上推測相矛盾。比如,竇天章為竇娥平反冤獄時,稱桃杌為“糊突的官”,桃杌最后的罪名是“刑名違錯”(第四折),并非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再如,根據劇情,蔡婆婆家中“廣有錢物”(第一折),張驢兒父子似為無業游民,如果行賄,竇娥一方在財力上應該更占優勢。桃杌是否收受了張驢兒的賄賂,他為什么會偏幫張驢兒、枉法裁判,竇娥冤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劇本一直沒有交代清楚,這是《竇娥冤》情節設置的一個主要疏漏。
2 人物形象的瑕疵
與情節設置的疏漏相關聯,《竇娥冤》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出現了瑕疵。
先來看桃杌。桃杌是造成竇娥冤獄的元兇之一。不過,桃杌在劇中的形象一直模糊不清。作者為桃杌貼上了貪官的標簽,桃杌一出場就進行了解嘲式的自白與表演。不過,由于劇本并未交代桃杌受賄的細節,因此劇中的桃杌只能算是個昏官。“關劇點出縣官貪財,但在審案中卻只寫昏庸。”[5]這樣,桃杌形象的實際意義與作者的創作意圖發生分裂。
再來看竇天章。竇天章在劇中具有雙重身份:父親加清官。不過,作為父親,竇天章顯得不近人情。十六年前,為了進京趕考,他將七歲的女兒竇娥出賣;十六年后,與竇娥重逢,得知罪人即為女兒端云,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竇娥“辱沒祖宗世德”,“連累我的清名”。作為清官,竇天章也有些名不副實。他身任“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自稱“廉能清正、節操堅剛”,“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但他似乎并不比其他官員高明,在他眼中,竇娥的冤案也只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問結了的”案件,“不看他罷”(第四折)。若不是竇娥鬼魂顯靈,這一案件很可能冤沉海底。因此,不少學者認為“竇天章就是個蒼白無力、概念化的形象,思想意義與藝術技巧兩無可取”[6]。
二、補足與完形:《竇娥冤》雜劇的現代解讀
1 《竇娥冤》改編本的解讀與創作
現代以來,關劇的疏漏與瑕疵已成為人們共識。《竇娥冤》改編本眾多,劇作家一直試圖在劇本的再創作中對關劇的文本縫隙予以彌補。
關于桃杌枉法的原因,不少劇本明確交代是桃杌受賄。馬健翎的秦腔《竇娥冤》專寫了一場《受賄》,在審案前張驢兒向太守的心腹行賄三個元寶,明確寫出竇娥遭冤斬并不是太守糊涂,而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造成的。\"’李約祉和張茂亭的秦腔《竇娥冤》也寫了縣官審案前接受張驢兒十兩銀子。[8]此外,周奇之的豫劇《竇娥冤》、晉南蒲劇院的蒲州梆子《竇娥冤》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寫出縣官受張賄賂。[9]
為了增強桃杌受賄的合理性,有些劇本還改寫了蔡婆婆與張驢兒的境遇。比如周奇之的豫劇本子將蔡婆婆改為小康之家,靠紡織勞動為生,張驢兒父子則是因吃喝嫖賭而傾家蕩產的破落地主。[10]陳牧的改編本則改成張驢兒從蔡婆婆處訛詐了三百兩銀子行賄,蔡婆婆將三問房屋變賣,后來只能在前街關帝廟內寄住。[11]此外,還有劇本將張驢兒誣告而勝訴的原因寫成他和衙役頭子有勾搭,縣官也認為這個街面上的混混兒可能對他有用處,故而枉法裁判。[12]
通過改編本的再創作,劇作家對《竇娥冤》做出了各自的解讀。一方面,認識到關劇的杰出成就,大多數改編本保持了原作基本面貌。另一方面,不少改編本也試圖對關劇做豐富和提高的工作。經過改編的處理,《竇娥冤》的文本縫隙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彌補,故事情節在邏輯上更加順暢,人物形象也更加完善。
2 文本縫隙與《竇娥冤》的深層意蘊
與劇作家不同,《竇娥冤》的研究者并不致力于彌補《竇娥冤》的疏漏和瑕疵,他們嘗試通過作品的文本縫隙解讀這部元代雜劇的深層意蘊。近年來,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兩種。
一種是蘇力的法學解讀。北京大學蘇力教授認為,“竇娥之冤與官吏的‘貪污’無關”,“也很難歸結為官吏昏庸無能的產物”。[13]他指出,在竇娥的案件中,張驢兒占有“優勢證據”。第一,死者為張驢兒之父,兒子殺父親的可能性小于竇娥毒殺張父的可能性。第二,公堂上,張驢兒稱蔡婆婆是自己的后母,“大人詳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張,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腳,他養我父子兩個在家做甚么”(第三折),由于張驢兒的陳述有事實支持,因而更加可信。第三,毒死張父的湯是竇娥做的,張驢兒下毒的機會小于竇娥。第四,竇娥為救助蔡婆婆做了認罪陳述,竇娥的自認轉變為她的不利證據。據此,蘇力得出這樣的結論:竇娥的悲劇是元代司法制度的產物,《竇娥冤》的意義在于,“該劇表明,在傳統社會條件下,司法很難處理像竇娥這樣的案件,這種悲劇實際上不可避免”[14]。
另一種是李新燦的社會學解讀。湛江師范學院的李新燦教授對《竇娥冤》做了進一步解讀,分析了《竇娥冤》的“深層意義”。一方面反映了元代社會的司法問題。“即使執法者公正,因為法律自身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法律并不能在任何條件下百分之百地伸張正義,竇娥之類的冤案仍有可能繼續上演,這種并非人為的法律悲劇更具有普遍意義。”[15]另一方面反映了元代女性的悲劇根源。竇娥的悲劇和元代女性的弱勢地位及集體潛意識相關:“蔡婆婆的反常言行凸顯了男權文化壓抑下守寡婦女的精神生活狀態以及她們對于守寡與改嫁的微妙心理,竇娥的突然屈招則出自于她為修來世一次性贖清前世罪孽的潛意識”。[16]
研究者把《竇娥冤》作為元代社會的“完形”,試圖透過文本縫隙解讀元代社會的司法面貌以及弱勢民眾的生存狀態。不過,這些解讀并非作品的文學解讀,文本縫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知識考古學”的對象。
三、虛構與真實:文本縫隙與《竇娥冤》雜劇的文學解讀
1 虛實關系與《竇娥冤》的文學解讀
納博科夫說:“沒有一件藝術品不是獨創一個新天地的……我們要把它當作一件與我們所理解的世界沒有任何明顯聯系的嶄新的東西來對待。”[17]《竇娥冤》創造了一個獨立的藝術空間,這個空間不同于現實空間,它展現的是作者關漢卿的心靈世界。不過,由于創作主體需要以現實世界為素材,將生活中的人物與事件提純、組合、夸張、變形,因此,作品的藝術空間與現實空間又總是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虛實關系成為解讀《竇娥冤》雜劇的關鍵。
第一,人物形象的虛實。
竇娥是關漢卿創造的元代女性形象。他將元代弱勢女性的所有悲劇因素都集中在竇娥一個人身上:父母離喪、丈夫早亡、孀居無子、遭遇流氓欺凌、官吏枉法,最后含冤而死。由于這種創造不是無中生有的捏造,而是對現實的高度濃縮,因而竇娥的形象顯得異常真實,她的苦悶、無助、怨恨、反抗都能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竇娥成為中國文學史中最動人的女性形象之一。
關漢卿在劇中對桃杌進行了漫畫式的描繪,他將元代貪官的特點加以夸張、變形,對貪官群體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判。元代法制昏聵、貪官污吏橫行,桃杌形象有豐厚的生活基礎。不過,由于作者忽略了人物行動細節的刻畫,桃杌成為一個臉譜化的形象。
竇天章由父親和清官兩個形象組合而成。父親竇天章取材于底層知識分子,清官竇天章則是虛構而成。由于在現實生活中竇娥的冤情昭雪幾無可能,關漢卿創造一個清官父親將案件查明。由于清官竇天章完全出于作者的良好愿望,因而這一形象顯得極不真實。此外,兩種身份合二為一,竇天章的父親形象與清官形象還產生了直接沖突:一個貧寒的父親迫不得已離棄女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個金榜題名的父親,十六年不履父親職責則是難以原諒的。
第二,情節的虛實。
《竇娥冤》第一折、第二折講述了一個不幸女子竇娥的故事。她三歲喪母,七歲被父親拋棄,婚后兩年丈夫去世,與婆婆相依為命。流氓張驢兒要霸占她為妻,誣陷她藥死公公。她求助于官府,但貪官桃杌徇私枉法,為救婆婆,她含冤認罪,被判極刑。竇娥的遭遇是元代弱勢百姓都可能經歷的事件,這兩折基本采用寫實的手法。
第三折寫竇娥赴刑。法場之上,竇娥面對湛湛青天發下誓愿:血濺白練、六月飛雪、大旱三年。隨著三樁誓愿一一應驗,竇娥的冤情以震撼人心的方式彰顯在世人面前。由于竇娥沒有任何有效的私立救濟資源,尋求國家救濟又以失敗告終,關漢卿為竇娥創造了一種奇妙的救濟方式——天理救濟。《竇娥冤》第三折是全劇的高潮,這一折采用了浪漫主義的寫作手法,虛構的痕跡最為明顯。
第四折寫竇天章衣錦還鄉,為竇娥平反冤獄。“根據現有的證據來看,沒有人能相信竇娥是無辜的,哪怕是包拯這樣的清官也無法憑空洗雪冤屈;或者是,哪怕包拯對此案有懷疑,他也未必有很大的動力和意愿來重新審理這樣一件已經終結、無法挽回生命的普通小民的冤案。……只有讓竇天章出場,這場申訴才可能啟動,這場冤案才有可能洗雪。因為只有父親才會更關心自己女兒的生前死后的命運,哪怕是死后的名譽;也只有父親才有那種不計成本為女兒昭雪平反的強大沖動和激勵(即復仇本能);同樣,也是只有父親才更可能相信自己親生女兒的訴說。”[18]因此,作者虛構了一個清官父親為竇娥平反冤獄。除了鬼神顯靈等情節之外,第四折基本采用寫實的手法,這一折的虛構特征,尤其是竇天章形象的虛構性常常為人們所忽視。
2 文本縫隙與《竇娥冤》的文學價值
《竇娥冤》的文學價值在于它創造了一個獨立的藝術空間。在這個藝術空間中,作者不僅講述了一個弱女子竇娥的故事,透過具體而微的情節揭示了竇娥悲劇命運的成因,更重要的是,通過竇娥故事的講述,作者抒寫了有元一代弱勢民眾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內心深處的苦悶、彷徨、不平和希望。借助竇娥臨刑前的指天罵地,郁結于人們胸中的憤懣得以宣泄;借助三樁誓愿的應驗,官吏的貪腐、百姓的冤情昭告天下;借助竇娥冤情得雪,善惡有報,正義的理想得以伸張。
由于這個空間遵循的是文學邏輯而不是生活邏輯,由于藝術空間與現實空間的巨大張力,作品中出現了一些疏漏和瑕疵。不過,如果不是這些文本縫隙,或許我們會忽視《竇娥冤》早已抵達的創作峰頂。桃杌,古代四兇之一。作者之所以用桃杌給官員命名,就是為了指出像桃杌這樣的貪官污吏是造成竇娥悲劇命運的元兇。不過,作者在創作時出現了一些疏漏。竇天章的形象瑕疵則揭示出另一組“創作密碼”,關漢卿之所以虛構一個清官父親的形象,“一方面是出于對正義的呼求和渴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觀眾企盼團圓的心理需求”[19],這個看似蒼白無力的竇天章形象正是作者創作意識的集中體現。
宗白華說:“戲曲的目的不是單純地描寫情緒,如抒情文學,也不是單純描寫事實,如敘事文學,他的目的是:‘表寫那能發生行為的情緒和那些能激成行為的事實。’戲曲的中心就是‘行為’的藝術表現……戲曲的藝術是融合抒情文學和敘事文學而加之新組織的,他是文藝中最高的制作,也是最難的制作。”[20]。在雜劇草創時期,關漢卿就能夠有意識地表寫人生,將戲曲創作引向藝術巔峰,這是《竇娥冤》雜劇成為中國戲曲藝術杰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王國維,宋元戲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121
[2][3][4]陳思和,文本細讀在當代的意義及其方法[J],河北學刊,2004(3)
[5][6][9][12]馮沅君,怎樣看待《竇娥冤》及其改編本[J],文學評論,1965(4)
[7][8][10]王衛民,《竇娥冤》與歷代改編本之比較[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3)
[11]陳牧,竇娥冤(改編)[J],大舞臺,1999(6)
[13][14][18]蘇力,竇娥的悲劇——傳統司法中的證據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5(2)
[15][16]李新燦,深層意義恰在于“情節疏漏”處——以陳牧改編本《竇娥冤》為參照[J],江漢論壇,2006(5)
[17]納博科夫,文學講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19
[19]田欣欣,文本細讀與中國文學史教學——以元雜劇為例[J],中國大學教學,2014(3)
[20]宗白華,藝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