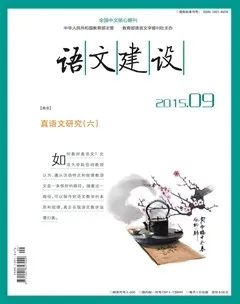當數字和愛戀發生沖突
伯爾的短篇小說《在橋邊》的主題是什么?教參如是說:
小說的主題,在表面上看是愛情,表現愛情對于一個處境堪憂的小人物具有如何強大的精神力量,而深層則是對德國戰后重建中偏重物質而缺乏精神關懷這一問題、以及小人物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的精神狀態的思考。
這樣的概括相當客觀準確。我們現在圍繞小說的具體內容來看看小說是如何對以上主題進行展開的,同時再探索一下伯爾這篇篇幅相當短小的小說又蘊含著什么其他深刻的社會意義。
一、對戰后德國民眾的批評
小說的主人公“我”顯然是個二戰中的傷兵。出于人道主義以及對傷兵的撫恤,政府給“我”安排了一份對于殘疾人來說或許是個“美差”的工作:數一座新橋上每天通過的人數。這份工作對于“我”來說當然無比枯燥乏味,而且“我”也不認同自己的工作具有什么實際意義,將其看作“毫無意義的空洞的數目”。
那么,從當時德國政府重建家園的角度看,“我”的工作是否真的沒有實際意義呢?先來看看教參的說法:
“新橋”這一意象,是德國戰后重建的代表;而對“新橋”所通過的人員、車輛的種種統計、計算,則代表了一種十分不可靠、近乎癡妄和盲目的樂觀。
將“新橋”看作德國戰后重建的代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將通過“新橋”的人員、車輛的統計與計算看作“十分不可靠、近乎癡妄和盲目的樂觀”,顯然大有問題。
德國人向來以工作嚴謹、認真、細致和具有前瞻性著稱。對一座重建的“新橋”每天通過的人員和車輛數目進行統計,以此為基礎總結歸納出一段時間內數目的變化規律,將其看作今后制定發展規劃的借鑒,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這正是政府給“我”安排這份工作的原因和初衷。教參則說“我”的工作“代表了一種十分不可靠、近乎癡妄和盲目的樂觀”,是對小說中“我”的糊涂想法的推波助瀾,明顯荒謬不通。
但“我”只是個普通的德國人,是曾經的戰士,不是懂經濟的知識分子,因而對于自己工作的意義明顯認識不足。在“我”看來,工作中統計出來的數目,空洞而無意義,因而采取了敷衍了事、虛假瞞報的態度:
我以此暗自高興,有時故意少數幾個人;當我發起憐憫來時,就送給他們幾個。他們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當我惱火時,當我沒有抽煙時,我只給一個平均數;當我心情舒暢、精神愉快時,我就用五位數字來表示我的慷慨。
可見從“我”手里出來的數字的多少,完全是由“我”的心情決定的。這里根本沒有客觀性可言。不僅如此,“我”還自作聰明地對察看統計數目的“他們”報以嘲諷的態度:
當我把我上班的結果報告他們時,他們的臉上放出光彩,數字愈大,他們愈加容光煥發。他們有理由心滿意足地上床睡覺去了,因為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走過他們的新橋……
他們算出,今天每分鐘有多少人過橋,十年后將有多少人過橋。他們喜歡這個未來完成式,未來完成式是他們的專長——可是,抱歉得很,這一切都是不準確的……
其實,“他們喜歡這個未來完成式,未來完成式是他們的專長”這句在“我”看來充滿諷刺意味的話,正體現出德國人工作中的未雨綢繆、事先規劃的長遠觀念與意識,而“我”對這一切卻全然無知。
二戰中德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戰火摧毀,戰后重建家園,人們的熱情非常高漲。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是,雖然人們對于能夠直接感受到的切切實實的重建成果抱有極高熱情,但一些應當運用長遠眼光來看、不能直接獲得眼前利益的工作與建設,往往不能得到目光短視的人們的充分認識和理解。“我”對統計過橋數字的工作輕視、冷漠、不理解,正是這種社會心態的典型反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伯爾短小的《在橋邊》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二、對精神關懷的呼喚
由于認識不到工作的意義,加上工作的單調乏味,“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渾渾噩噩的,“我”在消耗著毫無意義的人生,沒有信仰和精神寄托。就在苦惱煩躁的時候,冷飲店的姑娘就像一陣清新的風吹進了“我”的心田,她成了“我”在工作中的唯一寄托。
她每天要兩次走過橋,一次一分鐘。這短短的兩分鐘,成了“我”生活中最絢爛的亮色:
所有在這個時間內走過的人,我一個也沒有數。這兩分鐘是屬于我的,完全屬于我一個人的,我不讓他們侵占去。
女孩的出現嚴重干擾了“我”本來就馬馬虎虎從事的工作。當她出現時,“我”再也不能在她出現的這兩分鐘內清點過橋的數目了:
當她晚上又從冷飲店里走回來時——這期間我打聽到,她在一家冷飲店里工作——,當她在人行道的那一邊,在我的不出聲音、但又必須數的嘴邊走過時,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動;當不再看見她時,我才又開始數起來。所有一切有幸在這幾分鐘內在我朦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過的人,都不會進入統計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們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靈,不存在的東西,都不會在統計的未來完成式中一起過橋了。
這兩分鐘,是“我”追隨姑娘的芳蹤心隨她動的美好時刻。世界在這一刻幾乎都凝滯了,所有過橋的其他人都成了我思想中可憐的垂浮物,“我”把他們徹底忽略了,他們都是虛空的,再也不能進入“我”的統計中去。小說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我”隨著姑娘的倩影內心激烈地翻騰,但通過對過橋數目的忽略能間接看出“我”對姑娘的如醉如癡。是的,“我”已經不可自拔地愛上這個姑娘了:
這很清楚,我愛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讓她知道。她不該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計算都推翻了,她應該無憂無慮地、天真無邪地帶著她的長長的棕色頭發和溫柔的腳步走進冷飲店,她應該得到許多小費。我在愛她。這是很清楚的,我在愛她。
這段短短的話語,竟然連用了三個“我愛她”,并且兩次強調“這很清楚”,可見愛得沉迷和癡狂;但“我”對這種單相思又是很清醒的,或許是考慮到自身殘疾的緣故,“我”并沒有付諸行動,可能是顧慮到一旦付諸行動連這珍貴的兩分鐘都會喪失。只要心愛的人能夠無憂無慮、天真無邪地工作并且能得到許多小費,這就夠了。
表面上看,伯爾在寫愛情對人的影響,表現出愛情對人產生的無比強大的精神力量,教參中說這種精神力量“深層則是對德國戰后重建中偏重物質而缺乏精神關懷這一問題、以及小人物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的精神狀態的思考”,這自然可備一說;但筆者更愿意做出如下補充:一個戰爭中的傷兵,在戰后重建的過程中,從事著在他看來毫無意義的工作,并且從沒有受到愛情的激勵轉而熱愛自己的工作。類似這樣的社會現象,不也能引起人們足夠的深思嗎?
“我”對這位姑娘的迷戀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當飯碗受到了威脅,“他們”對“我”進行檢查的時候,“我”不能不端正自己的態度,發瘋似的數著橋上過往的人。即便如此,“我”仍舊沒有把心愛的姑娘計入統計數字,這也是“我”只比主任統計員少算了一個人的原因。按照“我”的想法,“我一輩子也不會把這樣漂亮的女孩子轉換到未來完成式中去;我這個心愛的小姑娘不應該被乘、被除、變成空洞的百分比”。“我”對工作的厭倦程度就如同對這位姑娘的愛戀一樣,也是無以復加。
由此,聯系小說中“我”的身份,引發了我們對一種社會現象的反思:一個因二戰而殘疾的德國士兵,雖然在戰后得到了較為妥善的安置,有了一個飯碗,但他的精神創傷有時卻是無法用現實物質彌補的。由于戰爭造成的生理與體格上的缺陷,面對自己心愛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愛情,他不能也不敢表達出內心熾熱的情感,只能把情感深深地壓抑在內心。由于對愛情毫不自信,對待工作也只能是應付,絲毫提不起任何興趣。說到底,這仍舊是一種戰后綜合征的體現。
戰后德國處于極度缺乏糧食、工作崗位和房子等物資的惡劣情況之下,更為可怕的是戰爭留給人們的心靈創傷,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后續影響無處不在。“我”的經歷和遭遇可謂典型。伯爾的《在橋邊》描寫人的心理活動時,雖然沒有直接寫出戰爭的受害者“我”對戰爭的憎惡之情,但通過敘述“我”對愛情的壓抑以及對工作的懈怠,還是間接地表達出戰爭對德國社會仍舊有著剪不斷的不良影響。以“我”為代表的德國民眾需要的不僅是工作,還要有精神上的關懷。精神上的創傷得到了療治,德國就不僅能夠從廢墟中崛起,而且其人文、思想以及文化也才能得到相應的恢復和繁盛。由此可見,伯爾的《在橋邊》是德國民眾對精神關懷的呼喚。
三、對社會進步的自信
小說的結尾對“我”來說可謂大歡喜:由于得到了主任統計員“忠實、可靠”的評價,“我”被調去數馬車。這樣一來,“我”就用不著整天待在橋邊了,因為馬車一天最多只有二十五輛,只需每半小時在腦中記一次數字就可以了;更令人欣喜的是,“四點到八點時根本不準馬車過橋,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飲店去走走,可以長久地看她一番,說不定她回家的時候還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愛的、沒有計算進去的小姑娘……”。
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于其中蘊含著永不褪色的進步意義,寄托著作者的理想與期望;哪怕是悲劇,也要通過“花瓶的破碎”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促使人們反思造成悲劇的原因是什么,從而引起社會療救的希望。伯爾的《在橋邊》思想趣味并沒有一味地沉淪下去,沒有讓“我”在生活中徹底失望,而是讓“我”重獲新生,從中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在故事的結尾,“我”幻想著“說不定她回家的時候還可以送她一段路呢”,聯系之前即使深愛著她“我也不愿意讓她知道”,“我”的思想更進了一步。相信有些善良的讀者甚至都能聯想到“我”與姑娘最終的大團圓的結局。可是教參中卻不這樣認為:“小說的結尾盡管皆大歡喜,故事卻似乎并未因此終止。作品中埋下了的伏筆‘我愛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讓她知道’,預示著‘數馬車’的好運對‘我’也是十分有限的,或許那將是永遠的愛戀,或許還將伴隨著更多的痛楚。”
以上兩種看法都是猜測。筆者以為,伯爾在故事的結局中并沒有說到“我”與姑娘最終的結局,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如果安排“我”與姑娘終成眷屬的結局,則不僅故事情節轉換太快,而且從故事的發展線索與脈絡來看,似乎又不太現實,甚至有一種嚴重失真的感覺;如果繼續安排“我”與姑娘始終保持過去的狀態——“我”只能遠遠地觀望她,但她不知道——從情節的發展來看則又處于停滯,也就是說,無論“我”的身份、思想如何變化,姑娘始終是水月鏡花,“我”和她之間始終處于之前的“原生態”,沒有任何變化,這恐怕又是讀者難以接受的。
那么,最折中、最完美的做法就是讓“我”對姑娘的情感更進一步,由起初的“不愿意讓她知道”發展到幻想“說不定她回家的時候還可以送她一段路呢”,但最終的結局是什么,伯爾沒有交代,甚至連暗示都沒有。讀者只能根據自己的意愿做出相應的猜測。見仁見智的事,就交給讀者按照各自合理的空間去揣摩吧。
但是,《在橋邊》中的“我”畢竟不是單個的個體,而是二戰后德國民眾的縮影與典型,從“我”的生活狀態與精神狀態中,我們可以看出伯爾對戰后德國社會的評判。伯爾在小說的結尾把“我”的思想境界推進了一步,“我”不再對姑娘保持遠觀,而是有所幻想。聯系之前“我”對生活的無比失望,“我”的幻想不正是一種前進的動力嗎?從“我”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出伯爾對整個德國社會寄予的樂觀和自信,這正是德國社會不斷進步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