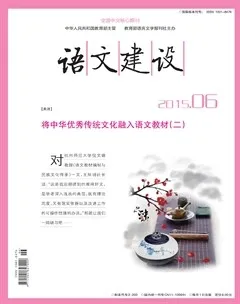語文教材編制與民族文化傳承
教材發展的本質是選擇文化,語文教材尤其如此。教育的社會意義,是賦予社會成員以一定的文化,使其了解和適應這一文化背景下的社會秩序,并且獲得在這一社會秩序下自我完善的能力和素質,這是一個自然人通過學校教育成為社會人的必由之路。因此,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的人們,無論是為了維持和延續某一種社會秩序,還是創造和確立一種新秩序,總要對文化做出選擇并加以組織,使之能成為有效進行傳播的教學內容結構,并將其具體體現于教材中,從而促成下一代對這一文化秩序的認同。這是教材為實現教育目標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務,也是語文教材發展的基本問題。
一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建設歷程看,我們走的是一條“之”字形的曲折道路。以往我們語文教材建設中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缺乏對“文化內容─教育內容─語文教材”的區分及其對動作程序的把握,即沒有從中華民族“文化內容”中精選出作為“教育內容”的核心知識,再圍繞核心知識搜集、組織大量的素材,然后才進入語文教材的編制工作。這與我國語文教材編制長期以來以“運動式”為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定力有關。其根子在于對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的“語文”的文化屬性認識不足,缺乏文化自信。
從古至今,盡管文化的傳播途徑是多元的,但語言文字無疑是一條主要途徑。文化隨著文字的記載與運用而傳承、發展,文化是語言文字的命脈,也是語文教育的命脈,然而長期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卻是我們語文教育的一個短板。
1.語文教育中的傳統文化支離破碎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由于“左”的思想影響,中華民族許多優秀傳統文化曾被當作封建主義的東西受到批判,當作糟粕遭到拋棄。“文革”十年更是走上極端,徹底砸爛了傳統。關于這一點,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已有結論:“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全黨工作重點一直沒有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由于‘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的影響,教育事業不但長期沒有放到應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運動的頻繁沖擊。‘文化大革命’更使這種‘左’的錯誤走到否定知識、取消教育的極端,從而使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廣大教育工作者遭受嚴重摧殘,耽誤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長,并且使我國教育事業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在許多方面本來已經縮小的差距又拉大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雖然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不可否認,享樂主義、物質至上的社會風氣也曾甚囂塵上,許多文化傳統在“產業化”中被不斷消解。加上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沖擊,語文教育中的傳統文化已經變得支離破碎。
2.古詩文在語文教材中所占比例偏低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片面地理解和強調教學內容要符合學生的生活實際,語文教學曾出現過三次“淡化”:一是淡化邏輯知識,二是淡化語法知識,三是淡化文言文。我們姑且不論這些淡化是否真正符合學生的實際,僅就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古詩文而言,不僅文言文在語文教材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而且許多古詩詞也只被編在課本的附錄之中(附錄是不教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功能受到嚴重削弱。語文教材的這種編輯思路與母語教材的文化屬性明顯是格格不入的。相比而言,在臺灣省的“國文”教材中,反映傳統文化的文言文的比例要高得多,在很長一個時期,初三約占55%,高中占比高達60%~80%。在高中,臺灣更設有教學時間為期一年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這里,我們不是簡單地以古詩文數量的多少論成敗,而是促使我們反思:承擔著中華民族共同語教育重任的語文教育、語文教材,究竟應如何對待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瑰寶。
3.語文學科在中小學的地位嚴重下降
回首當年,幾乎在社會上出現“下海”熱的同時,中小學的語文教育也受到“外語熱”和所謂“雙語教育”的沖擊,其后的“出國熱”進一步加劇了學生重英語、輕漢語的傾向。其實,學外語也好,出國也好,本身并不是壞事,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之一,但問題是許多地方不管外語師資力量和自身條件,一窩蜂都在搞所謂的“雙語教育”。而且為了追求不輸在所謂的“起跑線”上,小學從三年級甚至一年級開始就被要求開設英語課。在五花八門的各種理由中,仍有“拼音文化先進,漢字文化落后”的老調重彈。如果說民辦學校、社會教輔機構為了一己之私在嚷嚷“雙語教育”也倒罷了,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是,許多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門及其領導也在大力宣傳和推行這種“雙語教育”。不可否認,這對我們的語文教育和社會風氣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有位著名語文特級教師就曾尖銳指出:要不是高考考語文,語文在中小學的地位恐怕不是“小三子”“小四子”,可能連“小五子”也輪不上。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中,語文這門事關民族文化的主課怎么“主”得起來?學生的中文底子怎么能打好?更遑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
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語文教材中定位不清
時下,多元文化是一個使用十分頻繁的概念。毋庸置疑,文化具有多元性,然而一些不恰當的解讀和輿論導向,使之在許多時候成了貶抑中華民族文化的代名詞。我們許多同志也在“多元”聲中泛泛而談,在“多元”聲中昏昏欲睡,忘記了涉及民族文化的語文應該“以我為主”,沒有保持清醒的認識,沒有形成足夠的定力。因此,由此形成的語文教材文化很難說有時代價值。語文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的課程,民族性是它的文化個性。語文教材文化必須堅持“以我為主”,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風格,而絕不能以犧牲、拋棄或削弱民族文化,尤其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代價。中國語文課程不以中華民族文化為主,豈非咄咄怪事!
我國啟動和實施文化強國戰略已有多年,但中小學語文教材文化體系并不清晰。這從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教師節來臨之際考察北京師范大學時的談話可見一斑。他對中國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被去掉的現象,毫不掩飾自己的好惡。他在明確表示“很不贊成”的態度之后說,“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總書記的這番話,正像一些媒體上的評論所說:“既有著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的熱愛情結,又有著對民族文化傳承的焦慮與期待。”“既是習近平的個人感受,也是習近平對教育界提出的期待與要求;既是業務的,也是政治的。”“從政治的角度去解讀,習近平這番話不只是入世的,更是面向中國未來的。”[1]同時,這番話對語文教育界而言,也不啻是長鳴的警鐘,它促使我們從文化強國的戰略高度重新思考語文教育,要把中華民族文化作為語文教材文化體系建設的核心來抓。因此,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這一語文教育固有功能只能強化,不能弱化。當然,這種強化絕非只是簡單地在語文教材中增加幾篇古詩文數量的問題,更不能像一些地方的語文中考,將古詩文的分值提高1分,就以為落實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而需要對語文教育進行全方位審視,對語文教材進行深層次改革。
二
語文有第一語文和非第一語文的區別。我國中小學生所學的語文課程是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的漢語文,這是作為中國人的第一語文或母語的學習。母語是人的基本生存狀態。母語教育在促使學生成為“社會人”這個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功能。對于國家來說,母語教育不僅是立國之本,也是強國之本。無論是回顧歷史還是展望未來,一個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實是,漢語文教育對于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著超越時代的深遠影響。
喬姆斯基曾經說過:學習一種語言,就是進入一個文化系統。母語不同于第二語言的根本區別是,母語的根在于民族文化,民族性是它的主旋律。周有光先生指出:“共同語有范圍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語,有全國共同語(國語)。我們的共同語是在多民族國家中,以主體民族的共同語作為全國共同語。”[2]因此,漢語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是中華民族的母語。漢字即中國字,漢語文即中文。中文是聯合國規定的六種通用語之一。由此可見,從宏觀上看,所謂母語教育,其實就是傳輸和弘揚母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流程,它使一代又一代學子從中汲取母文化的營養,再去孕育一個民族燦爛的未來。
在當今世界,追求民族化、科學化和現代化是各國母語教材編制的一種普遍趨勢。因此,世界各國母語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都非常強調通過母語去親近并融入母文化、強化其“根意識”。通過建立對母語的尊崇感,促進學生養成對獨特的民族身份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如果說科學化和現代化體現了世界各民族母語教育的共同追求,那么民族化則是各民族母語教材建設的個性追求,這是一種文化認同。在基礎教育所有的課程中,語文課程的民族性最強。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語文教育家指出:“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內容工具,似乎都還可以借鑒于他國先例的地方,獨有國文,非由我們自己來探索不可。”[3]張志公先生也強調:“語文是個民族性很強的學科。這不僅受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特點的制約,而且還受這個民族文化傳統以及心理特點的影響。”[4]在民族化、科學化與時代化三者中,民族化是“核心”。擁有了民族化,母語教材才算獲得了自己的“靈魂”。
中華民族文化是一個豐富博大的有機整體,也是一種取之不盡的寶貴資源。它既包括漢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現代文化。從語文教材文化建設的角度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保護民族文化遺產,推動當代文化發展,建立文化創新機制,保障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也是促進學生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的必要舉措。當然,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并不拒絕和排斥人類優秀文化,因為任何一個開放的民族,它的文化發展都離不開學習和吸收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民族化也只有放到現代化的坐標中,才能擁有自己的完整目標和真實意義。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所關切的漢語言文化畢竟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文化,是面向世界的、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說我們的文化要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立足點和自己的性格。同時,只有開放的、面向世界的、經得起歐風美雨的、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才是有活力的,而不是博物館里的木乃伊。明乎此,我們的語文教材建設要走民族化的道路,就必須深刻反映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充分體現漢民族語言文字的特點,努力符合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和思維習慣。
三
任何教材內容的選擇都有一定的依據或價值取向,尤其是語文教材。語文教材內容的主體是選文,所以選文內容的文化構成是語文教材文化的核心部分。從時間維度加以考察,選文內容的經典性與時代性是母語教材選文的主要依據或文化特征。所謂經典性,主要是指這些作品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經過時間考驗,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并被廣大讀者所接受,因而它們必然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經典是文化之母,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只能從閱讀經典開始。
我國自現代以來,對語文教育規定“經典”作品的問題做過較深入思考的,可能要數朱自清了。當時朱先生是從文言作品學習的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的。與當時多數人非議古文教學的意見不同,作為新派人物,朱自清十分強調文言作品的學習:“我可還主張中學生應該誦讀相當分量的文言文,特別是所謂古文,乃至古書。這是古典的訓練,文化的教育。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至少必得經過古典的訓練,才成其為受教育的中國人。”在《經典常談》的序言中,朱自清特別強調:“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5]如果說朱先生當年提出的問題只是需要我們深思:讀什么、讀多少才算是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那么今天的語文教材要落實2014年3月教育部印發的《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精神,就必須加以細化、具體化。要按中小學的不同年段,遴選并確定一定數量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作為語文教材的必讀篇目(我們稱之為“定篇”)。以往的語文教材曾經指定過“基本篇目”或“背誦推薦篇目”及“課外閱讀推薦書目”,但它們與“定篇”并非同一回事。現有的語文教材雖然也在努力加強經典教學,但還遠遠不夠。因為作為中國公民,中華民族共同語的學習,尤其在中小學階段,“定篇”的數量與教學要求應該有一個基本標準,而非僅僅是推薦。也就是說,不讀這些作品就不能算是學了中國語文。
我們曾經指出:掌握以“定篇”身份進入語文教材的民族的優秀文化、文學作品,其本身就是語文課程的目的之一,就是語文“課程內容”的一大項目。在這里,“定篇”不俯就任何的學生,不管生活處境如何,不管閱讀情趣如何,每個學生都應該按同樣的要求去學習、掌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與朱自清先生所說的對學生“必須加以強制的訓練”達成一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贊同施蟄存先生的意見:課文課程“要有一個基本教材,由教育部組織全國最有權威的學者來編,選的篇目必須是適宜中學生讀的、眾所公認的名篇,然后固定下來,十年八年不變,這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念書,一提起那些文章,大家都讀過,使全國的青少年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語文水平”[6]。這里的“語文水平”,站在今天的立場看,當然不僅僅限于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而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語文的素養。
總之,在當前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下,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中小學語文教材文化傳承功能的本質回歸,是固本培元、振奮民族精神的有力舉措,而且是促進學生國家認同、文化自信的重要條件,對于立德樹人同樣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劉雪松.習近平“很不贊成”中透露的信息[DB∕OL]. http://blog.ifeng.com,2014-09-09.
[2]周有光.語文生活的歷史進程[DB∕OL].中國改革網,2010-01-27.
[3]王森然.中學國文教學概要[A].李杏保,顧黃初.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124.
[4]張志公.語文教學論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351.
[5]蔡富清編選.朱自清選集:第二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3.
[6]王榮生,倪文錦.論語文教材中的“定篇”類型選文[J].全球教育展望,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