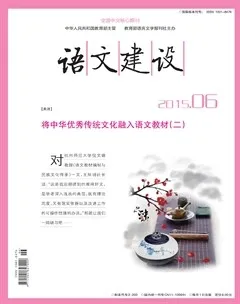閱讀教學“碎片化”分析及對策
閱讀教學在小學語文教學五個領域中所占課時最多,從總體上看,教師對此的投入也要遠遠超過其他幾個領域,但閱讀教學少、慢、差、費的現象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僅就閱讀教學的碎片化問題進行論述,希望引起廣大語文教師的足夠重視。
閱讀教學碎片化即把一堂課原本完整的目標和內容體系割裂成若干碎片,妨礙了學生對閱讀內容以及自身閱讀能力體系的整體構建,扼殺了學生持續學習的興趣,以致教學效率低下,教學目標難以達成。
一、“碎片化”現象分析
1.肢解式講析——導致信息碎片化
【閱讀教學案例1】
師:請同學們看第4自然段,看一看,這里運用了什么修辭方法?
生:這段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方法。
師:這句話中“三月的和風”“小溪的流水”實際上是指母親動聽的歌聲。作者這樣比喻,形象生動地寫出了母親嗓音的輕柔、甜美,讓我們感受到了她的歌聲如和風般輕柔,如小溪般流暢,十分悅耳。再找一找課文中引用的歌謠,體會這樣寫有什么好處。
(生讀出文中引用的童謠。)
師:這樣寫,具體再現了歌謠的啟蒙作用,點明母愛主題。“母親用歌謠把故鄉的愛,伴著月光給了我,讓一顆混沌的童心豁然開朗”,這句話直接寫出了歌謠對作者的影響。再請同學們看看母親都為“我”講了哪些故事?
生:嫦娥奔月、牛郎織女天河相會。
……
以上是一位教師執教五年級的閱讀課《月光啟蒙》中的教學片段。在上述案例中,教師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斷與意愿,一廂情愿地將課文“肢解”,采用片段教學、關鍵詞句分析等方式,把完整的課文“切割”得支離破碎,將相對系統的知識體系分解成若干個知識點,再按部就班地去講解、灌輸,而學生的狀態則是“被學習”“被閱讀”。窺一斑未必能知全豹,觀一葉未必真知秋至。類似的肢解式講析,窒息了文本的生氣,“肢解”了語文的美。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使得學生除了蜻蜓點水式地獲取了碎片化的信息之外,鮮有思維品質的培養和鍛造。
錢穆曾經指出:“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事件與彼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影響深處”,“切莫一一各自分開,只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這樣的閱讀教學,難以尋得閱讀的普遍規律和具有具體指向意義的脈絡延伸,實際上是點對點的、簡單化的灌輸,表面看似乎解決了學生語文學習所面臨的具體問題,但是由于缺乏上位的、整體的設計,忽視了語文學習各領域、各知識點、各能力點之間的聯系,孤立、靜止、片面地就具體的微觀問題進行分析,學生得到的必然是零散的、無序的、表面化的信息,難以建構起基于語文學科本質的、整體的、深刻的思考。
2.封閉煩瑣式提問——導致思維碎片化
【閱讀教學案例2】
師:你們喜歡燕子嗎?
(學生齊答:喜歡。)
師:燕子的動作是不是很敏捷啊?
(學生齊答:是。)
師:你是從哪里讀出來的?
生:“在微風中,在陽光中,燕子斜著身子在天空中掠過,唧的一聲,已由這邊的稻田上,飛到了那邊的高柳之下”,我是從這里讀出來的。
師:具體說說,你是從哪一個字,哪一個詞讀出來的?
……
課堂提問是影響教學效益的關鍵因素。日本著名教育家齋滕喜博甚至認為,教師提問是“教學的生命”。分析上述《燕子》一課教學片段,不難看出,課堂提問仍然存在諸多偏頗:無意義、無價值的問題多,能夠切中要害的真問題少;事實性、記憶性的問題多,能夠培養學生專注能力、深思能力和反省能力的問題少;隨心所欲、零打碎敲式的問題多,目的明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少。教師的提問停留在淺層次的交流上,最典型的莫過于這種脫口而出的“喜歡嗎”“是不是”之類的問題,學生也只是簡單回答“喜歡”“是”。這樣的問題便是無效問題,無益于啟發學生積極思維,與“灌輸式”教學無異。這樣的課堂上,學生在緊張地、匆忙地應對教師較為密集的提問,學習只不過是為了尋求一個結果,而無須也無暇顧及過程的意義。表面上看,學生學習積極主動,師生交往互動頻繁。實際上,學生只是在被動應對,真正的探究學習并未發生。由于問題過多、過濫、過于碎片化,缺乏內在聯系,學生只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對還是錯,而不去思考對或錯的原因及意義、此問題與彼問題的關聯、下一個問題會是什么、為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等等。
類似的偏頗式提問,導致邏輯思維的碎片化,最終導致思維能力弱化。在膚淺的問答過程中,學生難以形成完整的、有縱深感的知識體系,他們回答問題時表現出來的論點的片面化和論據的膚淺化,還會使系統的、層層遞進的邏輯思維被擱淺。這樣的問題,使得思維由深入淺或淺入淺出,學生很難主動去理解和閱讀,必然造成思維的惰性,不可能產生深入、系統的思維活動。
3.泛濫式朗讀——導致思想碎片化
【閱讀教學案例3】
師:請同學們自由朗讀《匆匆》這篇課文,把喜歡的語句畫下來。
(學生聲音洪亮地自由朗讀。)
師:匯報一下你畫了哪些語句,請讀給同學們聽。
生:“在默默里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里,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
師:誰還能有感情地朗讀這句話?
(指名另一學生再次朗讀。)
師:你還找到了哪句話,給大家讀一讀。
……
朗讀是重要的閱讀教學手段。書聲瑯瑯是語文課堂的一道風景,但不意味著朗讀要充斥整堂課的教學。上述案例是高年級的閱讀教學片段,學生在這一學段的閱讀,默讀、瀏覽、略讀同等重要,而教師一味地、單一地讓學生進行朗讀實踐,這樣的做法是失當的。首先,教師要求學生從頭至尾全文朗讀,又沒有提出有思維價值的問題,這本身就是欠妥的;其次,朗讀過程中沒有引導學生理解語言文字,學生甚至不知文字究竟承載了怎樣的情感,又怎么會做到有感情地朗讀;最后,教師在這個教學片段中的朗讀訓練明顯缺乏目的性,只是為了朗讀而朗讀。
這種泛濫式朗讀,剝奪了學生靜默沉思的權利。對于文字,學生無法做到沉潛其中、靜心涵泳,得到的只能是表面化、片面化、碎片化的所謂思想,而缺乏精神的成長,沒有思想的在場,必然會導致閱讀的貧瘠與淺薄,這樣的閱讀充其量是偽閱讀。
二、“去碎片化”對策
1.主題式教學——化零為整
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一節閱讀課最重要的不是知道了一個或幾個信息,也不是掌握了一個或幾個知識點。閱讀教學內容涵蓋面廣,知識跳躍性強,時空跨度大,但內在聯系非常緊密。因此,教師應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優化教材,對教材進行二度開發、選擇、組織與重構,確定一個鮮明的教學主題,并圍繞教學主題重新組合教學內容。教學主題猶如一根紅線,能把看似零散的一個個點貫穿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系統的目標與內容體系。比如一位教師教學日本作家清少納言的《四時的情趣》,確定了這樣的主題:不同的季節有怎樣的情趣,作家是怎樣寫出這種情趣的。這一案例的教學,教師讓學生的閱讀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從現象到本質、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在教學實踐中,教師把主題首先呈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有一個整體的感知,然后再讓學生自己去閱讀、思考、感悟、總結,避免了肢解式的煩瑣分析,學生先見森林,再見樹木,獲得的是完整而深刻的印象。
2.整合式提問——提綱挈領
閱讀教學中的每一個問題所涉及的內容都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因此,教師在設計問題時不能以單個知識點、能力點孤立地提問,而應圍繞教學主題,把一個個知識點放到整體的學習內容中去,再根據問題的結構類型,將封閉的與開放的問題組合起來形成問題鏈。比如,一位教師執教《凡卡》一課時設計了這樣的問題:凡卡的爺爺能收到這封信嗎?收不到信為什么文章結尾還寫凡卡那個甜蜜的夢呢?這樣的問題緊緊圍繞教學主題,問題與問題之間有縝密的邏輯關系,易于喚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閱讀期待,最終獲得思維及其能力的整體發展。
3.注重默讀——專注思考
1971年,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就對現代人的注意力匱乏癥做出了最好的診斷: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泛濫式朗讀除了只是讓學生獲取了相應的信息之外,另一個負面效應便是學生注意力的匱乏。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正在犧牲深度閱讀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在閱讀教學中,教師要合理把握朗讀實踐的容量,不見得越多越好,而恢復學生專注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注重默讀。尤其是高年級的長文教學,更要讓默讀作為主要的閱讀方法,在比較持續的默讀中,有助于學生深度思考,并獲得文字中所蘊含的,又經由個人建構的相對完整的思想。
總之,在閱讀教學實踐中,教師要警惕“碎片化”現象,讓教學基于整體的目標、解決整體的問題,讓學生經歷整體的過程,從而收獲整體的、優化的學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