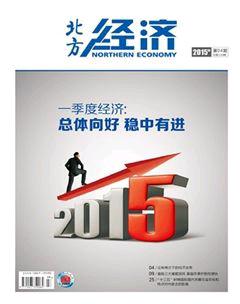為地方政府性債務戴上“緊箍咒”
王克修
《西游記》大鬧天宮的孫悟空讓眾神頭痛不已,曾幾何時,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也出現了一只“孫猴子”,那就是地方債務。 地方政府債務是指在某個時點上,地方政府作為債務人,由于以往支出大于收入所形成的赤字總和。截至2013 年6 月底,省市縣三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105789.05 億元,比2010 年底增加38679.54 億元,年均增長19.97%。其中,省級、市級、縣級年均分別增長14.41%、17.36%和26.59%。面對這種狀況, 各界人士發出警語:快給這只“猴子”戴上一個“緊箍咒”吧!
那么,作為不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地方政府,這么高的負債,拿什么來還呢?以往的經驗有四:一是新官不理舊賬,不管不問讓它爛;二是拆東墻補西墻,借錢還債;三是加強政府收費項目的征收力度,用收費來還賬等;四是賣土地還賬,這也是地方政府最有底氣的方式。
地方政府負債過高,固然有其本身的需要,但是更多地體現了地方政府領導風險意識差,急于出政績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甚至與政府主政官員的關聯利益有關。
當然,適當的地方政府債務也具有正面、積極的作用。2015年人大閉幕會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見中外記者時指出,中國的經濟還處于合理區間,而且我們的儲蓄率比較高,地方政府性債務70%以上是投資性的,是有收益的,而且我們也正在規范債務平臺,堵后門、開正門。因此,在現實狀況下,關鍵是合理控制債務規模,加強債務風險管理,給地方政府戴上“緊箍咒”。
戴上法治的“緊箍咒”
雖然我國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出現美國“底特律政府破產”結局,但仍需細化對債務的監管舉措,如人大應怎樣監督舉債行為、債務到期還不上該如何處置、誰應承擔責任等,都需要在預算法中明確權利和義務。中國原有預算法規定,“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此前的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一審和二審稿,都保留了現行條款。但在中國城鎮化進程提速背景下,面對地方建設投資熱潮,現行規定雖卡住了地方政府發債的閘門,卻沒有擋住地方政府變相舉債的腳步,不斷激增的隱性地方政府債務成為中國經濟風險之一。預算法修訂匯總了各方意見,明確規定:“經國務院批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一般公共預算中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可以在國務院確定的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舉借債務的方式籌措。”對地方發債規定了諸多限制,如“不得用于經常性支出”,債務還應有“穩定的償還資金來源”,地方政府不得在法律規定之外以其他任何方式舉債,以及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等。這意味著對地方政府舉債的開閘,但一條條“緊箍咒”表明了放開地方自主發債后嚴控債務風險的決心。
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不僅要摸清債務家底,而且要把政府融資舉債納入法制軌道,對政府舉債比例、數額進行科學界定。提高法律制度的執行力,治理地方政府過度負債。防止地方政府舊債未還又添新債。更重要的是,要前移監管關口,給地方政府盲目舉債套上法律“緊箍咒”。比如,把政府過度負債納入政績考核范疇,多從民生角度審視官員政績,完善包括政府負債在內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強化人大監督職能等。只有這樣,才能堵上政府負債黑洞,維護政府形象與公眾權益。
戴上審計的“緊箍咒”
政府性債務審計,摸脈更要開方子,否則勢必陷入“年年審計、年年加重”的惡性循環。追根溯源,地方政府大肆借錢、債臺高筑的原因有三:其一,財權事權不匹配。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后,大量的財權上收中央,較多的事權下放地方,教育、醫療、民生工程、社會福利處處都要地方政府增加投入,許多配套資金只能通過舉債籌措。其二,干部考核不完善。傳統政績評價指標中,以GDP、城市建設、形象工程為導向的問題普遍存在,加之考核問責不涉及政府債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地方干部舉債發展。等到債務壓力和風險凸顯,借債的前任官員早已升遷提拔,還債包袱則像“擊鼓傳花”一樣甩給后任。其三,債務監管不規范。舉債決策缺乏科學規劃和有效論證,導致舉債規模不受限制,更多地體現為長官意志;一些地方政府對債務管理工作重視不夠,數據統計不準確、不全面,加大了防范和控制債務風險的難度。
全國性審計工作要對中央、省、市、縣、鄉5級政府性債務進行徹底“摸脈”和測評。全國審計機關對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跳出“審而不計”的窠臼,推動相關規范約束措施的落實,給盲目舉債發展戴上“緊箍咒”。認真落實經中央批準,中組部印發的《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強調對政府債務狀況等情況的考核。這相當于給盲目舉債的干部上了“緊箍咒”。不顧有無償債能力盲目舉債,根源在于不承擔責任,要強化教育和考核,從思想上糾正不正確的政績導向,把政府債務作為一個硬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離任要審計,終身要追責。
戴上評級的“緊箍咒”
發布地方政府信用評級十分必要。評級方法的核心正是揭示債務主體安全負債的規模上限,告訴我們什么是其不可逾越的債務紅線,從而起到最為直觀的預警效果。
評級涉及用于債務管理和風險控制的一系列具體指標體系,如地方債務的總規模、當年發債規模、發債的具體條件、債務發行方式、風險預警、償債基金、債務違約,等等。所有這些具體的操作問題,在國債管理層面已經相對成熟,轉用于地方債只是一個技術和時間問題。但與發達國家信息公開不同,我國地方政府信息一般不公開,評級機構很難主動做信息評級,需要通過授權委托方式展開,所以取決于政府部門的需求,目前還停留在方法論證階段。
總之,為了加快經濟增速,地方政府千方百計擴大招商引資的力度、鼓勵負債經營、舉債投資建設,且國家對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制度規范和有效監管,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多頭、無序的融資局面。其結果是,顯性和隱性債務膨脹,償債風險隨之抬高。需指出的是,地方債務和地方政府性債務不是一個概念。地方債務 = 地方政府性債務 + 地方企業債務 + 地方家庭債務。可見,地方政府性債務是衡量債務存量的最小口徑,真正的麻煩在于三者疊加。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在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強債務風險管理,給地方政府戴上“緊箍咒”。其中,法治和透明要成為牢不可破的原則:該確立法律框架的搭建框架,該申明財政紀律的頒布典章,該轉化管理方式的協調推進。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決策咨詢中心副主任、教授)
責任編輯:康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