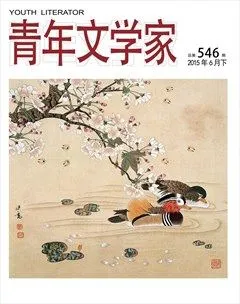順承與反抗
摘 要:母親和女兒的關系是女性存在的核心,在韋爾蒂的小說中孝順的女兒幾乎貫穿了她所有的作品。本文通過對比《樂觀者的女兒》和《六月演奏會》中的兩對母女,特別是在做孝順的女兒和做自己之間做著艱難選擇的女兒們,反映她們選擇做孝順女兒要付出的沉重代價。
關鍵詞:《樂觀者的女兒》;女性主義;韋爾蒂
作者簡介:陳向普(1975.11-),女,大連外國語大學,河南洛陽人,應用英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8-0-02
《樂觀者的女兒》是韋爾蒂獲得普利策獎的長篇小說,作品充滿了豐富的女性主義色彩。她以看似平淡的筆觸,刻畫了一個南方家庭的內部矛盾。故事的很大部分都是女兒勞雷爾對于自己父母的回憶。其中最讓讀者感到震撼的當數第三部分結尾處對于過去漫長的回憶。在母親病重時,勞雷爾和父親一樣,毫無能力把母親從病痛中解救出來,更不能擊退死神的逼進。家庭,朋友甚至牧師都不能給母親貝基以安慰,最后貝基在絕望中死去。在去世前,母親對著勞雷爾說出了那段最震驚的話,“你本可以挽救你的母親,但你卻只是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我為你感到絕望 ”。對于聰穎,敏感的勞雷爾,貝基臨死之言肯定深深地傷到了她。這個部分暗示了很多女性選擇做孝順女兒所付出的代價,特別是勞雷爾。無論是小說還是現實生活中,母女關系以及強大的女性傳統從一代傳到下一代都是很難界定的。然而,在韋爾蒂的小說中,期待使得很多女兒在接受女性傳統方面顯得尤其困難。當然和諧快樂的母女關系也是存在的,但是貝基和勞雷爾的關系卻不是如此。我們無從知道貝基的觀點,因為在小說開始的十年前她就去世了。鄰居,朋友,她的丈夫和女兒的記憶再現了貝基的一生。在小說開始,麥凱爾瓦法官向醫生描述他的眼疾時提到了自己的妻子。他是在修剪妻子的玫瑰時眼睛被刺傷的。他補充到,“貝基肯定會說我活該”。法官的假設反映出記憶中妻子典型的反應。
父親總是會溺愛獨生女兒,所以法官在女兒婚禮上的大肆鋪張也就不足為怪了。盡管是二戰的困難時期,勞雷爾的婚禮上還是有香檳和從新奧爾良請來的黑人樂隊。在妻子的眼中,法官的行為“完全是鋪張浪費,幼稚”。當回憶道這一段時,勞雷爾,就像個孝順的女兒,完全站在媽媽的立場上。然而她的兩句話卻值得推敲,一句是直接的宣告,“媽媽是迷信的”,完整的意思在接下來的假設句中完全體現出來,“媽媽或許是認為過度張揚自己的幸福是不幸的”。如果是這樣,貝基讓所有的幸福瞬間都顯得很可疑。上帝會懲罰看起來過于幸福的人;過度沉浸在快樂中也會使幸福變味。如果勞雷爾關于母親的迷信的說法屬實,那么早在勞雷爾的婚禮上母親的表現就為這個幸福的時刻施下了最咒語,暗示著后來這種迷信的應驗:勞雷爾和菲利普的婚姻幸福美滿,然而菲利普的死亡結束了這種幸福。縱觀小說中的母女關系,勞雷爾對于自己童年的回憶在貝基作為年輕女性的回憶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年輕時的貝基很獨立,比自己的哥哥們都勇敢。隨著她年輕時故事的展開,讀者發現很少有女性能夠和貝基相比。卡羅爾吉利根在中說過,“敏感于被人的需求并承擔起照顧別人的責任使得女性能夠注意到不同自己的其他的聲音,在做決定時也會考慮到別人的觀點”。而梅·薩藤曾經說過,“媽媽們很溫柔,毫無疑問,我們身體里母性的部分能夠給予這種溫柔,而我們身體中孩子的部分渴望感受到這種溫柔”。不管是梅·薩藤還是卡羅爾吉利根,她們關于女性,關于母親的觀點到了今天也不過時。但是如果這個標準套在獨立,勇敢,堅韌的貝基身上,那種母親應有的溫柔,敏感如果不是完全缺失的,至少也是次要的。
對于一個不敏感,更不溫柔的,甚至在臨死還要詛咒自己女兒的貝基來說,勞雷爾是孝順的。在整理父母遺物時,勞雷爾的記憶重現,她開始重新審視父母,他們的婚姻,他們的缺陷,同時也重新審視作為孝順女兒的角色。自始至終勞雷爾生成父母是相愛的。但在最后,貝基不僅否認了女兒,也否認了丈夫。丈夫承諾將死的貝基他會帶她回老家,對于這些無用的承諾,貝基喊道,“騙子,騙子”。在一家人執手相對無言后,貝基朝著勞雷爾說出了最后的詛咒,因為女兒沒能夠完全認同和參與自己作為將死之人的絕望和痛苦。韋爾蒂大部分小說中的女兒都是母親孝順的女兒,至少在母親去世前。父母有時要求過多,就像小說中的貝基的朋友把法官的再婚歸罪于勞雷爾;認為女兒們就應該呆在家里照顧父母,而不是跑到芝加哥去發展自己的事業。
在《金蘋果》,特別是《六月演奏會》和《漫游者》中,讀者又看到了孝順女兒,維吉的身影。《樂觀者的女兒》和《漫游者》極為相似。兩部作品都關于于一個親人的故去;兩個故事都聚焦于葬禮,在葬禮上聚在一起的鄰居們說起逝者時的夸張言語讓孝順的女兒困惑不已,不知該不該說出與他們觀點相反的實情;最為關鍵的是,兩個故事都有強勢的母親和孝順的女兒。故事中母親凱蒂和貝基有明顯的區別。貝基大學畢業,嫁于法官,住在城里;而凱蒂住在城郊,嫁于農夫,靠賣花草和冰激凌為生。盡管兩部作品相隔22年,但卻有著共同的主題:強勢的母親總是想當然的認為女兒就應該成為她們期望的那樣。
在《六月演奏會》中,女兒維吉開始時并不是個孝順的女兒。她是鋼琴老師的得以門生,并有一段甜蜜的戀情;甚至成為了鋼琴師。然后她離開了家鄉去了孟菲斯。讀者不知道在那里她呆了多久,做了什么。只是在她17歲時她回來了,母親迎接她的是,“你回來的剛剛好,該擠奶了”然后就解開帽子,扔在他倆之間的地上,盯著她的女兒。如果維吉有傷心,難過或者絕望的故事要傾訴,分享,她根本就沒有這個機會;如果她希望趴在媽媽的懷里痛哭一場,她也沒有能夠這樣做。如果她衣錦還鄉,沒有人祝賀歡呼。實際上,痛苦是母親的特權,但是母親不是為了女兒哭泣,而是為了丈夫和兒子。敘事者說,“在她的房子里,除了她沒有人可以哭,只有她可以,為了她的丈夫和兒子,因為他們都離開了”。凱蒂和為維吉之間的緊張關系繼續著,直到凱蒂死亡的晚上和她葬禮的那天。這時的凱蒂再也不能種花和水果到路邊去賣了。因為中風,她只是整天坐在那里,等待著維吉下班回家。最后當維吉回來時,我們看到這樣的對話:
凱蒂:看看太陽都到哪里了……
維吉:我看到了,媽媽
維吉到家晚了,在她還沒來得急換下高跟鞋和上班裝時,凱蒂已經開始列舉她的任務了,維吉什么也沒說,把念叨著“我已經自己呆了一天了”的凱蒂哄金了屋子。凱蒂在一個星期天去世的,或許有個四十幾歲的孝順女兒對于凱蒂來說不只是個福氣。但是母親的去世并沒有終結維吉的角色。第二天維吉被要求觀看母親的身體,當她拒絕時,人們竟說“你真不配有這樣好的媽媽”。像勞雷爾一樣,維吉也不再做孝順的女兒,而是開始做自己。她的決定來得很自然,沒有準備,沒有預兆。有人問,“你要留在這嗎,維吉”她回答,“明早就離開”。
在美國南方,更多的時候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不得不照顧家庭。在刻畫凱蒂和維吉時,韋爾蒂承認女兒們被母親們的要求和期望死死地禁錮住。女兒們或許在母親們活著的時候無法原諒她們,但當母親去世時,女兒們才能夠真正離開家,開始自己的人生。所以對于一個女性來說,要想不再是個孝順的女兒,成為獨立的個體,母親必須死去。如果說在母親們活著時,女兒們是她們不斷地要求的受害者,那么去世后的母親成了受害者。去世使得母親把自己的女兒從一切日常的繁瑣中解放了出來。
對于韋爾蒂作品的女性解讀可以發現韋爾蒂的焦點在于對母親的態度,在于女兒要尋覓不同于母親的獨立的生活。她們不想變成她們母親那樣的人,通過離開家鄉到北方接受教育,她們儼然已經成為了完全不一樣的獨立的人。
母親的去世重新定位了女兒的角色。她們的生命是她們自己的,她們的角色不再是在母親的家里打理家務的孝順的女兒們。女兒順承母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反抗母親也不是總是如此明顯的。維吉和勞雷爾離開了他們母親的家,甚至是母親的城市。反抗母親是孝順女兒想要獨立,想要成為自己的必要的第一步。孝順女兒的故事對很多先是認同母親后來反抗母親的女性來說并不陌生,正如有評論者所說,“我想只有當你的父母都去世時,你才成為你自己。說起來很殘忍,但卻是事實”,而更恐怖的是對于女兒們來說這尤其是事實。
參考文獻:
[1]Eudora Welty,The Optimists Daugh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