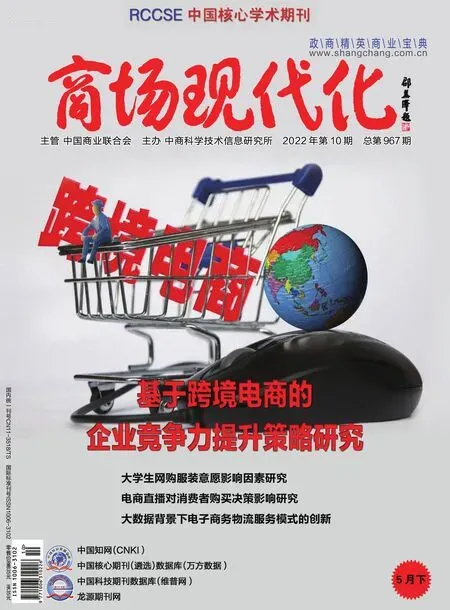論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認定的若干問題
朱海威
摘 要:良好的市場秩序是保障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也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前提。當下,合同詐騙罪已成為危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惡性腫瘤”,不及時切除將會進一步侵犯我國公民的公私財產所有權益。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需要市場秩序規范,而當下利用簽訂合同詐騙錢財的案例已成為我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重難點。因此,對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認定的若干問題進行分析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企業經營;合同詐騙;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
一、前言
從合同詐騙罪立法淵源對合同一詞進行剖析可知:本罪合同指的是經濟合同,刑法立法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詐騙若干問題的解答,但在《解釋》第二條中規定:通過經濟合同渠道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利用經濟合同一詞逐漸出現在人們視野,而正確界定合同含義必須綜合修改后的刑法進行分析,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范圍擴大,廣泛性和包容性明顯增強,正確處理好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的認定意義重大。
二、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概述
合同詐騙罪客觀性質決定了其與市場經濟關系的聯系程度,而與社會關系并無多大聯系的“合同協議”并不在屬于合同范疇,例如婚姻、監護、收養撫養等協議。另外,在不違反刑法初衷原則下需最大限度的懲治犯罪,合同詐騙罪合同來源于經濟合同,但刑法最終目的是根本原則。因此,除了通過經濟合同渠道進行詐騙外,利用其它“合同”進行的詐騙活動威脅到市場秩序穩定后,都可在刑法上可預測為合同詐騙罪,這類合同本質都屬于合同詐騙罪的延伸范圍。除此之外,對于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的認定證據需具備客觀可見性,刑法法定原則上規定被告人利用合同存在證據是基本要求。但在實際生活中,合同類型具有多樣性,包括口頭書面和其它公證形式,不同類型合同在訴訟案件中的舉證程度也不盡相同。所以從客觀角度分析,口頭合同應被排除在合同詐騙范疇外,但由于口頭合同也是合同法公開確認的一種形式,訴訟案件中的被告人詐騙行為發生經濟往來,且利用口頭合同也同樣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要素,無論是簽訂還是履行口頭合同被騙取財物的都可根據合同詐騙罪實際情況論處。
三、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
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理論區別應把握以下幾點:
1.主觀目的
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行為的成立一般都是以假意簽訂合同為例,最終達到對對方當事人財物的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詐行為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只是片面的欺詐性質。
2.客觀方面
民事欺詐行為基于隱瞞事實的真相而控制在一定程度內,可有民事法律或政策調整得以解決;而企業經營中的合同詐騙已構成嚴重危害,合同虛構內容發生質變,需要刑法介入。民事詐騙行為人一般缺少履行合同內容的能力,有民事責任存在。
3.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不同
企業經營合同詐騙罪中的行為人一般沒有履行合同誠意,客觀上對于合同內容采取消極應對態度,走小成本換取大利潤路線;民事欺詐行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但經過實際努力仍舊無法達到合同預先要求的效果內容。
4.對所獲財物的處理方式不同
企業經營合同詐騙中,行為人在騙取對方財物后一般采取揮霍或潛逃策略,毫無履行義務的行動;而民事欺詐行為人在獲取前期資金后,一般是用于購置合同材料,從而為完成合同內容做準備。
5.產生的法律后果不同
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當事人需承擔一定刑事責任,而民事欺詐則需民事相關責任規定解決。筆者認為:確定行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別二者的關鍵之處,基于客觀行為和客觀性質的決定才不至于有失偏頗。
四、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1.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認定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合同詐騙罪中目的型犯罪的主要特征,這點從根本上區別于合同民事糾紛,而非法占有的界定屬于主觀狀態范疇,肉眼和儀器測量都不能進行直觀衡量,只能依據一個人的外在表現進行認定。認定一般是根據行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行為人基于自身能力履行的態度、綜合行為人積極性和造成損失原因三方面進行衡量。筆者認為通過履行能力來認定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問題是不科學的,因為合同簽訂時,行為人是否有能力履行合同內容本身就是基于自身主觀意識的結果。假如具備合同履行能力的是通過合同這一外在形式來實現經濟目的,部分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是基于此合同誘惑點,誘騙他人簽訂合同,而后逃之夭夭。也有履行能力不夠而在合同內容中夸大其詞,達到誘騙簽訂合同和詐騙他人財物的目的,或是想用自己小本經營來換取超過額定范圍的利潤。當然,在行為人不具備履行能力的情況下,也會存在詐騙他人財物和執行無本經營策略以謀取利益等可能。因此,履行能力和非法占有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統一聯系,也不具備必然聯系。
具體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在合同簽訂階段查看是否具有欺詐行為,具體表現在通過虛擬擔保或身份達到欺騙目的,讓簽訂方形成錯誤認識而支付錢財的情況。企業經營中合同簽訂要以當事人真實身份進行洽談,以免發生合同糾紛時不易解決。倘若當事人在合同簽訂中有意隱瞞部分真實情況,虛構或假冒他人名義進行的行為一般可認定為非法合同簽訂。而擔保是保證債權人發生債券沖突時進行的一種補償方式,如當事人擔保提供虛假信息又不履行義務,一般可認定為企業經營中的合同詐騙現象。二是簽訂合同后的行為人具體履行狀況,如果雙方誠信合作,則合同生效就意味著行為方履行義務的開始,合同終止履行只能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結果。假如合同生效后行為方消極對待或是具備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況就可認定為企業經營中的合同詐騙。行為人的積極態度與搪塞行為存在本質區別,本來有合同履行實現的可能性而采取拖延等手段進行錢財詐騙的行為,也是一種基于主觀心理的推定。所以,在實際企業經營中的合同詐騙罪認定應綜合考慮認定方法與行為人反證。
2.合同詐騙罪的數額如何認定
《刑法》條令條例規定:合同詐騙數額大小是構成企業經營合同詐騙罪的基礎條件,只有足量額度才可被認定為詐騙,而具體數額大小則是對行為人進行刑法判決的必要條件。
(1)關于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
企業經營中的合同詐騙數額存在兩種:一種是合同上明碼標注的金額,一種是在實際履行過程中產生的金額。但由于合同明碼標注的額度一般比較大,所以筆者認為實際詐騙的金額數量是判定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輕重的標準。原因可分為兩種:客觀上說實際詐騙的財物數額是對財產所有權和經濟管理制度侵害程度的重要衡量標尺,主觀上說詐騙者一般不可能把合同上標明的金額全部騙到手,定金和保證金詐騙是常見的兩種形式。所以用行為實際詐騙金額來衡量犯罪程度符合刑事犯罪基本責任原則,但合同標明的數額大小在詐騙案件中可作為量刑情節進行考慮。
(2)關于合同詐騙是貨物時的數額認定
如果合同詐騙對象以貨物進行衡量,那貨物銷贓過程中的詐騙認定是以實際金額為準,還是以銷贓所得為準,銷贓所獲金額高于實際金額或低于實際金額又如何進行認定是一種常見的企業經營詐騙現象。筆者認為:一般情況下,行為人詐騙成功后會急于銷毀贓物,銷毀金額一般要遠低于貨物實際價格,因此要以實際貨物價格進行詐騙罪量刑的認定標準。另外,當銷毀贓物價位高于實際貨物金額時,這時的贓款由被害人損失和買贓人損失兩部分構成,對于企業經營詐騙者來說,兩部分非法所得金額都應納入量刑范圍計算。
(3)關于連續詐騙的數額確定
在企業經營合同詐騙過程中,也會出現連續詐騙且中間出現歸還現象情況,這種情況的詐騙衡量是以累計金額計算,還是最終所得金額計算也是一種常見的企業經營詐騙種類。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應分為客觀和主觀兩種,客觀上行為人歸還詐騙財物,被害人損失大幅減少,詐騙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主觀上行為人在詐騙過程中主動放棄詐騙意念,應以實際詐騙金額和被詐騙者實際損失量刑計算。
(4)關于共同實施合同詐騙的數額認定
對于共同實施合同詐騙的現象,應用共同詐騙金額來衡量合同詐騙總數。受害人損失客觀上是以被騙金額總數認定,而詐騙行為是以詐騙金額總數認定,共同犯罪人故意詐騙主觀上也都指向詐騙總金額。但在量刑過程中,不同當事人的社會危害性不同,應依據不同主體的犯罪具體金額進行認定。其中,也有主犯與從犯的本質區別,只有運用共同詐騙金額進行衡定,才可依據不同行為主體進行罪行衡量,這也是刑法共同犯罪主犯與從犯一般原則的要求使然。
五、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其它方法”
刑法在第224條1—4項中明確指出四種不同類型的合同詐騙類型,并在第5項標示“以其它方法騙取當事人錢財的”做出概括性規定,適應今后經濟發展和保持該法穩定也是立法的主要目的。與此同時,這種表述也給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認定帶來困難,其它方法設定屬于一種主觀意識形態,但凡符合企業合同詐騙特征的都可劃分在詐騙罪范疇。筆者依據自身實踐經驗,針對常見的企業經營合同詐騙方法做出以下歸納與劃分:
1.擬造虛假合同欺騙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
2.擬造虛假貨源,簽訂空頭合同。例如行為人通過借去或租賃貨物來欺騙被害人,并和被害人簽訂合同后達到詐騙貨款的目的;
3.蒙蔽誘使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愿簽訂合同,本質上利用被害人信任達到欺騙目的;
4.通過虛假廣告和信息渠道誘騙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不正當手段謀取中介培訓費;
5.冒用投資商,經銷商,合作商名義簽訂合同進行欺騙的;
6.采用賄賂手段讓當事人簽訂合同,例如部分當事人與國家政府機關或國有企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誘騙國有資產就是此類典型情況;
7.債務行為人未經債權人同意就將合同義務全部或部分轉移給第三方,達到逃避債務的目的。例如國內部分皮包公司與第二者簽訂供貨合同時,待收到定金或貨款后就應用欺詐手段將合同義務轉移給第三者,等到被害者發現受害時,對方當事人仍借故不履行相應義務等;
總而言之,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把利用合同載體進行詐騙和簽訂履行合同義務的詐騙形式進行區分,前者是在合同的前期進程中應用,后者是在合同簽訂后期進行應用,前者的掩蓋形式主要是企業合同,后者對合同載體客體體征體現不明顯。
六、結語
綜上所述,企業經營中合同詐騙罪認定問題類型多樣,而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是認定詐騙成立與否的臨界點。以上分析進一步證明:良好的市場秩序是保障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和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前提。雖然合同詐騙罪可危害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但科學及時的預防和明確細化的立法認定將有效抵制不法分子詐騙行為。當然,為從根本上保障我國公民公私財產的所有權益,推動市場經濟良性發展,所有從業人士都應上下齊心,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周彥平.合同詐騙罪的構成及認定的若干問題[J].中國政法大學,2014(08):231-244.
[2]肖中華.論合同詐騙罪認定中的若干問題[J].政法論叢,2012(02):255-267.
[3]周銘川,黃麗勤.詐騙與欺詐概念辨析[J].江蘇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4):121-133.
[4]郭躍.淺議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認定和區分[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4(01):23-25.
[5]陶陽,徐繼超.論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及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