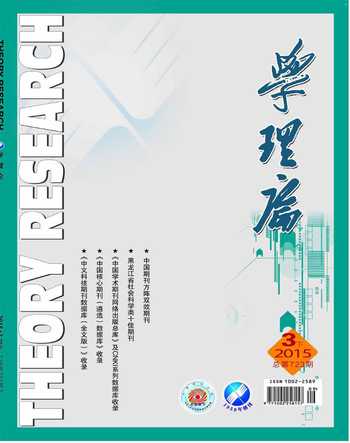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對策
周勇
摘 要:我國當前國家與社會關系正朝著相互影響的互動演進,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卻仍處在一種政府、自治組織、經濟組織相混合的管理模式,存在著政經不分和政社不分、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缺失、土地產權關系模糊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應當采取政經分離、賦予經濟組織法人資格、明晰土地產權關系等相應對策,發(fā)展壯大集體經濟。
關鍵詞:國家與社會;農村集體經濟;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51-03
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來,農民家庭經濟獲得了快速發(fā)展,但集體組織經濟發(fā)展則不明顯,集體組織的經濟實力甚至還有所下降,同時,經過30多年的發(fā)展,似乎進入了一個“高原期”。鄉(xiāng)政村治體制的確立、村級治理模式的變遷,在實踐中并沒有徹底改變集體經濟與政府、社區(qū)的關系,對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并不十分明顯。隨著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資本對農業(yè)的滲透,農業(yè)企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突起,我國農業(yè)經濟正逐步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格局。如何堅持集體經濟在我國農業(yè)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發(fā)揮集體經濟的重要作用,成了學界當前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試圖在“國家與社會”視野下,通過對我國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現(xiàn)狀、問題進行分析,提出發(fā)展對策。
一、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現(xiàn)狀
當前的農村集體經濟是由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經濟發(fā)展而來,有鄉(xiāng)(鎮(zhèn))、村、組三級,仍處在一種政府、自治、經濟組織相混合的管理模式。經營體制是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tǒng)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經營主體主要有集體組織和農民家庭、專業(yè)大戶、農民專業(yè)合作社、龍頭企業(yè)、經營性農業(yè)服務組織等。總體上看,集體組織經濟實力下降、集體經營弱化,發(fā)展遲緩;農民家庭經濟雖發(fā)展強勁,但后勁不足;農民家庭與集體組織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離散關系,表現(xiàn)出明顯的“小農經濟”特征。具體表現(xiàn)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集體組織經濟實力有所下降。主要表現(xiàn)為集體組織的集體經營弱化和部分鄉(xiāng)村企業(yè)關閉或出租、轉包。從每村擁有集體資產量、年內可分配收入及集體經濟收益情況等方面看,2000年,每村擁有集體資產150.9萬元,比1999年減少2.6%,其中擁有生產性固定資產66.2萬元,基本與1999年持平;每村年內可支配收入為19.37萬元,比1999年減少0.9%;有集體經濟收益的村388 997個,占匯總村數(shù)的53.9%,有近一半的村沒有集體經濟收益。2006年,全國農村村組集體所有年末生產性資產原值為4045億元,比2005年減少16.2%;每村年內可支配收入為39.8萬元,比2005年減少3.2%;有集體經營收益的村為258 813個,僅占匯總村數(shù)的43.1%,比2000年減少了近10%[1]。也就說,在全國有50%左右的村集體沒有集體經營收入,集體收入主要依靠財政補貼、土地和集體資產出租等有限來源,經濟實力較差,發(fā)展艱難。
第二,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集體組織內部發(fā)展不平衡,突出表現(xiàn)為集體統(tǒng)一經營的弱化和農民家庭經營的絕對強勢。如從2002至2006年村組集體經營收入與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情況來看,村組集體經營收入分別為:13 987.7、15 225.7、15 547.3、16 565.3、18 309.2億元,在農村經濟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別為:12.0%、11.6%、10.3%、9.5%、9.1%;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分別為:59 992.0、64 908.8、72 827.6、81 051.5、90 451.3億元,在農村經濟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別為:51.4%、49.3%、48.2%、46.2%、45.2%[1]。二是村級集體組織之間發(fā)展不平衡,主要體現(xiàn)在以村為單位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的階梯性差距上。從2007年農村集體經濟的發(fā)展情況看,農村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村383個,占匯總村數(shù)的0.06%;在1 000-3 000元的村,占34.8%;在3 000-5 000元的村,占40.9%;在5 000-10 000元的村,占20.7%;10 000元以上的村有11 054個,占1.8%,其中在30 000元以上的村有107個[2]。并且,這種差距和分層并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的暫時現(xiàn)象。
第三,農民家庭仍然是經營主體的主力軍。農民家庭作為組級集體經濟的基本細胞,是集體經濟的經營主體,具有經濟實體的性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主體[3],自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農民家庭迅速成為集體經濟經營主體的主力軍。1983年底,97.8%的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了包干到戶,涉及農戶總數(shù)的94.5%,2000年,全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村數(shù)為717 047個(當年匯總村民委員會數(shù)為722 745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農戶為22 219.1萬戶(當年匯總農戶數(shù)為23 127.6萬戶)[1]。截至2011年底,家庭承包經營農戶為2.288億戶,比2010年底增長0.14%[4]。
第四,經營主體的新變化。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經營主體在原集體組織、農民家庭基礎上,相繼出現(xiàn)了專業(yè)大戶、農民專業(yè)合作社、龍頭企業(yè)、經營性農業(yè)服務組織等新形式,正在逐步形成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yè)經營等共同發(fā)展的新型農業(yè)經營體系。僅以農民專業(yè)合作社為例,2011年底全國總數(shù)已達50.9萬個[5],2012年3月底為55.23個[6],到2013年3月已超過73萬個[7]。
二、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存在的問題
(一)政經不分、政社不分
我國當前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帶有明顯的國家社會一元結構痕跡,政府機關、自治組織、經濟組織三者黏合在一起,集體組織至今尚未完全獨立,政府與社會、經濟的關系也就沒有完全理順,政社不分、政經不分。政府機關與自治組織、經濟組織,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也就沒有分開。
集體經濟組織是一種非獨立的、依附于農村基層政府機關和群眾自治組織而存在的經濟組織。從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fā)展來看,合作化時期的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是獨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時期雖然政經、政社合一,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分別屬于農村三級集體經濟組織的名稱,但當前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是農村基層政府機關,村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村民小組也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的細分單位,集體經濟組織成了一種非獨立的、依附于這些組織而存在的經濟組織。
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我國農村基層政府機關,但同時還擁有集體土地和鄉(xiāng)辦企業(yè)等集體資產,鄉(xiāng)鎮(zhèn)級集體經濟仍然存在,鄉(xiāng)鎮(zhèn)政府實際上就是本級集體經濟的管理者,政經不分;村委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同樣擁有集體土地和村辦企業(yè)等集體資產,也是一級集體經濟,同時,受“強國家——弱社會”的影響,村委會還具有鄉(xiāng)政府派出機構的職能,成了實際上的農村基層“準政府機關”,政府、社區(qū)、經濟三者的黏合表現(xiàn)尤為突出,政經不分、政社不分、村治與經濟不分;村民小組是由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隊發(fā)展而來,作為農村集體經濟基層組織,是農民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等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同時也是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具有社區(qū)成員和集體成員的雙重身份,村治與經濟同樣沒有分開。
因此,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管理的現(xiàn)行做法是由鄉(xiāng)、村、組干部代為行使,村委會成了三個組織、一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綜合性組織,政府、社區(qū)、經濟三者沒有分開。村級集體經濟既承擔了行政、社區(qū)的職能,也承擔了行政、社區(qū)的管理和建設開支。這種做法容易導致集體生產經營活動受行政干預;集體組織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分散;集體經濟利益受損等現(xiàn)象的發(fā)生。
(二)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缺失
市場主體有法人和非法人之分,二者之間的權利存在很大差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的缺失,限制了集體組織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突出表現(xiàn)在農村集體組織不能在工商部門登記取得經營資格,也就不能獨立開展經營業(yè)務;不能在國家質量技術監(jiān)督部門取得組織機構代碼證,就沒有依法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的通行證,也就不能在銀行開賬號,難以從金融部門獲得貸款,不能在稅務部門申請購買稅票等。這些都使得農村社區(qū)集體組織只能依附在其他經營主體上,只能將其資產以入股、承包、租賃等方式參與其他經營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而成為難以壯大的“小矮人”[8]。
(三)土地產權關系模糊
對于農村土地所有權,我國法律規(guī)定是清晰的,《憲法》規(guī)定屬于集體所有,《土地管理法》進一步規(guī)定為農民集體所有。對于農村集體財產所有權,我國法律規(guī)定也是清晰的,《民法通則》規(guī)定: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包括法律規(guī)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集體所有的財產受法律保護。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雖然賦予了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fā)展農業(yè)產業(yè)化經營。但由于受政社不分、政經不分的影響,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仍然存在模糊的事實,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土地產權主體模糊。首先是主體認識模糊。由于農村集體組織不獨立,依附于行政機關和群眾自治組織而存在,政經不分,容易產生土地所有權人不是集體而是國家的模糊認識。其次是行使主體模糊。由于集體組織的非獨立性,加之現(xiàn)行法律體系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主體規(guī)定也不明確,集體土地所有權由鄉(xiāng)村干部代為行使的做法,行使主體變得模糊。再次是主體關系模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鄉(xiāng)、村、組三級,它們分別擁有不同的土地所有權,三者又是一種上下級關系,而且土地產權邊界模糊,使得三者之間的關系模糊不清。
二是集體與農民之間土地產權關系模糊。集體和農民對農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如何行使所有權,農民對集體所有的其他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如何行使所有權等一系列關系模糊,尚未完全厘清。
三是土地所產權不能充分行使。一方面,土地作為稀缺資源,國家對其實行嚴格的政策保護和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限制性規(guī)定明確而具體,保護性規(guī)定相對模糊抽象,加之國家征用土地制度設計不夠細致和行政干預等原因,使得集體土地所有權得不到尊重[9],有些土地限制政策甚至超越了限制的界線。另一方面,由于集體與農民之間土地產權關系模糊和現(xiàn)行的做法,使得集體和農民在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上,難以充分表達所有權人意志,挫傷了農民維護土地權益的積極性,只有當集體利益受損并影響其個人利益時,才會聯(lián)合起來共同維護,如集體上訪、阻工等。
三、發(fā)展對策
(一)政經分離
政經合一,是國家社會一元結構的產物,政企分離問題,在國有企業(yè)已經解決。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的政經分離問題,在1982年《憲法》中曾經做出過規(guī)定,要求設立鄉(xiāng)人民政府和鄉(xiāng)農業(yè)合作經濟聯(lián)合組織。但是到1984年底我國基本完成由社到鄉(xiāng)轉變時,由于全國絕大部分農村地區(qū)已不存在集體生產經營活動,所以鄉(xiāng)農業(yè)合作經濟聯(lián)合組織一直沒有建立,政經和政社不分一直是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存在的一個問題。
因此,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首先應該是解決政經分離、政社分離問題,實現(xiàn)政府、社區(qū)、經濟三者分開。通過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和村委會相分離,成為獨立的經濟組織,解決政經不分和政社不分問題,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真正擁有生產經營自主權的、獨立的市場主體。
農民專業(yè)合作社雖然也是獨立的市場主體,也能解決集體經濟的獨立問題,但存在著缺陷,即只有當集體組織的所有成員統(tǒng)一加入同一個合作社時,原集體組織才能成為新合作社組織,問題才能得以解決。但問題是根據(jù)《農民專業(yè)合作社法》之規(guī)定,同一集體成員按自愿原則,可以加入不同的合作社,這樣原集體就仍然存在,仍然不能成為獨立的經濟組織。因此,應該在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同時,還要解決原集體組織的獨立問題。
廣東南海區(qū)所推行的社區(qū)黨組織、村(居)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五分離”的“政經分離”改革,是一個大創(chuàng)新,改變了原基層黨組織、自治組織和經濟組織黏合在一起的“政經不分”管理模式,標志著農村體制改革已闖入深水區(qū),為新一輪農村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
(二)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
通過立法或修改現(xiàn)有法律,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社法人或公司法人資格,使其具有市場主體法人資格。雖然已有的《農民專業(yè)合作社法》所規(guī)定的農民專業(yè)合作社具有法人資格,現(xiàn)有農村集體組織也可以依法登記取得法人資格,但公司法人的集約化、專業(yè)化、組織化、社會化程度更高,應該讓較發(fā)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公司法人資格,成為現(xiàn)代企業(yè)。
比較《民法通則》之規(guī)定,集體經濟組織是具有法人條件的。一是依法成立。這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身問題,而是法律規(guī)制問題。二是有必要的財產或者經費。集體組織擁有農村土地,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出讓、租賃、入股,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耕地的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擔保和入股,土地作為農業(yè)生產特殊的生產資料,當然是財產,并且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中不斷升值,除此之外,還擁有公益性與經營性等固定資產,為數(shù)不少的發(fā)達集體還擁有一定數(shù)量的經費。三是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實際情況是盡管集體經濟組織不獨立但都一直保留了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至于名稱和組織機構是否符合要求,則可根據(jù)新的法規(guī)重新命名和組建即可。四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雖然國家對土地所有權有限制性規(guī)定,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入市、出讓、入股,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可以入股,同時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主要取決于法人財產,不能因為部分集體經濟組織不具有,而否認所有的都不具有。
在農業(yè)經濟多種所有制結構中,集體經濟居于主體地位,引領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方向;集體經濟組織還擁有農村土地,這是其他農業(yè)企業(yè)無法比較的優(yōu)勢;在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進程中,都應該賦予集體經濟組織公司法人資格。
(三)改革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明晰土地產權關系
造成當前農村土地產權關系模糊的原因很多,如集體經濟管理體制、經營制度、土地制度、組織治理結構等,但主要是土地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制度,實現(xiàn)了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但在當前以土地流轉為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產權關系模糊問題,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應該從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內容分離轉移到所有權上,在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重新分配所有權。
從當前農村土地產權關系來看,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使用權屬于集體成員。可以抵押、擔保和入股并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轉等權在內的土地經營權,實際上就是所有權。基于當前現(xiàn)狀,應該設立“集體土地兩極所有權”:一級所有權歸集體所有;二級所有權歸集體成員所有。
綜上所述,根據(jù)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現(xiàn)狀和存在的問題,應當采取政經分離;賦予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改革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明晰土地產權關系等相應對策,發(fā)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鼓勵發(fā)展農村集體組織經濟和農民家庭經濟;鼓勵集體組織以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鼓勵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yè)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yè)企業(yè)流轉,發(fā)展多種形式規(guī)模經營,培育新型經營主體,構建集約化、專業(yè)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yè)經營體系。
參考文獻:
[1]彭海紅.當前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特點及其發(fā)展條件、途徑[J].理論導刊,2011(11):66-69.
[2]中國農村年鑒編委會.中國農業(yè)年鑒[M].北京: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09:337-340.
[3]劉茂松.論現(xiàn)代家庭經濟實體的特性[J].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02(4):105-109.
[4]農業(yè)部經管司、經管總站.2011年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及管理情況[J].農村經營管理,2012(5):24.
[5]2011年農民專業(yè)合作社發(fā)展情況[J].農村經營管理,2012(5):28.
[6]王彥萍.關于紅旗鎮(zhèn)農民專業(yè)合作社建設得幾點思考[J].現(xiàn)代農業(yè),2012(11):66-67.
[7]李靜紅、汪曉東等.廣東農民專業(yè)合作社信息化發(fā)展策略思考[J].農業(yè)網絡信息,2013(7):123-128.
[8]鄭有貴.農村社區(qū)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地位研究[J].農業(yè)經濟問題(月刊),2012(5):22-28.
[9]祝金甫、馮莉.農村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宏觀經濟管理,2011(8):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