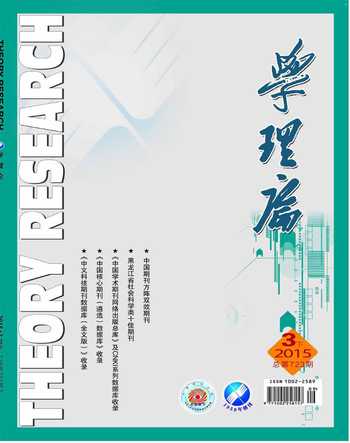淺析陳陟云《新十四行:前世今生》前五章的藝術張力
李婕穎
摘 要:“張力”對詩歌的藝術有著重要影響。陳陟云創作的《新十四行:前世今生》用連貫性特征動詞與悖論性詞組、戲劇性處境以及內含的哲學思辨,取代傳統十四行體主要用格律來構建詩歌的藝術張力。這為新十四行體詩歌創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關鍵詞:新十四行詩;張力;語言;存在主義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114-02
美國學者艾倫·退特在《論詩的張力》中提出:“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展(extension)和內包(intension)的有機整體。我們所獲得的最深遠的比喻意義并無損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說我們可以從字面表述開始逐步發展比喻的復雜含意:在每一步上我們可以停下來說明已理解的意義,而每一步的含意都是貫通一氣的。”[1]“張力”(tension)是一首詩的肌理紋路,沿著這些紋路讀者可以感受詩魂的律動。詩人陳陟云創作的《新十四行:前世今生》的張力不僅以矛盾沖突的形式展示,同時也發生于矛盾緩和階段。
《新十四行:前世今生》是廣東詩人陳陟云自2007年7月起創作的詩組。目前已完成前七章。由于缺乏十四行體的押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的節奏感,但是詩人用了更為巧妙的手法彌補,那就是以多種形式建構詩歌的“張力”。
第一層張力:連貫性特征動詞以及悖論性詞組的使用
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蘭波認為詩人應該尋找的語言是“靈魂對靈魂的語言,它結合一切芬芳,聲音,顏色,思想與思想的縱橫交錯。”[2]
詩人在《新十四行:前世今生》中運用了一系列具有連貫性特征的動詞,如第一章第一篇:
薇,帷幕落盡,已隔前年/“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東流的一江春水淹沒歷代/你我的情緣如舟。那凌波而來的/絕色女子定然是你,一路抖落鉛華遍灑/宛如落英隨流漂去/薇,今夜我靜靜看著鏡象中的你/猶陷雕欄玉砌之重圍/該推哪一扇門,方可打開你的視線/紅羅亭內醉未酣/相擁入壺成一夢/誰在前世,誰在今生/薇,今夜我內體音韻枯槁/白骨叢之處蕩出朵朵異香。
陳陟云運用了“淹”“漂”“開”“推”“入”“蕩”等動詞將詩歌“薇”意象的出場以及由朦朧到清晰,再由清晰到模糊,以及這個過程中“我”的思緒變化。而這些動詞的連慣性表現了動作并非一蹴而就,為詩人筆下的物象制造了運動軌跡(運動過程),因此上述詩句節奏就會呈現出強弱相間的特點。“薇”雖然出現了,但是與“我”仿佛隔岸相對,并且由“漂”、“抖落”等動詞的非有意性,暗示了“薇”并未注意到“我”,而“我”則希望把情感的節奏加強嘗試向“薇”表達內心熱烈的情感。因此運用了“推”、“入”等動詞,讓“我”將這份愁思淋漓盡致地傾訴予“薇”。在這首詩中“薇”節奏緩慢的出場,仿佛與“我”不曾相識,而“我”情感的遞進變化與之產生鮮明對比,這種一張一弛的節奏感為詩歌籠罩了一層耐人尋味的命定感,“薇”就在“我”面前,然而“我們”卻形同陌路。
此外,全詩多個章節運用了悖論的語言組合,為詩歌增添了相斥的藝術張力。燕卜遜認為,悖論能使詩歌迸發出一種“張力”[3]。如“白骨叢生”、“朵朵異香”(第一章第一首),“終極的愛,是未曾愛過”(第二章第一首),“構筑殘酷的優雅”(第三章第四首),“殘酷的美麗是相擁哭泣”(第三章第五首),“打印一份發黃的青春氣息”(第三章第六首),“讓真情殘酷,讓相愛孤獨”(第三章第八首),“一秒幾乎長于一生”(第三章第九首)等。強弱不同的動詞搭配形成句子間的張力,悖論語言的運用則成為詞組間的張力。“吹奏高不可及的寒冷”(第三章第三首)“吹奏”這個動詞讓寒冷的感覺更為幽遠,同時這個動作可表現寒冷的力度,并非撲面的柔和而是深入骨髓的陰冷。再如“終極的愛,是未曾愛過”,究竟詩人表述的是“愛”還是“不愛”?“走進你,就走進了痛苦,離開你,就遠離了幸福”(第三章第五篇)與上述詩句形成對應關系。詩人試圖通過悖論的語言,制造詩歌中的矛盾沖突,從而表達自己的哲學思考。
第二層張力:“戲劇性處境”的設置
除了富有質感的語言,《新十四行:前世今生》營造的“戲劇性處境”也強化了詩歌的張力。詩中具備了人物,場景,動作等戲劇要素,并通過節奏感的語言推進詩歌的矛盾沖突,因此與散文詩區分。如第四章描寫了“我”一周的生活,串聯起來即一個戲劇的場景。這場“情感劇”并非是“我”的獨角戲,“薇”也是“劇中”不可缺少的角色。“薇,周一的早晨是惺忪的早晨”(第四章第三篇)、“薇,整整一個周二的上午,一個人被包裹在‘工作的內核”(第四章第四篇),“薇,周三的雨一直在下,體內的陰暗被一道閃電劈開”(第四章第五篇),“薇,周四的一天,只有一個單向的角度,直指無限的可能”(第四章第六篇),“薇,黑是周五的底色,偌大的會議室如光感后的底片”(第四章第七篇),“薇,周六仿若一只小貓,躲在角落里”(第四章第八篇),詩中“我”向“薇”訴說一日所見,而“薇”始終沉默,甚至是冰冷的。正由于“薇”的“失語”才會讓后半部詩句中“我”的哀愁,落寞越發濃烈,同時讓“我”作為孤獨行者的形象立體化。而這種戲劇性處境推進了詩情的變化,“我”與“薇”微妙的單向度話語,化為詩歌思想內核的筋脈,張弛有序。
第三層張力:關于“存在”的哲學探索
詩中表達的思想是《新十四行:前世今生》藝術張力的第三個維度。詩人用象征性的意象探討了存在、死亡、時間、虛無、語言、內核等哲學問題,其中“自在存在”與“自為存在”的矛盾讓其張力延伸至詩歌的精神層面。如詩句中的“終極的存在,是存在背后的虛無”(第二章第一篇),探討了“存在”與“虛無”的關系:存在的本質是虛無,最大化的存在就是到達“虛無”的狀態。詩中提到的“虛無”可理解為靈魂的升華,與“肉身的存在”是不同的概念。
薩特認為“決定人的存在就是他自己的虛無化”[4]548。因此,人的存在并非指“自在的存在”,而是作為意識層面的“自為的存在”,所以“人是自由的,就是因為它在行動中表現出來的不是他自身,而是一個對自我的在場,他總是超越。”[4]548真實的存在并非是作為客觀物質的“客觀存在”而應該實現意識(精神)層面的“自為存在”,從而實現荷爾德林式的“詩意的棲居”。
第二章第三篇較為直接地表現了詩人對“存在”以及“虛無”的觀點,“沒有什么比岸上的景色和一匹馬的飛奔更為虛幻”、“沒有什么比我們的觸感和一朵花的開謝,更為虛幻。”該章節詩人集中探討了時間性的問題,按常理而言,“馬”應該是具備實體性的,然而詩人感悟到飛奔的馬具有“虛幻性”,但是這種“虛幻性”究竟是指向“馬”還是處于某個運動狀態的“馬”呢?通過“一朵的花的開謝”可排除第一種可能性。“飛奔的馬”與“開放的花”具有“虛幻性”,這是由于處于運動狀態的生物體現了一種“時間性”,并且“花”與“馬”可以被人的意識所認識與表現,因此整個運動過程也側面反映了人的意識流動,而此流動在詩歌中又是“虛幻”的,這就為詩歌意蘊內核空間營造了一種理解層面的張力:具有運動性的物體與人的意識披上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
接著詩過渡到對“自在存在”與“自為存在”的探討,即人的意識與肉體(客觀存在)的關系,以及其表現出的“我”與“他人”的關系探索。在詩歌中,“我”的肉體作為“自在存在”的表現,充滿了苦楚,所以若干詩句提到物體穿越身體,如“虛設的鵲橋穿過身體”(第一章第七篇),“箭鏃,從我們體內穿梭”(第二章第五篇),“‘歲被敲入身體”(第二章第八篇),這時“我”已把“自在存在”看的微乎其微,反而著重對“自為存在”的思考,并且這種思想是辯證的。詩歌先是表現了“自在存在”與“自為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人的一生并不能脫離二者的其一。“因而傾聽獲得雙重的意義,在生命之外傾聽一滴水,在滴水中傾聽曾有的生存”(第二章第三篇)和“如光灑下,尋找肉身”(第三章第二篇)清晰體現了“自為存在”與“自在存在”前者依存于后者然而又超越后者的關系,并通過“我”與“水”(他者)的關系中表現。“在生命之外傾聽一滴水”著重點在“水”,指向“自在存在”,“在滴水中傾聽曾有的生存”,則指向“自在存在”讓“我”“觸摸”到的“自為存在”,薩特認為“自為存在”雖然具有超越性,但是這種超越性不能離開作為主體性他人的“自在存在”,也就是我們的認識深化不能離開他人的存在而單獨存在,“我們身體——其特性即本質上是被他人認識的‘我認識的東西就是他人的身體,而我關于我的身體所知道的主要東西來自他人認識它的方式。”[4]289“我的存在”把“我”推向了他人的存在和“我”的“為他的存在”。針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散落全詩,為其整體提供了內在的動力。
這種“我”與“他者”的關系不僅表現為“我”為“物”身上,詩中更多表現為“相愛”的兩方。“邂逅相愛的人,難免是一種痛苦”(第三章第二篇),“走進你,就走進了痛苦,離開你,就遠離了幸福”(第三章第五篇),“薩特認為愛情是一種意識活動,因為愛情遠遠不止是純粹肉體的占有的情欲,所以很難成功和滿足,我和他人都是自由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愛情就是沖突。”[4]469然而,如果沒有“我”與“他人”的這種關系,“我”不可更好認識自己,只能借助“他人”的“存在”才可以超越“自在存在”達到“自為存在”。在詩中,這種對人生的思考是逐層深化的,詩人先由“時間性”引出“存在”問題,而存在的現實悖論無時無刻讓詩歌中充滿了對精神生活的思索與尋覓,在此基礎上,詩歌開始將這種抽象的生存問題以“愛情”為具體例子,而在這個具體例子中又通過“我”與“他人”細微的交流與接觸體現出來。因此詩歌的藝術張力是逐層遞進的,也是矛盾逐漸明晰的過程,這就為《新十四行:前世今生》建構了重要的思想內核。
陳陟云創作的《新十四行:前世今生》雖沒有傳統十四行體的格律結構,但其通過三種逐層遞進方式而構建起來的藝術張力不僅彌補了詩歌中缺失的音韻美,而且營造了富有生命活力的意象世界以及高度思辨的藝術空間,為新十四行體詩歌創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新批評”文集[M].趙毅衡,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8:117.
[2][法]蘭波.致保爾·德梅爾(1871年5月15日).蘭波詩全集[M].葛雷,梁棟,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
[3][英]拉曼·塞爾登.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M].劉象愚,陳保國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4][法]薩特.存在與虛無[M].陳宣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