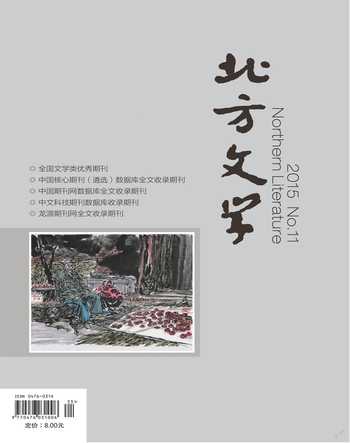淺論《山海經(jīng)》的思維特征
賈子璇
摘 要:《山海經(jīng)》是保存中國神話資料最多的一部古書,其中記載了大量奇異的事物,有對地理、山川的描繪,以及鳥獸等殊方異物的記載。《山海經(jīng)》的寫就代表著先民對世界的朦朧認知,因而具有奇異的想象和浪漫主義色彩。觀其整體創(chuàng)作思維,體現(xiàn)了顯著的“以已度物”的思維特征,通過自己的直觀感受和認知水平對當(dāng)時的世界加以描述。這樣的創(chuàng)作也體現(xiàn)了在當(dāng)時的認知和生產(chǎn)力水平條件下,出于解釋現(xiàn)實的需要,而立足于“自我中心意識”下來觀照萬物。
關(guān)鍵詞:奇異想象;以己度物;自我中心;現(xiàn)實需要
一、《山海經(jīng)》中的奇異想象
歷代以為《山海經(jīng)》為怪書。《史記·大宛列傳》中說:“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唐代杜佑《通典》中說:“《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jīng)。”[1]古人都以其記述怪誕,神靈鬼怪,在接受上也有一定的過程。從其名目來看,分為《山經(jīng)》和《海經(jīng)》,但在圖書“經(jīng)史子集”的分類中,《山海經(jīng)》并未因“顧名思義”被古人分在經(jīng)部的地理志中,而被分在雜學(xué)的子部中。
它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充滿了各種奇跡,有珍貴的礦物、神奇的植物、怪異的動物等。其中,對動物的描寫有神物和怪獸的區(qū)分,奇異的想象體現(xiàn)在這些動物是多種動物的特征組合,如在《南次二經(jīng)》中,“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等,這樣的例子在整部《山海經(jīng)》中都存在。這樣奇異的動物形態(tài)是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見不到的,除去對動物的怪異想象,在《山經(jīng)》中有礦物的描寫,數(shù)量之多超出現(xiàn)實,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感。這種奇異的想象從實質(zhì)來看是人為創(chuàng)造,而且是先民創(chuàng)造出的與現(xiàn)實完全相反的一個世界。對其中大多鳥獸蟲魚的想象,它們的出現(xiàn)會帶來征兆,通過征兆的好壞來區(qū)分吉兇。如在《南次二經(jīng)》中有,“見則其縣多放士”“見則郡縣大水”“見則縣有大繇”等。
這種奇異的想象既是背離現(xiàn)實的另一個世界,也是先民在認知水平低下的條件下試圖對現(xiàn)實做出的解釋。對于生活中的自然災(zāi)害等,社會程度不發(fā)達的先民無力做出任何的抵抗,而寄情與思維上的想象,希望存在一個社會,有神奇藥效的植物,有不死國,通過一些征兆就可以判斷現(xiàn)象,來克服徭役的繁重,克服洪水、大旱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威脅,克服對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懼。
二、前綜合思維方式
神話中對世界起源的探索源于一種渾沌的狀態(tài),唐的《藝文類聚》中引到:“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這種對于世界起源的渾沌想象就是先民創(chuàng)作神話,寫就《山海經(jīng)》的一種思維方式。列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中認為,原始思維大多數(shù)場合中不同于先進民族的思維。[2]列維·斯特勞斯卻將之相近的思維稱為“野性的思維”,并在以此書命名的書中研究了未開化人類的“具體性”與“整體性”的思維特點。[2]神話思維與原始思維是有區(qū)別的,與原始思維相對應(yīng)的是文明思維,神話思維是原始思維的高級形態(tài)。[3]
鄧啟耀先生談到:“由于神話是一種尚處于‘渾沌中的前綜合思維,后世各種思維方式的相對專一的功能在神話中依然混為一體,……成為萌芽狀態(tài)的各種功能合一的原生體、渾沌體。”[4]這種初始階段的思維方式就如同人類的兒童時期,自我也不知道自己和外界世界的界限,在心理學(xué)上被稱為思維主體與思維對象未分化的心理階段。[2]鄧啟耀先生認為:“在神話思維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中,思維主體與思維對象的關(guān)系,有實的一面,也有虛的一面;有不分化的一面,也有分化的一面。”[4]
(一)未分化下的整體性
神話思維下的神話創(chuàng)作出于思維狀態(tài)上的未分化時期,思維主體與思維對象似乎在一種虛幻的關(guān)系中合為一體。[4]而這種未分化性表現(xiàn)為一種人與自然的整體交感。人與萬物“心物合一”,自然中的現(xiàn)象必定會為自己帶來一定的結(jié)果。《山海經(jīng)》中多狀物,如某種植物具有的特性,吃了這種植物,這種特性就可傳遞到自己身上。他們認為萬物與自己一樣,有靈性,有性格,動物的出現(xiàn)必定會帶來預(yù)兆。這種整體性首先由于先民的認識水平與思維發(fā)展程度的局限,將自己與外部世界看為一體而少于改造,同時,這樣的整體性也代表著一種對自然的崇拜與畏懼,如原始人通過模仿蛙叫來祈雨[3],對于當(dāng)時還處于原始社會狀態(tài)下的先民來講,這種整體性是一種客觀的事實,他們必須依賴自然而生存。
(二)虛中有實的渾沌感
多半人認為《山海經(jīng)》中大量虛構(gòu),而在這樣的一些描繪中,也有真實的事物參雜其中。混沌思維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自然萬物在人類感知中的混沌無序[5]。就“整體”與“渾沌”這兩種感覺來講,本身就有聯(lián)系,整體性是混沌思維的一個突出特點[5]。因為視人與自然為一個整體,對于當(dāng)時認知水平低下的先民來講,很難分清自然中什么是真實與虛幻,是對自然一個模糊的認知。
要在生存條件極為艱苦的遠古時代活下去,依靠豐富的感情經(jīng)驗以獲得對事物形態(tài)、性質(zhì)、規(guī)律的某種領(lǐng)悟或洞察,比依靠想象和“幻想魔力”要大量和經(jīng)常得多。[2]這種虛大部分體現(xiàn)在對未知恐懼的幻想,對于他們未到過的地方,未能解決的某個地區(qū)的死亡傳說,他們會用奇異的想象來相信那里有怪獸,但大部分的虛構(gòu)卻來自于實際的經(jīng)驗。如虛構(gòu)的動物組合,超不出他們的認知范圍,多是雞、牛、虎等常見的動物,而這些動物是要吃東西,要繁衍的,這種虛的想象基于對實的認識,來解釋自己對未知的恐懼與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中遇到的自然災(zāi)害。
三、思維的類比性
類比的思維方式也是先民創(chuàng)造神話時體現(xiàn)出來的一個思維特征。原始先民還未形成抽象性思維,他們只能將類比推理或類比邏輯作為自己思維的重要方式[5]。這種類比基于自己直觀的認識與感知,帶有明顯的整體性和模糊性,而這種類比是有中心的,那就是先民自己。通過與自己的對比然后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和認知。這種思維的形成,是人類突破渾沌思維的一個階段,開始有了自我意識,我不同于他物的認知。比較基本的就是通過事物的外形和屬性來類比,如在《繹史》中引盤古的神話:“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fēng)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這是一種直觀類比的形象思維,通過物體的形狀相似,加以一定的想象和神圣敘事來進行創(chuàng)作。由物物類比下,發(fā)展到由人及物的類比,開始注重自己的感知與外界的關(guān)系。
(一)以己度物
原始先民以對自身的體驗為參照系數(shù),將人類的自身體驗,移情幻化到客觀事物身上。[2]基于前綜合思維方式,未成熟的思維階段,“以己度物”的思維特征屬于原始思維中的高級形態(tài),雖說依舊是一種無意識的類比邏輯,但這個時候先民開始對自己的感知有了認識,對自我有了認識,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感受認識這個世界,把這個世界統(tǒng)一于自己的認知范圍中,用自己有限的認識來解釋他們所見到的現(xiàn)象,他們認為這些現(xiàn)象也如自己的感知一樣,有預(yù)兆并且可以控制。大衛(wèi)·休謨曾說:“人們身上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意向,即認為一切生物都跟他們自身相類似,并把這些他們非常熟悉和他們完全理解的……品格轉(zhuǎn)移到每一種物象上面。”[2]在《山海經(jīng)》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在《南次三經(jīng)》中:“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還有很多“食之不腫”“佩之不迷”等此類屬性轉(zhuǎn)移的例子。
(二)以已知推測未知
先民對于世界的這種想象,大多數(shù)是基于自己已有的認知,而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進行推測和預(yù)演。這樣越是相反越是不可能的想象,立足的是他們已知的世界。只是由于他們本身的思維處于不成熟的階段,相比于現(xiàn)在用已知推測未知的科學(xué)推演,他們得出的未知結(jié)論大多有了夸張臆斷的奇異色彩,因而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特充滿想象的世界,造成了虛實互滲。
對于當(dāng)時所發(fā)生的自然災(zāi)害以及統(tǒng)治者帶來的戰(zhàn)爭、徭役等痛苦,先民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也無法擺脫,他們希望在自己已有的認識范圍內(nèi),可以預(yù)測自己的生命,用一些征兆來避免災(zāi)難。于是他們在想象的世界中,在稀有金屬易物很貴的條件下,會有全是礦藏的山,會有不死國,可以逃避死亡,會有鳳凰這樣的鳥獸為自己帶來祥瑞,也有明顯可以辨識的怪物讓自己遠離危險。他們既表現(xiàn)出了對未知充滿想象的浪漫色彩,也表現(xiàn)出了在已知世界中的弱小。
四、自我中心意識下的現(xiàn)實需要
關(guān)于先民為什么會創(chuàng)造神話,《山海經(jīng)》的成書年代以及作者都眾說紛紜。總的來說,神話是先民對未知世界的初步探索而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產(chǎn)生的一種文學(xué)形式,神話具有極強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它的創(chuàng)作不是漫無目的,而是基于一種“自我中心意識”,從自身出發(fā)去觀照萬物。這樣的自我中心意識體現(xiàn)在絕對化的二元對立中,通過二元比較突出自我中心。在《山海經(jīng)》中,有四對形成對比的國家:小人國和大人國,長臂國和長股國,女子國和丈夫國,三首國和三身國。這四對極端的比較為我們勾勒了先民所處的正常社會,突出了在《山海經(jīng)》創(chuàng)作過程中典型的“自我中心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并非自我膨脹或唯我主義的霸權(quán)論,而是先民對未知世界探索的一種方式。當(dāng)時由于交通條件不便,自然環(huán)境惡劣,他們很少能去很遠的地方,但是出于一種需要,人想要認識世界的欲望又無法隔斷,他們只能通過自己,立足于自我的生活環(huán)境來想象未知的環(huán)境與世界。
同時這也解釋了先民創(chuàng)造神話的現(xiàn)實需要,思維與存在本身就是一對矛盾運動體,作為誕生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神話是當(dāng)時先民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在當(dāng)時認知水平和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的條件下,面對自然惡劣的環(huán)境,與無法預(yù)測的自然災(zāi)害,他們試圖通過一種方式來預(yù)測,通過一些征兆來防御,加之現(xiàn)實生活的困苦與生命的短暫脆弱,都讓他們對他們面前的自然與未知世界產(chǎn)生了恐懼和敬畏感,在當(dāng)時不成熟的思維認知階段,用奇異想象來創(chuàng)造一個神話世界,解釋自己生存的環(huán)境,也是出于當(dāng)時他們的現(xiàn)實需要。
參考文獻:
[1]張陳.《山海經(jīng)》 神話敘事探研[D].西南師范大學(xué),2004,5.
[2]潛明茲著.中國神話學(xué)[M].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5,1.
[3]鮑穎.從神話思維到發(fā)散式思維的方法論革命[D].南京師范大學(xué),2008,5.
[4]鄧啟耀著.中國神話的思維結(jié)構(gòu)[M].重慶出版社,1992,1,1.
[5]王增永著.神話學(xué)概論[M].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