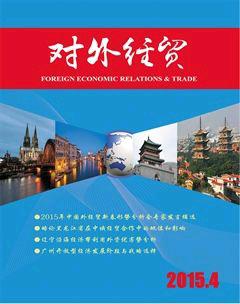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對外開放戰略
隆國強
在過去的30幾年,中國走出了一條在全球化背景下,通過不斷地擴大和深化開放來推進工業化的成功道路。但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后,并不意味著可以沿著過去30多年的老路繼續原來的戰略。主要是因為有三個重要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我們自己的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中國經濟在減速。一開始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周期性的波動。過去30年,我們經歷過好幾次周期波動。經過非常審慎的研究,特別是對國際上一些追趕型經濟發展歷程的分析,最后中央得出重要判斷,就是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常態。習總書記在2014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從九個方面,對新常態新趨勢新特點做了闡述。此前,在APEC會上,習總書記從三個方面做了闡述,第一就是中國經濟從高速或者超高速增長進入一個中高速增長;第二個就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第三個是增長動力的轉換。從過去依靠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轉向依靠創新、效率的提升,來尋找新的動力。所以,中央提出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
新常態真正的新處,需要我們改革到位,新的增長動力要到位。新常態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也就是說國家的發展階段不一樣以后,它的發展目標會進行調整。可能更多地要強調怎么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動力,怎么真正形成靠創新驅動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新增長模式。
對外開放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戰略,是適應國家發展目標的子戰略。所以當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后,我們整個發展戰略調整的時候,需要調整對外開放戰略。
第二個變化是國際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以前全球經濟的繁榮,對我們來說就是外需的快速擴張。國際金融危機以后,轉入經濟增長低迷、結構調整、格局大調整的新時代。這里面有很多挑戰,也有很多機遇,對我們這么一個出口大國來說,外需增長放緩,當然面臨全球產能過剩加劇,全球競爭更加激烈,貿易保護主義也會有所抬頭。
但是,也會有一些新的變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還得為了走出危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有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潮。過去一二十年,中國很多工程承包企業在國內市場上鍛煉了能力,在全球工程承包市場上確實有很強的競爭力。工程承包出口不簡單是獲得上千億的合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帶出去的承包設備,這些技術含量更高、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產品,是我們出口結構的變化。
再比如說,現在全球都在推進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也誕生了一些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的信息技術、新能源、美國的頁巖氣,還有生物技術等等,非常活躍,各國也非常重視。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一個真正能夠引領全球經濟走出這種危機后調整的一個大的產業。所以說,新技術革命是方興未艾,蓄勢待發,還沒有真正形成。
外部環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全球經濟貿易規則可能又處在一個新的密集構建過程中。特別是以美國主導的TPP為代表,不是簡單地推進區域貿易合作,還蘊含著很多發達國家希望推動的新的經貿規則。對中國來說,新一輪的經貿規則,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第三個變化是中國和世界關系發生深刻變化
過去30多年,我們參與全球競爭,從經貿小國,變成經貿大國,一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低成本、優質的勞動力。人口紅利支撐了對外開放,特別是出口競爭力快速提高。通過建立經濟特區,搞加工貿易,吸引出口導向型的外國直接投資。把外來投資者的技術、管理、品牌、國際銷售渠道和我們的低成本優勢,特別是制造業勞動力、藍領工人的低成本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所以我們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全球貿易排名第32位,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大國、貨物貿易大國。人均GDP從148美元到了7000美元。
我們和很多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菲律賓、馬來西亞的人均工資是中國的3倍。現在反過來了,我們是它們的3倍。我們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還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因為我們的勞動效率比他們高。我們有比較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綜合成本還是有優勢,產品質量上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如果動態地看,可能這個變化還會繼續削弱我們傳統的競爭優勢,這是發展的結果。
有沒有新的優勢在涌現?其實也是有的。人口結構也在發生很快的變化。有不利的變化,比如老齡化快速到來。年輕勞動力的結構也在變化。2000年,我們一年高考招生是108萬人,現在招700多萬,畢業700多萬大學以上的學生。我們每年有1500萬—1600萬人進入勞動大軍。原來108萬人進入高等院校,剩下還有1400多萬人可以做藍領工人。現在700多萬人去上了大學,上完大學以后,又進入勞動大軍,但他們已經不愿意做藍領工人了。勞動力市場上,藍領工人繼續招工,工資上漲得快。大學生找到一個他喜歡的穩定的體面的就業機會,很難。
在藍領工人的市場,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是勞動力流動太快,流失率非常高。流失百分之百的企業非常多。極端的企業可以到500%,一線工人換了5茬。這樣的情況有利有弊,好處是通過勞動力流動,知識在快速地擴散、快速地交換;不利就在于,快速擴散、快速流動,讓工人缺乏勞動技能的積累。企業主不愿意過多地去投資工人的培訓,培訓完就走了,培訓的費用打水漂了。當產業需要升級,需要更高素質的勞動力的時候,藍領工人的素質、技能并不能支撐這種結構的升級。所以,更好的質量、更高的技術含量、更好的服務這些有很多是需要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來支撐的。
人口紅利表現在什么地方?素質提高了,研發成本和發達國家比就有優勢。再加上國內這個大市場,從原來潛在的大市場,變成了現實的大市場。
盡管經濟增長速度從10%降到了7%, 但7%的增長就是7000多億美元的增量,相當于土耳其(全球第16大經濟體)全年的GDP(8000億美元)。雖然減速了,但基數大,對全球GDP的貢獻依然還是最高的。這就會對追逐本土市場和研發成本的投資者產生吸引力。這和以前把中國作為一個低成本加工出口基地相比,發生了很大改變。endprint
在這三個變化里,有很多挑戰,也有很多新機遇。以前的機遇主要是有利于我們擴張,有利于推進工業化規模,而現在的機遇有利于升級。
規模的變化,導致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我們自己可能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一下子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增量是全世界最多、最大。
作為一個新興的崛起大國,本身會有很多新的訴求,這些訴求包括要對全球的規則制定發生影響力。
國際社會也會對我們有新的期盼。這就是大家聽到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美國人說,你不能搭便車等等。其實種種對中國的這些聲音,都反映了我們的規模擴張、新興大國的崛起,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改變。這和其他東亞經濟體、四小龍在追趕階段與世界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小經濟體只面臨結構升級的問題。大經濟體除了結構的變化,還有一個規模變化帶來的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挑戰。
新常態下對外開放戰略目標的調整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同時能夠牢牢地把握好這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帶來新的機遇,就必須調整我們的對外開放戰略。
過去30年,我們最主要的是利用外部的市場和資源,來加速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這個目標是歷史性的,我們已經完成了。
下一個目標是什么呢?可能是兩個。一個是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結構升級,尋找新動力的要求。另一個就是通過調整戰略,和國際社會形成良性互動、互利共贏的關系,確保中國能夠和平崛起。否則,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處理不好國際關系的話,就是孤獨的大國,很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新常態下對外開放戰略調整的重點
第一,制造業,要在全球的生產價值鏈上實現升級。
第二,服務業。要著力解決服務業擴大開放,提升國際競爭力問題。我們的服務貿易發展也很快,在全球是進口第三位、出口第四位。這些年服務貿易的逆差也是快速地在擴大,整體競爭力還比較弱。服務業發展滯后,競爭力提升不快,歸根結底,就是對內管制過度,對外開放不足。我們絕大部分的服務業都有著非常嚴格的管制,這就大大妨礙了服務業的技術創新。國內管制很多,開放肯定是不足的。所以三中全會特別強調,服務部門要加快開放,要采取負面清單的管理辦法。所以這是結構調整下一步擴大開放的新重點。
第三,對外投資。短短的10年時間里,中國一躍成為一個重要的投資體。既是利用外資的大國,又是一個對外投資的大國。2003年對外投資只有285億美元,到了2013年已經達到1078億美元。
很多企業需要在全球來整合資源,通過在全球的投資,可以控制一些戰略性的資源,來保證國家的資源安全。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就是通過對外投資,特別是并購,來整合全球資源。通過并購來獲取技術、研發、品牌和國際銷售的渠道。商務部一直推進品牌戰略,品牌戰略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培養自主品牌,把它變成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另一方面是通過并購獲得品牌。這個過程會是相當漫長的。
第四,金融業。要加速推進金融開放。金融開放也是相對滯后的,金融開放搞不好,會帶來系統性的風險。所以管理開放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搞不好有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但是這并不能夠成為金融開放長期滯后的理由。怎么開放,國內首先要改革,為金融開放創造好的條件和基礎,包括匯率機制的調整、人民幣國際化等等,內容非常豐富。
第五,國際經濟貿易關系。就是營造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貿易關系。在多邊層面上,需要參與全球治理,引導規則,向希望的方向逐步地去調整。不是說把現有的經貿規則推倒重來,沒這個想法,也沒這個能力。在區域層面上,加速推進和其他國家區域貿易安排,除了FTA,很多功能性的合作也不應該忽視。除了封閉的FTA以外,開放的自由主義也可以繼續去推進。比方說“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有很多區域安排在里面疊加,這種區域合作、功能性合作,也有FTA的疊加。此外,在雙邊層面上也有很多工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