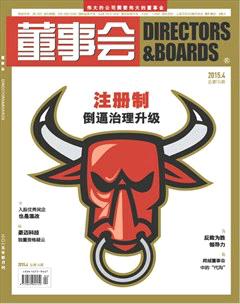公司治理的“緊箍咒”
梅慎實


“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是“行政授權”還是修改《證券法》“權力法定”?是中國證監會“單審制”還是中國證監會與證券交易所“雙審制”?時至今日,關于注冊制改革的具體模式,盡管市場各界尚存在爭議,但不管改革取何路徑,都將倒逼公司內部治理重大變革、提質增效。
政府還是市場主導
有人認為,我國目前仍然屬于新型的、轉軌時期的市場階段,經濟發展不全面不均衡,發展質量不高,尚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重要轉型時期,各種市場經濟力量互相牽制互相博弈。如果只是盲目地完全效仿美國式的證券注冊制,相當于一下子打開了證券發行的大門,短時期內可能會導致證券發行的繁榮,但從長遠來看,由于注冊制是基于對一個理性投資者的信賴基礎上的制度,而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屬于投機型的市場,投資者缺乏理性投資觀念和較成熟的投資知識,爆炸式的證券發行可能使投資者陷入投資困境。
因此,為了早日推出股票發行注冊制,應該擯棄完全的、理想主義式的全盤西化的路線,從實際國情出發,使體制既能符合國情,又能促進市場發展。這就需要根據不同的資本狀況制定多層次、全方位、多階段的發行體制,規范各環節的手續,提高整體效率和質量,在循序漸進地向更自由開放的注冊制過渡的同時,要注意加強對證券市場的政府監管力度、提高監督質量,即采用“政府主導”的、中國證監會“單審制”注冊制模式。這種觀點認為注冊制改革需要所謂的“穩步推進”,主張在對現行《證券法》小修改的方向下,采取“行政授權”的方式引進注冊制。
也有人認為,我國的注冊制應在全面修改《證券法》的前提下,重塑中國證監會和交易所的角色,實行“市場主導”的、中國證監會與證券交易所“雙審制”、“權力法定”的、符合國際慣例的注冊制。
核準制中,證監會能夠決定一個公司是否可以公開發行股票與上市。證監會核準公開發行股票,就意味著同意了該股票上市交易,因為核準制下實行的是股票公開發行與上市連續進行的體制。但在注冊制下,理論上說一切公司只要提供了真實有效的信息都可以上市,這時就會要求投資者對這些信息進行篩選,投資者會謹慎比較各個公司的優劣再進行投資,那些業績差、希望通過尋租賄賂政府上市融資的企業都會被淘汰。
其實,注冊制與核準制一樣,本質上是國家層面立法的制度安排和頂層設計問題,不存在實質障礙。要說障礙,那就是大家應該把思想認識真正統一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上來,切實消除部門利益、本位主義,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我們要使股票發行從“父愛式”的篩選變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由發展式放養。也就是說,在注冊制下,公司股票公開發行與上市的決定權在于市場,想要參與市場競爭的公司如果不遵守游戲規則就會被市場淘汰。
在美國,股票發行成敗的關鍵不在政府,而在市場。即使注冊生效,也不意味著高枕無憂,市場如果對企業不認可,也可能發行失敗。一個典型案例是,2012年,中國租車公司神州租車準備在美國上市,成功注冊后,卻遭遇市場環境的突變,市場認購意愿低于預期,最終不得不撤回發行申請。因此,我國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首要任務,是實行股票發行與上市決定權分開的、證券交易所差異化的上市條件體制。
先改革還是先立法
目前,關于注冊制立法還有“先改革、后修法”和“先修法、后改革”之爭。
現行《證券法》第48條規定“申請證券上市交易,應當向證券交易所提出申請,由證券交易所依法審核同意,并由雙方簽訂上市協議。”這表明上交所原本就應該履行“上市審核”的法律職責。因此,不必等待《證券法》的修訂,證監會有權對IPO審核權進行重新分解,在不改變證監會現行法定“核準”地位的前提下,證監會可以采用行政授權方式,授權證交所設立“上市委員會”,負責對IPO申報企業進行實質性審核,并將證交所的“上市審核”環節前置于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發行審核”之前,證監會發審委將以此為依據,進行最終的“形式審核”,并由證監會簽發是否核準IPO的文件。
在現行《證券法》尚未修訂前,采用這種過渡性辦法及措施安排,可以讓注冊制改革的大部分工作變通先行,而不需要坐等《證券法》的漫長修訂,這樣就可以規避、調和《證券法》修訂前某些條款與現實改革的所謂“沖突”。
當然,基于注冊制在證券發行前的放松,良性的市場發展要求對公司在證券運營過程進行全面而嚴格的監督,同時配備完備的法律體系來規制證券發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責任問題。注冊制的實施與市場的法制體系、懲戒機制以及投資者保護水平高度相關,前端放松需要后段加強。從境外經驗來看,在實施注冊制、放松準入環節限制的同時,需要不斷健全配套法律法規,不斷加強中后端監管執法和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力度,這是注冊制得以順利實施的有力保障。
必須指出的是,注冊制首先考驗的是證監會的監管能力,實行注冊制不僅意味著證監會對IPO審核權力的下放,更是證監會職能的改變,使證監會從IPO的審核者變成IPO的監管者——證監會和交易所要圍繞注冊制制定“三張清單”,即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哪些是必須做的,哪些是做不了要交給市場的,哪些是由發行人自行負責的等,都要一一明晰邊界。修改《證券法》時,要結合注冊制的形式審核要求,嚴格區分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職權,避免證監會的“管得過寬”、“管得過細”的情況,減少我國證監會需要審核的實質條件,把審核資源重點放在提高招股書披露質量上。此外,還需要重新修訂證券法、公司法,以及民法與刑法中有關證券犯罪的相關條款,嚴懲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欺詐上市、信息造假等證券犯罪行為。
倒逼內部治理升級
盡管對于注冊制改革的具體模式,市場各界還存在爭議。但不管采用什么模式,都將對公司內部治理產生重要的倒逼作用,促進后者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內部治理水平。
曾經在納斯達克市場上市的網易公司,在國內算是一個大公司,但是它卻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上經歷了“退市風波”,沒有經受住“一美元退市制度”的考驗。原因很簡單,就是網易公司的財務年度報表沒有及時提交,只是晚提交了幾天。其實這事放在中國不算什么,對于網易這樣一個大公司,業務繁忙,報告肯定也復雜,晚提交也情有可原,況且只是晚了幾天而已。但是這事放在美國股市,就算你是網易,也要讓你退市。美國的股市極其重視一個公司的信譽,要在美國股市玩,首先就要遵守完完全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就要完全接受投資者的考驗。因為一個公司一旦上市,就不是你幾個大股東的私事,而是要放在陽光下,讓大家考驗考驗。從這一事例上,我們就可看出,美國的股票上市制度,盡管管得很少,卻極其有效率。
中國現在的狀況,是“進股市嚴,出股市難”,沒有形成有效的股市競爭和流動機制。人們經常能看到的現象是有很多公司被貼上了“ST、PT”的牌子,出現了大跌的情況,但過不了多久,這些公司會奇跡般好轉,出現新高,其實這里面牽涉了多方面的利益。
但隨著嚴格并多元化的退市機制的建立,企業“金剛不壞”的上市資格破除,企業在市場檢驗和約束下無法通過舞弊實現圈錢、賣殼與利益輸送的企圖。企業需要建立正確的價值導向、治理理念,確立符合市場經濟運作的結構和策略,提高運營效率。那些未能實現市場化經營、嚴格管治的公司,可能會因經營業績不佳而被資本市場淘汰。
提高信披質量,擬上市公司、中介責任加重
美國信息披露體現了重大性原則,詳細得當,有利于投資者把注意力放在重大信息上面,方便投資決策。披露規則從投資者角度制定,全面細致,公開透明,指導性強。證券監管部門嚴格監管披露文件外散布信息影響市場,確立披露文件的中心地位。各種風險在充分披露后,由市場賦予一定的折扣率并反映在定價中,投資人基于自己的投資策略和風險偏好進行選擇,與政府的態度無關。在公司上市之后,注冊制根據“市場有效”及“信息不對稱”理論,更加要求企業進行持續信息披露,讓市場第一時間掌握信息,使投資者能夠迅速作出決策,也為有盈利能力的企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向注冊制改革推進的過程中,中國證監會主要對擬發行公司審查是否合規,信息披露是否全面、真實,而不作投資價值判斷,這樣才能逐步從投資價值的實質審核向信息披露的形式審查過渡。
這就要求,擬上市公司將面臨市場中介機構未來更加嚴格的審核,如果擬上市公司出現虛假陳述等問題,擬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都要受到處罰。中介機構若發現擬上市公司有問題而不作為,包括券商、律所、會計師事務所等都有責任。通過落實發行人和中介機構的主體責任,推動各方歸位盡責,強化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提升發行人信息披露質量,抑制虛假信息、包裝上市,全面揭示可能存在的風險和可能影響投資人決策的信息。
內控水平要求更高
公司制度的誕生是形成當今繁榮市場最大的貢獻者,沒有之一。如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財富都是由公司創造并由其掌控的,一個好的公司治理環境所帶來的利益是無窮的。作為上市融資者,公司的誠信、實力等都是至關重要的,這一切要反饋到股票發行中還依賴于公司的治理結構。發行的主體是公司,上市融資價值也在一個個公司實現,只有在優良的公司治理結構中才能真正發揮資本的作用,促進整個金融市場的壯大。為提高擬上市公司透明度,加強對公眾投資者的保護,擬上市公司將面臨健全公司治理及內控方面更強力的監管。
為此,擬上市公司除了在治理、內控上更注重合規外,可考慮引入獨立第三方對公司治理進行風險評析,推進內部控制規范體系建設,不斷提高治理水平。
董監高治理責任更大
過去中國證券監管方面的立法,實際上是有缺陷的,比如出現訴訟情況,如果公司敗訴,往往是由公司出面賠償股民的損失,從法理上來說,公司本身就是屬于股東的,如果拿公司的錢賠償股東的話,實質上等于股東自賠,而且對于那些沒有得到賠償的股東來說更加不公平。
在境外,如果公司敗訴,通常會追究董事高管人員的個人責任。可以預期,今后將從《證券法》角度而不局限于過去的《公司法》角度,進一步細化和強化董監高的義務和責任,形成完備、配套的責任追究機制。這意味著,注冊制施行后,公司董事、監事、高管個人將面臨更大的責任。董事、監事、高管一方面需要勤勉、審慎地履行信義義務,一方面也需要采取恰當的救濟方式,例如購買董責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