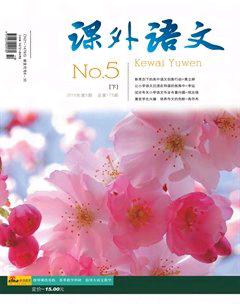新常態下的高中語文創客行動
黃立婷
【摘要】新常態下的高考,英語分值在降,語文分值在提,不要指望在“特殊加分”上做“手腳”。高考題目,不會太繁、不會太難、不會太偏、更不會太舊,許多時候能力、創意比知識更重要。
【關鍵詞】高中語文;創客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A
全面和系統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帶動許多一線教師的創客行動。顛倒課堂的資源和標準化的考試,知識的“天下為公”,歡樂的共同分享,成為許多創客的追求的主旋律。在這樣新常態下,師生更多在瞄準新方向、尋找新樂子,啟迪智慧,點亮人生。學習也是休息,讓教育生命舒展而茁壯。
一、課前調研不走秀
課前調研不僅是我們教師,更多時候我們要把視角投向學生,師生共同的調研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和導向,但有一點是共通的——“要讓每項成績的背后都有一種推動力”(愛因斯坦)。對于高中師生來說,最重要的動機是工作和學習的樂趣,最重要的方法是踐行。我們在教育中,常講尊重,常講以學生為主,而客觀上,我們的教師常常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本上,而對于學生的情況真的知之甚少,或者認為沒必要去做那些“無聊”的功課的。而事實,我們的一線教師發現,只有針對性地教學,師生才會不做或少做無用功的。筆者在教學《伶官傳序》前,讓學生先自己做些相關的題目,在調查中,發現有幾個學生連歐陽修的這篇文章看都沒看,就看著老師給的題目,從網上直搜答案見題填空的,然后,才去做一些實戰性的題型,可以想見這樣做下去,表面是省時省力了,真的到實踐中,是要“吃癟”的。于是筆者引導他們先將文章讀熟,其實文章本身也不長,連標點在內,也就四百零幾個字符。讀熟了,背會了,快的同學十分鐘就搞定了,這時再去做作業,其收獲就決非網絡所能相比的了。真的把書讀進心中的,他們對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之理會有更多的解讀與鏈接。“莫能與之爭”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粗讀感覺“身死國滅”好像就是“溺愛伶人”之故,再讀就會發現“逸樂”的危害,三讀就會聯想到北宋的時勢,想到歐陽修的身份,想到他這樣寫對朝政的觀點,會想到文章的針對性,四讀聯系自己,會發現其更具有普遍性,如果自己正在那里“糊弄”作業的,或許會驚出一身冷汗的。這樣好的文章不獨是道理的深刻,更有語言的委婉,氣勢的充沛,“嗚呼”起筆,“也哉”收尾,以嘆始終,其中的韻致在多次的反復嘆詠之中,讓我們感受到委婉的言辭,《伶官傳序》“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沈德潛)篇幅小,起伏不小,發人深省,皇帝能接受,百姓能理解。
在我們調研學生的時候,發現問題最好單個交流,針對性地引導,輕易不要把發現的問題直呈其事,有時方法的不當,正確的觀點就會得不到圓融地貫徹的。
二、課中教學不跑偏
反思我們的課堂教學,許多時候我們是用專業教育力圖讓學生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考試的機器,學生考得高了,教師和身價也跟著抬起來了。而“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惡鮮明的辨別”卻相對的被淡化了。過分地分數競爭,常會扼殺語文本身所依存和蘊集的那種精神。“教育應當使所提供的東西讓學生作為一種寶貴的禮物來領受,而不是作為一種艱苦的任務要他去負擔。”(愛因斯坦)。教學的不跑偏,第一是觀念,學生學語文,是來“受禮”的,受禮的心情是愉悅的,是感恩的,帶著這樣的心情去學習,自會和文本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和教師之間有一種和諧感。聽說有的學校高考一結束,學生就去撕爛語文教科書,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教育者深思的事情。第二是對癥,這種對癥一是學生中到底有什么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要引導學生做一個什么樣的人;二是對文本的把握,這個文本的本身有哪些地方需要著重的內化,哪些地方可以和我們的生活進行對接,分析文本,不止于文本,還要分析當時的作者、當時的背景,文章也是當時的情勢。同樣,文章是要拿來用的,分析文本,要和學生的實際進行對接,和學習文本時的時勢對接。學以致用,要培養成學生對于語文的那種誠摯的興趣和對真理的追求。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學習,學生才會有理解的愿望。
三、創意踐行不停歇
對文本的學習,要解決的不僅是課本的本身,更多是要解決類似的問題,對接生活中的問題,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表明自己的觀點等。文本是一種點亮,一種智慧的啟迪。學習《地球上的王家莊》(見蘇教版高中語文讀本必修三)我們不獨是引導學生去解釋文中“我”所產生的許多問題。更重要的是思索作者為什么會產生這許多的新奇問題,文中的我處于一種什么背景之下,什么樣的思想狀態。分析文章中懂的和不懂的,我們會發現許多問題是作者懂的,而文中的“我”是不懂的;有作者懂的,而我們不懂的;有父親懂的,而“我”不懂的。這些都反映了小說審美的規范,讓人物越出常規,而當我們掩卷沉思之后,發現一切都在不平衡中,凸顯出了心靈差距。
對作品的分析,更多是要在于引用與創新,學生學了《地球上的王家莊》后,有的寫了自己家鄉的世事變遷,初寫者常常變成了寫實,沒有把握小說的諸多特點。筆者在教學時,聯系高中所學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等小說,讓學生歸納分析小說的一些寫作方法,然后,自己創編微型小說,有的寫了《雙簧》,寫退休之后的高官爺爺,如何定位在過去的聽匯報、拍板子的角色中,后來子孫們如何演出雙簧讓這個爺爺享受著做官的那一份感受。再后來爺爺自己發現,他說的話沒幾句被執行下去的。這才發現,過去他下屬所在的工作就是“雙簧”。
每部作品有其個性,每類作品有其共性,我們在教學中,要將這些個性和共性的東西讓學生在比較中鑒別,鑒別是為了引用、創新,在創新中生成,這才是創客的企望。
(編輯:龍賢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