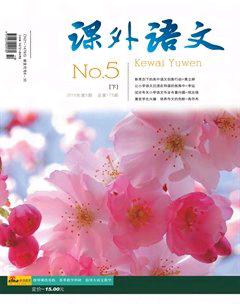多視角觀照下的高中語(yǔ)文教學(xué)
王媛媛
【摘要】本文的多視角觀主要論及師生間的觀照、讀者和作品之間的觀照、讀者和作者的觀照。多角度的觀照遠(yuǎn)不止于此,但從上述的觀照中,我們可以得到不少啟迪。
【關(guān)鍵詞】高中語(yǔ)文;觀照例談;目標(biāo)建構(gòu)
【中圖分類號(hào)】G63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筆者作為高中的語(yǔ)文教師,是常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批評(píng)類的文章的,艾布拉姆斯教授就有四要素的提法——社會(huì)、作者、作品、讀者。如果以作品為中心,向社會(huì)、作者、讀者三方發(fā)散,就構(gòu)成了一個(gè)三角形,當(dāng)然,社會(huì)、作者、讀者與作品的交流常常是雙向的。下面筆者就以《看蒙娜麗莎看》來例證高中語(yǔ)文教學(xué)多視角觀照吧。
一、我看學(xué)生,學(xué)生看我
反思自己的教學(xué),我看學(xué)生,曾經(jīng)認(rèn)為現(xiàn)在的學(xué)生是享樂的一代,指望他們主動(dòng)地去求學(xué),還不如我們自己去找好答案,找出重點(diǎn)來讓他們深入地記憶模仿。以這樣的觀點(diǎn)去看學(xué)生,結(jié)果學(xué)生是省事了,他們就等著教師去剖析,你講了,他們也就懂了,你講到的,他們會(huì)了,你沒講到的,或者講到的但變化了,他們就一頭霧水了。為了讓所講的部分,保證一點(diǎn)兒分?jǐn)?shù)也扣不到,教師不得不強(qiáng)迫自己:“我講的一定要百分之一百的正確,不然的話,一失全失——全班都等著我的標(biāo)準(zhǔn)答案呢!”有了這樣的心態(tài),就自然而然地對(duì)自己的能力產(chǎn)生了懷疑,每遇到問題一定要去教參找答案,教參上找不的,第一反應(yīng)是打開手機(jī)網(wǎng)搜一下,看了一家不敢肯定的,再搜幾家,有時(shí)同一問題出現(xiàn)了不同的或相反的答案,常去請(qǐng)同行去幫忙定位,教得很累,學(xué)生學(xué)得也很累。
學(xué)生看我每次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他們?cè)跐撘颇幸彩怯龅絾栴}第一反應(yīng)就“百度”,上課時(shí)學(xué)生經(jīng)常拿出手機(jī)來上網(wǎng)找。有的不知不覺地就被手機(jī)上的特別畫面鉤去了注意力,發(fā)現(xiàn)了這一問題之后,班主任就反對(duì)學(xué)生帶手機(jī)到班級(jí),不讓學(xué)生帶這些工具上課堂,教師就要做出榜樣,這就逼著教師和學(xué)生多做一些課前的功夫,但真的在課上出現(xiàn)了一些具體的問題,還是要認(rèn)真地去思考、去推斷。
最近筆者在上《看蒙娜麗莎看》這篇課文時(shí),學(xué)生看到課題第一反應(yīng)就是這個(gè)題目什么意思啊?按我們的語(yǔ)言習(xí)慣應(yīng)是“看蒙娜麗莎”或者是“蒙娜麗莎看我們”,熊秉明寫的“看蒙娜麗莎看”這樣的用法是不是一種修辭手法?如在過去,筆者會(huì)毫不猶豫地將答案全盤托出的。但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xué)生必是充滿依賴的學(xué)生,愛因斯坦說過,“只有個(gè)人才思考,從而能為社會(huì)創(chuàng)造價(jià)值……要是沒有能獨(dú)立思考和獨(dú)立判斷的有創(chuàng)造能力的個(gè)人,社會(huì)的向上發(fā)展就不可想象……”學(xué)生只有讓他們?nèi)プ约核妓鞔鸢福麄儾拍苷业揭环N成就感,他們才會(huì)有一種體驗(yàn),有一種責(zé)任感,有一種主人的感覺。學(xué)生在閱讀中、在思索中、在討論中發(fā)現(xiàn)《看蒙娜麗莎看》兩個(gè)“看”形成了無窮的循環(huán),觀賞者看蒙娜麗莎,蒙娜麗莎也在看觀賞者。進(jìn)一步地探究,有的學(xué)生說這幅畫不單只包含肖像畫,還包含了男性對(duì)女性的一種愛慕與想象,畫中的少婦神秘地勾起嘴角,也勾起世人結(jié)于他有了眾說紛紜的猜想……文章中像這樣的句式還有很多:如“她誘惑你的誘惑”“她的注視要誘導(dǎo)出你的注視” “他在這可怕的眼光中一點(diǎn)一點(diǎn)塑造這眼光的可怕”,有的同學(xué)由此提出了個(gè)人的語(yǔ)言習(xí)慣問題——是不是作者熊秉明對(duì)這類的句式有一種特別的愛,帶著這樣的問題,讓學(xué)生繼續(xù)去尋找論證,發(fā)現(xiàn)還真的如此,有的學(xué)生說,熊秉明在臨“老”之前,就寫過這種句式的詩(shī)。
二、我看作品,作品看我
筆者初次看《看蒙娜麗莎看》心里是有點(diǎn)抗拒的,文章看是好看,只是太深?yuàn)W,看了全文勉強(qiáng)知道,題目中的前一個(gè)“看”是我們讀者也是熊秉明先生的動(dòng)作,后一個(gè)“看”是蒙娜麗莎的動(dòng)作。如果我來寫這一篇文章就只能寫出“我”的“看”法,而蒙娜麗莎的看法我是不會(huì)去寫的——因?yàn)槊赡塞惿目捶ㄎ以趺粗馈M不是鬧玄乎。然而再讀文章,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作者高超的語(yǔ)言駕馭能力和敏銳的洞察力。“她眼角射過來的光,比我們這些欣賞者更專注、更鋒銳、更持久、更具密度、更蘊(yùn)深意。”何以為證?——蒙娜麗莎有少女的誘惑和少婦的誘惑,“如果那眼光里有秘密可尋,那就正是我們的彷徨、惶悚、緊張、狼狽。”文章寫到這里,按常人的思維此文寫到這里已經(jīng)是大功告成了,而作者熊秉明寫到這里,他還有思考,常人是用眼睛來看的,他是用“心”去解讀的,他不僅分析“誘惑”,而且要分析這兩個(gè)“看”之后的“蠱惑”,獨(dú)特的藝術(shù)、另類的解讀、意味深長(zhǎng)的結(jié)尾,我仿佛看到兩個(gè)名人:一個(gè)是達(dá)·芬奇,他創(chuàng)造了名畫《蒙娜麗莎》;一個(gè)是熊秉明,他創(chuàng)造了名著《看蒙娜麗莎看》。名畫名著相得益彰。
我看作品,由不解到敬佩,作品看我,它知我心,解我疑,釋我懷,更提升我們審美的情趣。
三、我看作者,作者看我
看完了作品,忍不住猜想起作者來,他是一個(gè)什么樣的人呢?白發(fā)、長(zhǎng)須、一個(gè)很睿智的老人?要不他的文章寫得沒這么深沉。是一個(gè)帥小伙子?要不,他哪有那么多的激情“春意”?還有可能就是作者看過達(dá)芬奇的真跡,蒙娜麗莎真的有一種顛覆的能量,然而去看過這幅畫的很多,有這一份藝術(shù)賞鑒的功力和緣分的人卻沒有幾人了吧?
看蒙娜麗莎沒有多少黃金的裝飾,看熊秉明先生的文字沒有多少華麗的語(yǔ)言,但那一份心靈的震撼卻是永恒的。作者看我,他也知道我們對(duì)這微笑的顧盼是永遠(yuǎn)達(dá)不到的極限。
總之,在高中語(yǔ)文教學(xué)中,就如《看蒙娜麗莎看》的蒙娜麗莎,我們?cè)诳此苍诳次覀儯覀冊(cè)诳串嫾遥嫾乙苍诳次覀儯覀冊(cè)谧x《看蒙娜麗莎看》,作品《看蒙娜麗莎看》又何嘗不是在解讀我們的內(nèi)心情結(jié)呢?作為教師,我們有更多的觀照,我們師生的觀照、師生對(duì)文本的觀照等等,在多重的觀照中,我們有時(shí)不必糾結(jié)于紛擾。如手表走時(shí),大的認(rèn)時(shí),中的認(rèn)分,小到讀秒。盯住一個(gè)目標(biāo),認(rèn)準(zhǔn)一個(gè)方向,“穩(wěn)坐中軍帳,可捉飛來將”。
(編輯:龍賢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