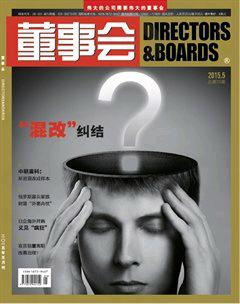吉百利:跌倒在“岔路口”
Morten+Bennedsen
當英國人眼睜睜看著吉百利被美國食品巨頭卡夫收入囊中時,無論如何也感受不到一絲“甜蜜”。這家堅守貴格會傳統的家族企業到底是如何淪為了全球化的犧牲品呢?
2009年8月下旬,英國巧克力制造商吉百利的董事長羅杰·卡爾(Roger Carr)收到一條信息,來自美國最大的食品商卡夫公司的董事長兼CEO艾琳·羅森菲爾德(Irene Rosenfeld):“我下周在英國,一起喝杯咖啡吧。”誰曾想,這一低調樸素的邀約卻拉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盤亙全球新聞報道頭條位置的收購戰的序幕。
吉百利董事會很快就拒絕了卡夫食品102億英鎊的收購要約,但這不能阻止羅森菲爾德在最后關頭選擇公開收購,一場拉鋸戰就此展開。一方是享譽186年的老牌家族企業,以其貴格會傳統以及積極參與社區服務而聞名;另一方是卡夫,一家在美國煙草巨擘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羽翼下快速崛起的食品業新秀。
英國媒體非常不滿這項收購提議,工會公開舉行專門活動表示反對,甚至英方政府官員、包括首相,都被卷入了關于這場收購的辯論中。諷刺的是,恰恰英國的反壟斷立法阻止了幾年前吉百利購買糖果公司朗特里(Rowntrees)的計劃,才給卡夫鋪平了道路。
投機基金決定命運
隨著收購計劃公布,吉百利股價從5英鎊飆升至8英鎊。
彼時,美國人掌握著吉百利50%的股份,而英國人持有的股份占比僅為28%,很多投資者都想賣掉手里的吉百利股票。對沖基金迅速介入,大肆購買吉百利的股份,持有量從5%迅速增加至31%,并且向羅杰·卡爾表示很樂意以20便士/股的收益出售手里的股票。
由于確認這場收購已經成為既定事實,卡爾無奈地選擇“見好就收”,提出了8.5英鎊/股的收購價格。對此,卡爾解釋道,“我是受雇于股東們的,必須做出能給他們帶去最大價值的決定……這是我的責任。”
而在私下里,卡爾卻有自己的想法。“這個新的商業系統似乎在竭力創造一種公平環境,然而,結果似乎是給了短期投機主義滋生的土壤。”卡爾之后向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闡述了對沖基金在這場收購戰役中的角色:“資本主義無疑是有效率的,卻不一定合乎情理——一些只持有股票數周的人決定了一家公司以及其他很多人一生的命運。”
家族持股膨脹后遺癥
這場收購并非突如其來。吉百利的股權結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就出現變化。當時,歐洲巧克力制造的領軍企業雀巢試圖買下陷入困境的英國品牌弗萊(Fry),弗萊家族選擇與吉百利合作,成立了大英可可和巧克力公司(British Cocoa and Chocolate Company)。此舉令吉百利公司內家族成員持有的公司股份翻番。
之后的十年里,歐洲巧克力市場面臨來自全球的競爭。美國公司搶占進入歐洲市場,推出了按數量而非分量計價的新品種;同期,收購了瑞士巧克力工廠的雀巢則開始在英國大力推廣大塊巧克力。吉百利也制定了相應策略,在公司的伯明翰和薩摩戴爾工廠啟動了一項投資周期15年的項目,以擴大生產規模:實現日產100萬條牛奶巧克力和200萬條什錦巧克力。在此期間,吉百利牛奶巧克力的價格下降了70%,公司雇傭人員則增加了1萬。
20世紀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定量配給令吉百利工廠的產量被迫降低,公司的一些現代化工廠也轉換用途,以支持戰爭。戰后,電視機的普及促成了巧克力市場的繁榮,也讓很多公司發現,百年的聲譽與客戶忠誠度竟然可以被一場策劃完美的電視宣傳顛覆。
在市場競爭激烈焦灼的那個年代,保羅·吉百利(1959年到1965年任吉百利董事長,是公司創始人約翰·吉百利的曾孫)還面臨著另一個艱巨挑戰:家族持股不斷膨脹。20世紀60年代早期,持有吉百利公司股份的家族成員數量增加到數百人,而其中僅有10人真正參與公司經營。持有股份的非經營人員與管理人員都急于將手中的股份變成真金白銀,迫使公司不得不考慮上市。1962年,吉百利董事會同意進行IPO,吉百利也第一次走出家族,不再受到家族的直接控制。
IPO之后三年,保羅·吉百利任期屆滿,其36歲的侄子艾德里安上任。艾德里安意識到公司100多年來依托貴格教派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些過時;以協作為基調的管理方式往往意味著決策的緩慢低效,他希望建立責任明晰的管理條線。最重要的是,艾德里安想要改變公司的發展戰略——原有的單純依賴可可粉的業務模式太容易收到攻擊。他還計劃擴張公司的業務版圖,增加經營的食品部類。
1969年,吉百利兼并了軟飲料公司史威士(Schweppes)。這對于傳統的貴格教派公司實屬不易。
成王敗寇“岔路口”
彼時,吉百利已經成為一家年營業額2.5億英鎊的公司,相當于雀巢的三分之一。不過兩者存在一個本質區別,這使得來自瑞士的雀巢更具優勢。雀巢擁有雙重股權結構,記名股票只出售給瑞士公民,能有效阻擊各類敵意收購。
而吉百利缺乏這種反收購保險機制,此外,掣肘于英國反壟斷立法,吉百利也不能收購弱小的英國對手朗特里來擴大規模、尋求自我保護。反觀沒被約束手腳的雀巢,在1988年以25億英鎊的價格成功購得朗特里,為公司爭奪英國市場建立了根據地。
“那是一個岔路口。”多米尼克·吉百利(1983年到1993年任吉百利CEO,1993年到2000年任吉百利董事長)認為,“本是英國成為世界巧克力業領袖的機遇期,可惜公司沒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2000年,多米尼克退休,他是家族中最后一個參與吉百利經營管理的人。那時候,家族信托股份占公司全部股份的比重只剩下不到1%。
公司分拆引火燒身
2007年,美國億萬富翁尼爾森·佩爾茲(Nelson Peltz)通過他的對沖基金——特里安基金管理公司買下了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3%的股份,并向股東們提出一個簡單易行且回報不錯的方案:分拆公司的糖果業務和軟飲料業務。如果不分拆,公司的總價值在120億英鎊上下,如果分拆,史威士價值70-90億英鎊,吉百利則價值90億英鎊。
大家都很清楚,這一分拆會令吉百利曝露在遭遇收購的風險之下。事實上,單獨的糖果業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香饃饃。只是迫于股東壓力,最終吉百利采納了佩爾茲的計劃。2007年,吉百利史威士董事會同意拆分公司。那真不是一個好時機。2008年春,全球金融危機襲來,分拆成本猛增至10億英鎊,相當于吉百利史威士總價值的1/10。2009年下半年,吉百利就收到了卡夫食品的收購要約。
對吉百利家族最后兩任董事長艾德里安和多米尼克來說,吉百利最終被美國人收購走實在是“一場悲劇與災難”。“180多年歷史就這么湮滅了。”多米尼克表示,“曾經引以為傲的公司最佳實踐標桿、領航180余年的燈塔,就這樣輕易地消失了。”
來源:歐洲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