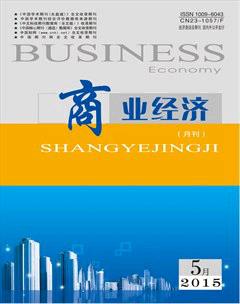國際金融中心格局變化和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張天桂


[摘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金融發展呈現新趨勢;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更加激烈,格局正在博弈中變遷。經濟發展及其所產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發展的內在原因和持久動力;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基礎以及由此形成的國際金融實力,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終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撐。盡管面對新興經濟體政府推動型國際金融中心越來越大的挑戰,倫敦、紐約自然形成型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依然相對明顯。
[關鍵詞] 國際金融中心;格局變化;傳統;發展
[中圖分類號] F831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urs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velopment trend has emerged.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s more intense and the situation changes with the competi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atural demand brought by the growth is still the internal cause and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strong and steady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rength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are the base for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Though challenge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driving by governments of new economic bodies are increasing, London and New York, two natur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still have competition strength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change of situation, tradition, development
隨著經濟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日漸加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全球金融環境的動蕩一直未能完全平復。一方面,在世界各國為應對危機而不斷反思的過程中,發達經濟體一向推崇的發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質疑,國際金融發展呈現出相應的新趨勢;另一方面,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相對變化,尤其全球經濟戰略布局向亞太地區的轉移,使國際金融中心格局展現出相應的新變化。盡管來自新興國際金融中心的挑戰日漸增大,無論倫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還是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IFCDIndex)”均表明,倫敦、紐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尚無可能被撼動,強大的國際影響力也很難在短時間內被趕超。
一、國際金融發展的新趨勢
金融的過度創新和對虛擬經濟的放松監管,被視為引爆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為應對危機不斷推出各種救市措施的同時,發達經濟體對自由市場的態度有所改變。為規避系統性風險,保障金融穩定和安全,不但對金融市場進行積極的干預,而且著手對既有金融監管制度施以改革,加大金融監管的力度,進一步展開國際金融監管協調,推動金融監管體制的一體化。無論被稱為“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格的金融改革法案”的美國2010年《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還是英國的《2009年銀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抑或歐盟2010年一致通過的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2012年“折中”通過的有關對銀行業進行統一監管的協議,其目的均在于此。G20、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在努力構建國際金融監管的新框架。前者于2009年倫敦峰會明確,加強金融監管,創立更強有力、更具全球一致性的跨國合作及高標準監管框架;發表《加強金融系統》宣言,同意以嶄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替代金融穩定論壇,并擴大監管措施的適用范圍,不但將信用評級機構納入其中,而且首次覆蓋對沖基金,要求今后監管措施必須能夠阻止過度杠桿,采取行動反對“避稅港”等不合作行為。后者于2010年形成《巴塞爾協議Ⅲ》,上調資本充足率下限標準,要求設立“資本留存緩沖”,并在信貸增長過快時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進一步加強對銀行業的風險管理。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監管將更加強調相互之間的超主權合作。
而改進和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管理,降低對不適當風險融資的依賴,阻止過度冒險與投機,無疑在其中處于極為重要的地位。2014年G20峰會將加強風險防范作為3大目標之一,明確其所承諾的金融監管改革包括加強對衍生品市場的監督。盡管金融創新是國際金融快速發展的關鍵,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實體經濟的發展,但虛擬經濟畢竟源于實體經濟,即使相對獨立也還需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為實體經濟服務。經受過度創新、脫離實體經濟獨立發展洗禮的國際金融市場,在監管之下逐漸調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使衍生產品等金融創新立足于傳統基本業務,既能防止經濟過度虛擬化又可促進實體經濟切實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也因此呈現出與實體經濟更為緊密結合的新趨勢。2011年7月,紐約市長在“未來的紐約”發布會上指出,太過依賴華爾街經濟是紐約發展的桎梏之一;為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紐約5個行政區多元化戰略還包括生物科技、現代制造業和小型企業。endprint
二、國際金融中心格局的新變化
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發展以及地位變化,在極大程度上以自身及其隸屬國家/地區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并與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相適應。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實力此消彼長,尤其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和國際地位提高、全球經濟戰略布局向亞太地區轉移,均在國際金融中心多元化、多層次格局的變化中有所體現。
倫敦金融城自2007年起每年3月、9月發布GFCI,已成為目前國際公認的最權威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盡管局限性在所難免,其還是通過相對全面的連續性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金融中心格局的變化。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前4位排名相對穩定,倫敦、紐約地位牢固,是國際金融中心格局毋庸置疑的核心。在2009年9月也就是危機爆發后一年的排名中,中國的深圳、上海均進入前10,分別以695分、655分位列第5和第10,深圳更是首次入圍即登前10榜單;上海還在2010年9月和2011年3月、9月連創新高,以693分和694分、724分達到第6位和第5位,2012年3月以687分排名第8;此后二者均未能再出現在前10榜單之中。從2013年9月、2014年9月、2015年3月的排名可以看出,美國經濟的緩慢復蘇,不但使紐約首次超越倫敦拔得頭籌,而且前10之中還占有3席,舊金山、波士頓相對穩定,芝加哥、華盛頓在第10位上下稍有波動;歐洲經濟仍未能走出泥潭,前10中僅有倫敦和蘇黎世入圍;亞洲經濟尤其東亞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占有4席,除傳統的香港、新加坡、東京以外,首爾自2012年進入前10榜單以來一直名列其中,并在2012年9月以685分上升到最高的第6位,2013年、2014年、2015年得分均在700分以上。這顯然與2007年9月的排名已有很大不同(見表1),來自亞洲尤其東亞的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逐步提升、地位日益鞏固,在國際金融中心格局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歐洲除倫敦繼續領先、蘇黎世相對穩定外削弱之勢較為明顯。
表1 倫敦金融城GFCI排名
注:根據Global Financial CentresIndex(1-17)整理而成。
新華-道瓊斯IFCDIndex報告自2010年開始發布,以其對國際金融中心成長性的首次關注而受矚目。2014年報告中,名列“成長發展”要素前茅的是上海、東京、新加坡、紐約、倫敦、香港、北京、深圳、巴黎、迪拜,歐洲2個、美國1個、亞洲7個(見表2)。在總共發布的5期報告中,前10位尤其前6位相對最為穩定,在地域分布上已呈現相對均衡的態勢;與GFCI一樣,紐約、倫敦無可爭議居于前兩位,只是二者的座次剛好相反;東京的位置比GFCI靠前,位居全球第3;香港在2013年才剛剛超越東京來到全球第3,2014年就不僅被東京反超,還首次排在新加坡之后僅列第5;而上海始終位于前10之列,已由2010年的第8、2011年到2013年的第6再進一步,與香港并列第5。尤其需要強調的,與GFCI相似,國際金融中心的位次變動具有較為明顯的規律,歐洲整體下降,亞太及北美均有所提升。除“成長發展”要素評價一直穩居第一外,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金融服務業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為基本目標的金融制度的不斷創新不無關系,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服務水平”要素、由“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子要素構成的“國家環境”要素評價均大幅提升8位,“綜合”排名首次進入前5之列。香港則在“環境”要素評價排名中座次下滑8位,首次跌出前10之列;“成長發展”要素評價,與新加坡提升2位不同,下滑4位列第6。而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的2014年全球競爭力排名,香港也自2005年以來首次跌出三甲之列,同樣被新加坡超越、下降1位至第4。
三、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式創新和功能演變:關鍵要素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初同樣為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緩慢而長期的自然結果。但隨著其對國家/地區經濟推動作用的日漸增強和在國際戰略中重要地位的日益顯現,政府逐步介入自身金融業的發展,開始通過規劃有意識地鼓勵和推動本國/地區有條件的城市超越一定的發展階段快速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因此轉化為一種自覺的人為結果。即,與反映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相互關系的需求反應和供給引導理論相對應,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包括自然形成型和政府推動型。前者由強大的經濟實力所推動,資金需求拉動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經濟和金融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結果;這也是為什么最初的國際金融中心通常產生于發達經濟體,倫敦、紐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通常集國際經濟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于一身。后者由政府強有力的金融政策所推動,資金供給推動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在經濟和金融尚未發展到相應水平、由政府抓住機遇創造并改善其必要條件跨越式前行的人為結果;這也是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離岸金融業務的興起,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中美洲島嶼國家產生了包括新加坡、巴哈馬在內的各具特色的政府主導型國際金融中心,并逐步促成多元化、多層次的國際金融中心格局。由此可見,正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金融的創新,由自發轉向自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完成了自身的創新演變:不但于既有自然形成型之外增添了政府推動型這一創新模式,而且在國際金融中心隨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政府這一人為因素的作用還在增強;即使自然形成型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政府也加大了政策扶持和監管引導的力度。需要強調的是,政府推動型最終要以經濟和金融自身的快速發展為根本基礎,市場和政府相協調正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所實踐。
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簡而言之就是國際金融資源的聚集和輻射,主要包括金融信息集散和價格發現、資源優化配置及風險管理,分為金融市場中心、結算中心、信息中心、管控中心;同樣是在發展中為適應新的需要而逐步提升和拓展,即,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不斷演進。最初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提供貨幣兌換、貿易貨款結算和金融中介;國際金融中心所聚集的金融資源的種類和規模不斷擴大,投融資功能顯現并日漸增強;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倫敦國際金融中心適應世界經濟發展對美元的需求,推動歐洲美元市場的迅速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跨國資源配置功能進一步突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分散日漸增加的由經濟金融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國際金融中心的風險管理功能不斷發展與完善。endprint
無論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式創新還是功能演進,經濟發展、金融自由和創新、制度的適宜供給都是其極為關鍵的要素。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實力和腹地經濟,即經濟規模的深度和廣度,是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發展并葆有競爭力的關鍵依托和動力源泉。金融自由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重要基礎,而金融創新既是國際金融中心模式創新得以實現的重要條件,也是其功能演進的根本途徑。制度的適宜供給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模式創新最終得以實現的決定性因素,還是其功能演進市場作用得以強化的外部推動力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推進,尤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方興未艾,經濟腹地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大倫敦、大紐約金融中心圈已現雛形。
四、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共性因素與基本條件
自2010年IFCDIndex發布以來,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在5項要素評價中有3項,即“金融市場”、“服務水平”、“國家環境”要素排名一直穩居前兩位;“產業支撐”要素,紐約位列榜首,倫敦也在2012年超越東京上升到第2位;即使唯一“欠缺”的“成長發展”要素,紐約、倫敦也均在前7之列,2012年更是僅僅排在上海之后居第2、第3位。
就形成模式而言,倫敦、紐約均屬自然形成型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就類型而言,倫敦、紐約均屬功能中心,是“一體化”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就發展而言,倫敦、紐約均屬自由放任、開放競爭理念的積極踐行者,是金融創新最為重要的策源地。除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信息便利、社會政治環境穩定等通常特征外,綜觀倫敦、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和變革,經濟強盛、貿易發達、實力雄厚,貨幣強勢、金融自由、體系完備,是其得以形成的共性因素;順應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以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取向,適宜適度的金融創新和政策支撐,自然漸進,是其強化競爭優勢、創造相對優勢持續前行的基本條件。
無論倫敦還是紐約,其所隸屬的國家都是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崛起的那個時代最為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全球對外貿易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自發選擇、自由發展、自然結果,市場發揮主導性作用,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過程注定相對較為緩慢。雖然1880年美國就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紐約才正式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是在這一相對漫長的時間里,美國建立起現代金融制度,發展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美元也被廣泛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和借貸,金融國際化程度大幅提升、聚集和輻射功能兼備,完成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需要的積累。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又增強并拓展了自身的金融聚集和輻射功能,進一步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強化了美國的全球霸權。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顯然,從這一角度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轉換不可避免地與國家經濟實力的興衰、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倫敦、紐約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際經濟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本幣的國際化加速了國際金融資源的聚集和輻射,國際貨幣的強勢地位毋庸置疑。直至20世紀50年代,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變,而改變的原因同樣是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使國際金融中心不必完全依賴國內資金的供給,進而得以相對擺脫對國際經濟中心的依附;倫敦正是以此為契機,通過適時的金融體制改革,在國際經濟中心和本幣地位相對較弱之時重新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除頒布《2009年銀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并于2013年成立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和審慎監管局外,隨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日益提升,英國再次“盡全力讓倫敦位于全球金融創新的最前沿”。不僅密切關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還繼續扮演先鋒角色:2011年把打造人民幣離岸市場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2012年4月啟動倫敦金融城建設人民幣業務中心計劃,2014年10月成為首個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的西方國家,2015年3月在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中率先正式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由中國發起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倫敦國際金融中心面對歐債危機困擾依然顯示出良好的穩定性和持續的發展潛力。盡管如此,經濟發展及其所產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發展的內在原因和持久動力;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基礎以及由此形成的國際金融實力,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終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撐。而國際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一定的鎖定效應。尤瑟夫指出,不管繁榮還是蕭條,國際金融中心往往能保持很長時間,即使暫時落后也能快速趕上。
[參 考 文 獻]
[1]劉蘭香.巴塞爾III初定一級資本充足率底線增至6%[N].21世紀經濟報道,2010-09-14
[2]陶君道.國際金融中心與世界經濟[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
[3]李清娟,等.華爾街時代:紐約國際金融中心演變及發展趨勢分析[J].科學發展,2013(10)
[4]高長春.戰略金融:國際金融中心生存報告[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5]覃劍.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新趨勢及展望[J].海南金融,2014(5)
[6]尤瑟夫·凱西斯/陳晗.資本之都:國際金融中心變遷史(1780-2009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7]賀瑛,等.國際金融中心比較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
[8]余秀榮.國際金融中心歷史變遷與功能演進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
[9]包蘊涵.倫敦攜手人民幣強化金融中心地位[N].中國經濟時報,2014-09-15
[責任編輯:王鳳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