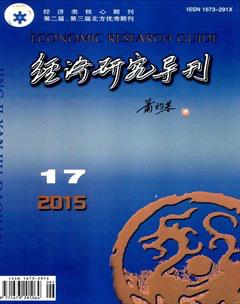淺析“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理論
江婷
(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 外國語分院,浙江 ?海寧 ?314408)
摘 要: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哲學界對于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一股新思潮,以廣松涉、望月清司等學者為代表,學術研究成果甚豐。在簡要介紹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過程和核心內容的基礎上,試對其特征進行分析,并探討其在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對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借鑒指導意義。
關鍵詞:張一兵;日本新馬克思主義;廣松涉;望月清司
一、何為“日本新馬克思主義”
“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是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的一個比較新潮的學術概念。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和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相比,它究竟“新”在何處?下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就這一概念進行簡要論述。
(一)概念的提出和爭議
“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是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提出的一個概念范疇,用來指認戰后日本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廣松涉、望月清司、平田清明等學者為代表的一支具有特殊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它與追隨前蘇東的日本共產黨傳統理論家們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有著本質的區別,強調在同當代學術思潮的對話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1]。
這個概念自提出以來,一直在國內學術界頗受爭議。反對方的代表人物是清華大學韓立新教授。韓教授主要提出兩點理由:一是簡單地將廣松涉等人的理論與日本其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論區分開來是不恰當的,它們之間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有相互交融的部分,應都歸納到“日本馬克思主義”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中。二是在“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確立的情況下,一下子就使用“日本新馬克思主義”一詞不妥[2]。
張一兵教授將“新”字加入命名中,是為了突出這支哲學流派內涵上的特殊性,以區別于其他流派。張教授在強調特殊性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它當然也和其他學派一樣具有共性。而韓立新教授爭論的重點主要在名詞之爭,對于概念的內涵并沒有太多的論述。筆者認為,盡管韓教授對于命名的具體用詞的質疑是合理的,但并不影響我們在學習和討論的過程中使用這一概念。所以,下文的論述都將以張一兵教授所提出的“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為藍本。
(二)“新”在與傳統教條主義的抗衡
如上文所說,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是“在同當代學術思潮的對話中堅持和發展”起來的。結合時代背景來看,當時的馬克思主義領域的主流學術思潮主要有兩支,前蘇東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這里主要指斯大林式的意識形態話語)和西方“人本學”的馬克思主義(人本學馬克思主義是當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國內很多學者認為該理論在根本上已經背離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前者對對亞洲國家的共產黨理論家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本亦不例外。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無一不對教條式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而對人本學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則是因人而異的。其中,廣松涉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人本主義;望月清司在反對教條的同時隱性認同人本主義。他們分別代表了日本新馬克思主義中的兩類理論邏輯[2]。由此可見,區分“日本新馬克思主義”與其他流派主要取決于其對傳統教條主義的態度。
張一兵教授認為,廣松涉(1933年—1994年,日本的哲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1949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年輕時曾活躍參與日本社會各項政治運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青年馬克思論》、《唯物史觀的原像、》《馬克思主義的成立過程》、《資本論的哲學》等。——選引自日本維基百科“廣松涉”詞條,賀譯。)堪稱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廣松涉的全部學術思想是很龐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其進程中第一個非常出彩的主要邏輯模塊”。“反對和拒斥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的教條主義邏輯構架,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起點。”這“代表了一種異質于傳統斯大林式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日本戰后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作為上個世紀中多馬克思主義學者主要他性鏡像的前蘇東的意識形態文獻學構架,被廣松涉毫不留情地罵得狗血噴頭。廣松涉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起步于斯大林教條主義大寫意識形態他者的解構,這注定使他成為與理論意識形態上追隨前蘇東的日本共產黨正統理論家的‘教條主義相異質的一代新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望月清司等人的思考往往是對廣松涉這種突破的理論的回應。”[3]
二、“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
關于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理論特征,在上文中已經進行了闡述,即與追隨前蘇東的日本共產黨正統理論家的“教條主義”相異,強調在同當代學術思潮的對話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更進一步論述,兩派代表學者的核心觀點又有不同之處。
(一)廣松涉的理論特色
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廣松涉的核心思想是用“物象化”批判來發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廣松涉把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中的人本主義異化論邏輯的批判性否定,與一個全新的邏輯詮釋結合了起來,即物象化的邏輯。”[3]廣松涉主張,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為分界點,馬克思的思想是從異化論向物象化發展的。馬克思在《188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使用了黑格爾的“異化論”概念(黑格爾的異化論,指既為實體又為主體的絕對精神的自我異化和自我恢復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來闡述私有財產的產生過程,但未能說明勞動的異化到底是怎么產生的。與此相對,《德意志意識形態》將基于分工勞動的社會關系視作歷史的基軸,以此擺脫了黑格爾的異化論。這個轉換是由實體主義是階段向關系主義世界觀的轉換。然后,廣松涉在這個詮釋的基礎上大膽進行衍生,創立了自己的一整套涵蓋“物·社會文化·歷史”等領域的“物象化”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選引自日本維基百科“物象化”詞條,賀譯)。
(二)望月清司的理論特色
望月清司的核心理論是“市民社會論”,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進行了一番史無前例的全新詮釋。望月并不承認后來列寧等人提出的并為后來中日等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界所廣泛接受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社會歷史發展五分法,而是立足于馬克思本人所持的“資本主義以前的人類社會共同體可以分為亞細亞、古典古代、日爾曼三種類型”。望月認為,“所謂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就是說明‘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過程的理論。”“馬克思對歷史的描述從宏觀上來說就應該是‘共同體→市民社會→社會主義這樣一個三階段,它們分別對應過去、現在和未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則是對這一歷史發展趨勢的揭示和證明。”[4]
三、“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啟示
日本新馬克思主義具有反對教條主義的積極意義,在其特色理論的構建上也有一定的創新精神,但它最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鑒的,更在于它的方法論。
(一)回歸原典
廣松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始于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文獻的復原整理。“雙聯頁排印、重現刪改蹤跡、再加馬克思、恩格斯文字的異體標注,產生了經典文獻出版史上第一個復原構境式的經典文獻物……這開啟了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思潮中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理論激活和問世。在手稿性文獻編輯的復原構境出版物的開創性這一點上,廣松涉功不可沒。”[3]
我們再來看看望月清司的情況。上文已經說到,望月清司提出“市民社會論”的原點,正是由于他立足于馬克思的原始文本,而非后人的解說。我們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經常會接觸到“雖然馬克思本人并沒有明確提出社會發展五步論,但應該說馬克思的論述中已經包含了這個想法”,對此望月清司提出了質疑:真的是這樣嗎?在仔細研讀馬克思的原文之后,望月得到的答案與大眾是大相徑庭的。
回歸原典,就是指回歸到原始的典籍,不輕信后人的注解,而回歸到原文、甚至是原始手稿里面去找答案,從原始文件的蛛絲馬跡中尋找線索,因為只有原典,才能最準確地代表原作者的意圖。經過列寧、斯大林等人的加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部分內容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易容,這些改變究竟是否全部體現了進步,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派的學者們對此提出了質疑。他們經過考察馬恩的原始典籍,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創新見解。無論他們的新見解具體到底有多少價值,這種實事求是、尊重原典的做法無疑是一項值得推崇的學術規范。
(二)厚積薄發
厚積薄發,是指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無一不具備非常豐富的知識背景,他們并不是單單研究馬克思的,而往往是在通曉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近代科技以及擁有實際斗爭經驗的知識大背景下,來研究馬克思主義。這與我們國家的很多同志一輩子只讀“紅色經典”的學習方法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一門孤立的科學,而是與其他學科都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沒有相對完整的知識背景是不可能真正讀懂馬克思主義的,這也就是前蘇東和我國早期陷入教條主義的原因之一。
上文中已經提到,廣松涉的全部學術思想是很龐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是其中的“一個模塊”,其余在他思想中同樣舉足輕重的還有現代自然科學和當代西方哲學。“在長達三四十年的執著的理論思考進程中,先后有馬赫、愛因斯坦、量子力學、康德、馬克思、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格式塔心理學、生態學甚至后現代思潮等重要學術資源不斷滲入到廣松涉的思想構境之中。”[3]如果不熟悉黑格爾的理論,廣松涉是不可能透徹看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歷了一個從遵循黑格爾到擺脫黑格爾的過程。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中,沒有分清“異化”和“物象化”這兩個概念、將它們混為一談的人,正是由于沒有讀懂馬克思師承的黑格爾。
(三)與時俱進
讀罷日本新馬克思主義代表學者們的論述,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無論“物象化論”還是“市民社會論”,它們的時代感都非常敏銳。抓住當紅熱點、探討現時需要,是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建立者們在方法論操作上給予我們的非常重要的啟示。
“市民社會”一詞由來已久,19世紀中葉以后曾一度被人們忽視,直到二戰結束后,這個概念又在西方再度流行開來[5]。但是西方學術界對它的解說并不完全適用于東方社會。直到望月清司出現,“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作為一個范導性原理”來看待和研究市民社會問題,“突破了傳統的機械決定論模式”[1],有助于東方國家從更加因地制宜地運用這個理論。
(四)三點方法論之間的關系
他們思維的跨度之大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他們的出發點是原始典籍,終點是當代熱點,中間搭建“越洋大橋”的是學者本人博大的知識背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上述三點方法論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呈現出一個(下轉16頁)(上接13頁)合理的過程。缺少任何一環,這場博大精深、深入淺出的思維構建就不可能完成。
四、總結
日本新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有關它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或褒或貶,各持一方。例如,在第四屆廣松涉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王代月和黑龍江大學江海波質疑望月清司的“市民社會論”能否直達馬克思思想深處;中山大學劉森林指責廣松涉沒有注意到盧卡奇對“物象化”和“物化”兩個概念已經做出的區分;還有上文闡述過的清華大學的韓立新教授亦表示“日本新馬克思主義”一詞用語不妥。但這些批判在日本新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深厚根基面前終顯薄弱,逃不出名詞之爭的意味。要想對其做出更有力的批判,恐怕還需要苦下一番工夫。它究竟功過如何,以后歷史自然會給出評說;對我們普通學習者來說,它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其中那些難能可貴的學術精神。
參考文獻:
[1] ?周嘉昕.“日本新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市民社會與國家暨第四屆廣松涉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哲學研究,
2010,(1).
[2] ?“日本馬克思主義”還是“日本新馬克思主義”?(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04-06.
[3] ?張一兵.廣松涉: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11).
[4] ?韓立新.望月清司對馬克思市民社會歷史理論的研究[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9,(4).
[5] ?鮑景華.市民社會基本概念梳理[J].中共四川省委級機關黨校學報,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