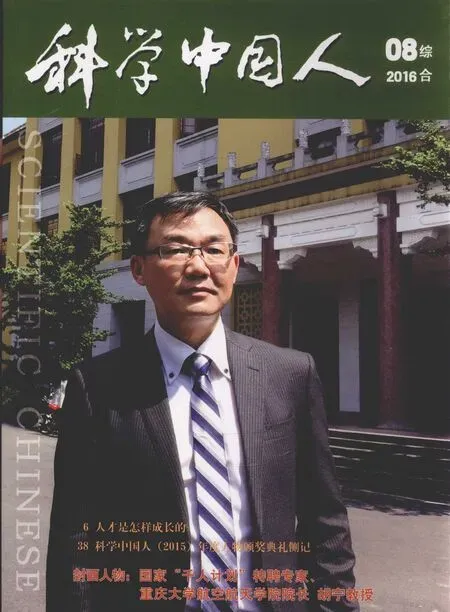尋找一個切入點,激活一堂語文課
陳建忠
重慶市華鎣中學校
尋找一個切入點,激活一堂語文課
陳建忠
重慶市華鎣中學校
俗話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的,它是在告訴我們語文文本解讀的多樣性。
這也是語文不同于其他學科教材的一個顯著特點,它幾乎是一個擁有無數(shù)教學可能的信息載體。所謂“一篇課文可以有一千種教法”,也可以說是一種客觀事實。那一千種的教法中,作為教師的我們又該選擇怎樣去教呢?
在傳統(tǒng)教學中,教師循規(guī)蹈矩,從背景、段落劃分、段意歸納、語言賞析到主題探究,面面俱到,這樣只會導致“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局面和課堂教學的低效。
那么,我們該如何有效引導學生快速進入文本,實現(xiàn)教學效益的最大化呢?
我認為我們語文教師應該在文本上做文章,鉆研文本,找準文本的切入點,靠它去引領(lǐng)學生從整體上去把握課文,從語言文字上去感悟作者所表達的情感,讀透文本,使閱讀教學更富實效。
接下來,我將結(jié)合自己近階段與同事們集體備課過程中得到的種種收獲,特別是基于如何找準文本切入點、提高教學有效性進行的理性思考和探討,談談自己對這一問題的實踐與反思。
一、從文章的標題入手
文章的標題就是文章的中心意思的體現(xiàn),一般情況下我們能從標題刊出文章的主要意思,描述的主要情況,以及解釋的中心思想等。標題的制作是作者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可想而知其具有的意義有多重,標題的形式內(nèi)容不同,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也就不同,一般情況寫從標題中,能表現(xiàn)出所描繪的事物,所屬發(fā)的內(nèi)容等。而且還可以從題目中看到文章的主旨,從而加快學生對課文的理解。例如學《南州六月荔枝丹》這篇課文中,根據(jù)題目的設計我們就能知道文章所講述的是什么內(nèi)容,文章通過對荔枝的描述,以及引用大量的古詩詞來闡釋荔枝的珍貴與特點,更有利于學生對于課文的理解。同樣在《大自然的語言》這篇課文時,就可以根據(jù)題目設計這樣的問題:大自然會有語言?大自然的語言是什么?研究它有什么意義?
我曾看到一篇郭初陽老師執(zhí)教的《愚公移山》,開始就請學生關(guān)注課文標題,并親自板書“愚公移山”四字,書寫過程中特意突出“山”字的大和“愚公”兩字的小,讓這四個字形成更為合理的排列。緊接著便提出四個問題讓學生思考:第一,山是怎么樣的?第二,愚公是怎么樣的?第三,“移山”,“移”的過程是怎么樣的?第四,最后的結(jié)局又是怎樣的?這四個問題分別從“山”“人”“過程”“結(jié)局”等方面指向記敘文的各要素,成為閱讀這篇文章的有效抓手。這樣的文本切入不但使學生正確把握了文本的主要內(nèi)容,建立起了對文本的整體感,也為引出下面重點要教的內(nèi)容進行了預熱。
二、善于抓文中的“文眼”
“文眼”它可以是文章中的一句話,一個觀點,一個細節(jié),或是一個矛盾點、爭議點……,我們在教學中就要深入文本,去發(fā)現(xiàn)和抓住它。
如《背影》一文就可以抓住“淚”作為文章的切入點。文中的重點就是寫到作者的淚,第一處回到家時“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第二處看見父親買橘子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第三處父親買橘子回來,“我趕緊拭干了淚”,第四處看見父親的背影混入人里“我的眼淚又來了”,第五處結(jié)尾讀信時“在晶瑩的淚光中”。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遇到動情處,五處細節(jié)描寫,分別為傷心之淚、感動之淚、擔心之淚、牽掛之淚、思念之淚,從而感受到作者父子情深。
例如在一次《范進中舉》的習題課講解中,我把講解的切入點放在了范進的岳父為什么是一個屠夫,作者在這一設置的過程中有什么安排?通過這篇文章的學習,和人物形象的分析,能否結(jié)合這篇文章的人物特點聯(lián)想一下我們?nèi)粘I钪械默F(xiàn)象。這樣的切入點,也顯然區(qū)別于其他老師授課的切入點,學生一聽到這個問題,第一感覺就是要重新的閱讀課文,并且分析他的人物形象。學生們通過相互的合作對問題進行分析,從“屠戶”這一職業(yè)特點入手,分析出了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和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現(xiàn)象以及個人的精神狀況、有些同學甚至還聯(lián)想到了《水滸》里鄭屠這一人物形象。有時候老是應該去善于發(fā)現(xiàn)文章的切入點,從不同角度入手,就能發(fā)現(xiàn)新的事物,同時還能幫助學生加深對文章的理解。
三、從文章的主旨句深入
中學語文教學中存在著大量的記敘文,一般記敘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書法作者的情感,表達自己的思想。所以這些文章的主旨句就常常是一些抒情的句子。老師只要做到將主旨句找出來,并對其加以分析解釋,幫助學生理解文章內(nèi)容,就能使課堂的教學順利的進行下去,并且起到吸引學生注意力的作用。以魯迅的《故鄉(xiāng)》為例,在教學時,首先讓學生從全局出發(fā)理解文章的內(nèi)容,即小時候的故鄉(xiāng)與長大后的故鄉(xiāng)。、然后,抓住文章的主旨句。再對學生進一步引導:“小時候的閏土與長大后的閏土有什么區(qū)別?故鄉(xiāng)的美好在哪里?“讓學生帶著這個問題再去看書,學生自然就能理解文章為什么要如此行文,對作者的情感思路也就清晰了。
如《盲孩子和他的影子》的這篇文章蘊含著多種主題:首先對于盲孩子我們作為正常人應該幫助他們。其次就是教育孩子們要熱愛生活,感恩生活,保持一個良好的精神狀態(tài),你怎么對待生活生活就怎么對待你。再就是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主動去幫助他人,同時得到自身的升華。
四、以插圖為切入點
課文中所配的插圖也是語文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能充分利用好這個部分,就可以使之成為學生閱讀理解文本的拐杖。與文字相比,色彩艷麗,富有視覺沖擊力的插圖更能在第一時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引發(fā)他們的好奇心和積極思考。
在教學杜甫的《石壕吏》時,考慮到學生們對當時戰(zhàn)爭的感受過于抽象,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很難引起他們的共鳴,于是就讓學生先通過插圖自主創(chuàng)設情境,從圖中找出詩歌里所提到的人物。這樣的按圖索驥是富有趣味性的,學生們自然表現(xiàn)的興致勃勃。他們很容易的判斷出那兩個守在門口,橫眉怒目,氣勢洶洶的是“吏”,而站在他們對面手指比劃著的清瘦老太是“老婦”,牽著馬站在一旁正關(guān)注著事情進展的應該就是作者本人,躲在屋內(nèi)、靠窗屏息靜聽的則是“老婦”的兒媳。至于文章開頭提到的“老翁”早已“逾墻走”,自然是不可能出現(xiàn)在畫面中的。
當然,解讀文本的切入點還可以選擇其他途徑,但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都必須建立在教師本人對文本智慧的閱讀之上。因為唯有智慧的閱讀才能產(chǎn)生智慧的教學,教師才能有自己獨到的發(fā)現(xiàn),進而設計出高效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往往高屋建瓴,思維容量大,能引發(fā)真正有效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學有所依,學有所思,學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