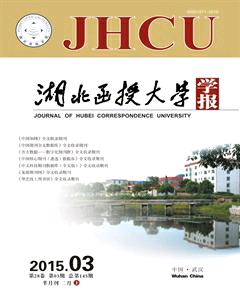弗·伍爾大小說《達洛維大人》中的女性意讀
向家佳
[摘要]弗吉尼亞·伍爾夫是英國著名意識流小說作家,她本人即為女性,筆下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她作品中傳達的女權主義觀念和女性解放意識都十分強烈。尤其是在其代表作《達洛維夫人》中,讀者可以明顯感覺到女性意識對角色建構潛移默化的影響。
[關鍵詞]弗·伍爾夫;克拉麗莎;女性意識
[中圖分類號]1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03-0182-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89
[本刊網址]http://www.hbxb.net
一、弗·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意識
弗·伍爾夫是歐洲女權主義作家中的先鋒人物,她在女性意識寫作和女權主義評論方面都頗有名望,這源自于她自身的女權意識。伍爾夫年少時被兩位同父異母的哥哥施暴,遭受性虐待,導致成年后的伍爾夫難以對男性產生愛意,她是一個女同性戀者。身份與社會角色的特殊使得伍爾夫對女性本身的解讀越來越深刻,女性意識的覺醒也就隨之而來。
伍爾夫筆下的小說中,有很多女性人物形象,其中不乏女性意識的縮影。但她比女權主義者更高明的地方卻在于,她不僅僅將角色定位到“女性”這一封閉成分,而是在情節中更關注作為“人”,作為有靈魂和感知的“人類”的一員去建構角色,關注人類的命運和人生的意義。這樣就使伍爾夫的小說形象和主旨都得以升華,在整個人類命運觀照下的女性意識,突破了狹隘的界限,給讀者更深刻的思考。
二、父權社會下的女性壓抑與苦悶
(一)父權戰爭對女性的傷害
《達洛維夫人》盡管是意識流小說,并且在一天中寫盡了一個女人的一生,但她卻設置了明確的時間線索——1923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戰爭,作為男權制度下的衍生物,對整個社會、人性、生存都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創傷。伍爾夫在這篇小說中對男權社會下的戰爭行為,進行無聲的控訴,字里行間透露著傷痛的痕跡。
在小說的語言背景中我們就不難看出,戰爭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嚴重創傷。而作為小說主要人物之一的賽普蒂莫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受害者。作為戰爭中的幸存者,他并沒有感到自己的“幸運”,而是不斷為“戰爭后遺癥”所擾,肉體盡管存在,但心靈卻被蠶食殆盡。他時常受到戰友亡靈的幻覺折磨,只能以自殺的方式尋求安寧。而他的妻子——雷西婭,被戰爭傷害的典型女性代表,在陪著賽普蒂莫斯求醫問藥的路上,最折磨她的不是身體上的摧殘,而是心靈上的毀滅。丈夫死后,她感到的也并不是解脫,而是生活的無意義。女性作為附屬品的形象在雷西婭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戰爭和男權社會的扭曲使得她完全失去了自我,這是女性自身的悲哀。
戰士們的母親也是被傷害的女性群像的代表,福克斯克羅夫特太太,貝克斯巴勒夫人,都是其中一員,她們的兒子死于戰場,她們的心碎難以平復,這是戰爭帶給母親無法磨滅的創傷。她們忍受著無法忍受的喪子之痛,還要面對殘酷的社會和無意義的人生。這是伍爾夫對父權社會引發出的戰爭的無聲控訴。
(二)女性性壓抑
在婚姻中,達洛維夫人盡管扮演著賢妻良母的形象,但并不表示這樣的生活是盡如人意的。她和丈夫之間的關系很微妙,他們之間各盡丈夫與妻子的職責,卻顯得十分疏離。達洛維夫人始終是孤獨的,有些顧影自憐的感覺,盡管她將自己和家庭都打理得很好,但仍舊是一種情感和肉體的雙重壓抑。
達洛維夫人在婚姻中完全找不到激情和愛意,她時常想念自己以前的情人——彼得,即使再無往來也仍舊無法忘懷,這是她內心壓抑的真實袒露。而在她自己的意識流動中,自然也不再避諱“另一個自我”的內心想法。她懷念曾經與薩利相處的美好時光,她懵懂的意識中已經體會到自己是作為情人般的角色在與女友相處,當吻上她的唇,達洛維夫人曾感覺到內心的感情噴薄而出。她懷疑著自己內心的想法“這是戀愛嗎?”其實內心很明確自己的感受,只是主觀上不愿承認,這是男權社會對女性另一種情感的壓抑。
這兩方面的壓抑,都是兩性之間的問題,在當時那個社會,是婚姻重壓下的產物。這不僅是對女性性愛本身的壓抑,也是對女性心理的扭曲。伍爾夫這樣的表達,是其內心聲音的呼喊,盡管微弱卻擲地有聲。
三、克拉麗莎的消極抵抗
“達洛維夫人”,這個稱謂本身就有作者精心設計的指向性,“夫人”一詞代表的是一種社會身份,而非女性自身。但作為自我形象出現的“克拉麗莎”,對這樣的社會角色也有自己無聲的消極抵抗。
(一)獨自外出
小說的開頭就寫到女主角克拉麗莎獨自外出買花的情節,在這篇意識流小說中,并不是一個胡亂的起筆,是伍爾夫特別安排的情節。整個氛圍中都傳達出克拉麗莎的獨立與安然,自己過得好,正是對男權社會的消極抵抗。
克拉麗莎在獨自外出的時候碰到了老朋友休·惠特布雷德,他是典型男權社會中所謂紳士的代表。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公共領域是男人們的天下,女子甚至不允許獨自外出,即使是1923年,獨自外出也被看做是不合禮教的。休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質問克拉麗莎“去哪兒”,而她的回答卻恰到好處“我喜歡在倫敦散步,真的,比在鄉下散步好多了。”不卑不亢的反應為自己解圍,也是克拉麗莎獨立性格的展現。
(二)舉辦晚會
通篇小說都圍繞著克拉麗莎在家舉辦晚會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和所思所想展開。這個晚會是女主人一手操持的,甚至連花朵都是她親自采購。表面上看,達洛維夫人的晚會,是為了達洛維先生的社交圈而準備,她只是作為政客的女人這一附屬社會地位而存在。其實不然,舉辦晚會并不是她丈夫的意思,相反,達洛維先生認為晚會很無聊。因為這個宴會完全是出自克拉麗莎個人的審美和交情,這是她自己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她的事業。克拉麗莎借助這樣一種被當時社會和家庭所允許的方式,與自己的朋友以及這個社會建立另一種方式的聯結。只有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才能保證交流的平等。這是女主人公在男性社會的房檐下,傾盡自己所能做出的消極抵抗。
(三)婚姻外的情緒
克拉麗莎盡管已經嫁為人妻,并且表面看起來賢良淑德,但她內心仍有叛逆,對愛情亦然。她并不像其他女人那樣心如死灰。在作者筆下的意識流動中,她時常懷念起自己從前的愛人——彼得。彼得的形象是美好而縹緲的,是克拉麗莎腦海中建構的男性形象,她在隱隱的女同性戀傾向的背后,仍舊在心里為“彼得”留下一席之地。這也正是人性的矛盾與復雜之處,感情的線索就像意識流小說的筆鋒一樣,經常是不受控制的,無理由的存在和消亡。這種滾動的意識流,這種無人了解的內心世界,本身就是克拉麗莎以至于伍爾夫自己抵抗男權社會的一種話語方式。
結語
達洛維夫人和克拉麗莎之間的角色掙扎,本身就是對女性意識覺醒與壓抑間微妙感覺的真實傳達。作為達洛維夫人這一社會角色,她是傳統而安穩的存在;作為女性角色本身的克拉麗莎,以消極抵抗的方式掙脫男權社會的壓制。兩者在伍爾夫的意識流手法下此消彼長,融會貫通。這正是弗吉尼亞·伍爾夫作為成功小說家的高明之處,整篇小說并沒有只言片語關于女權主義的闡述,卻留給讀者深入思考的空間,可謂“于無聲處聽驚雷”。
參考文獻:
[1]弗·伍爾夫.達洛維夫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2]胡新梅.戰爭:創傷與女人——從女性視角解析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6).
[4]李銀河.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M].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
[5]瞿世鏡.伍爾夫研究[J].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5]王小航.強迫的異性戀和壓抑的女同性戀——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J].福建工程學院學報,2006(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