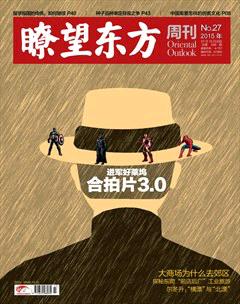大商場為什么去郊區
萬宏蕾
臺灣新光三越集團曾在北京的CBD東部邊緣建設一座號稱中國內地最賺錢的單體百貨——北京CBD“新光天地”。2015年4月,這家“新光天地”正式更名為“SKP”,消除了最后一絲新光三越的印記。
然而此前在2014年8月,新光三越與遠洋地產聯合拿下北京通州運河核心區的4宗地塊,總建筑面積46.45萬平方米、總價39.39億元,準備建設另一個“新光天地”。
可能將擁有三個功能區的“運河北京文化商務中心區”則是通州新城的核心區,目前關于“現代化國際新城”最利好的消息,就是未經證實的北京市政府將遷入。
雖然以“北京副中心”自居,但根據2005年《北京十一個新城規劃(2005—2020)》,通州新城不過是11個北京新城之一。
依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新城指承擔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產業、帶動區域發展的規模化城市地區。
這些被賦予眾望的新城歷經10年建設,從一片片荒地起步,拆遷、建路、蓋住宅、完善市政設施……“新光天地”這樣的商業綜合體的入駐,其實代表了它們正走向完善。
“以北京、上海、廣州為首的中國一線城市郊區商業的發展都在進入快馬加鞭時代。”中國商業地產聯盟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永平告訴本刊記者,“中國商業地產經歷了近10年的野蠻式增長,隨著大量人口外溢,新興商業物業向郊區發展的趨勢日益明顯。”
疲憊的中國商業地產和百貨業正寄望于這些新城商業。
通州現象
先后為CBD“新光天地”、通州“新光天地”提供策略顧問和商業設計優化服務的RET睿意德高級總監李靜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通州項目包含購物中心、寫字樓等綜合物業形態,這一區域的商業更多關注未來新導入商務人群。這將與CBD新光項目截然不同。”

位于北京CBD東部邊緣的原“新光天地”已正式更名為“SKP”
對于“新光天地”落戶通州,李靜雅的解釋是“作為距北京最近的郊區,通州到中心城區只有15公里,車程半小時左右;從通州去首都機場車程40分鐘,距離未來的新機場也只有大約1小時的車程。軌道交通除了已有的地鐵八通線和6號線,未來5年還有至少2條直通中心城區的軌道線路開通運營,由此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不言自明。”
“新光天地”并非通州唯一的“大象級”商業項目:僅2015年通州至少還將有3個大體量商業項目入市,預計新增供應量達22.28萬平方米。全年通州新增商業體量則占北京全市的17%。
商業綜合體落戶通州的理由其實十分充分:通州人口由2005年的88.5萬人增長到2013年底的132.6萬人,8年中平均每年增加5.5萬多人,年均增加6.23%。
這個數字比北京市同期的年均增加4.69%高出近2個百分點。
隨著人口逐年增加,新城的公共服務建設也逐漸為政府所重視,“軌道交通等配套設施的加速完善也加快了人口導入的力度,促進了軌道交通沿線新興商圈的形成,如通州、房山、亦莊、昌平、天通苑等商圈。”盈石集團研究中心總經理、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中國商業地產專業委員會主席張平告訴本刊記者。
盈石集團是一家全國著名的商業地產綜合服務機構。盈石集團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2014年起的3年內,北京商業物業將繼2007年之后迎來又一次供應高峰,其中非核心商圈將新增超過170萬平方米,約占總新增供應量的55%,“大北京區域發展的加速以及新興商圈的逐步成型與發展,促使新增商業物業向郊區發展趨勢日益明顯。”
根據RET睿意德中國商業地產研究中心數據,2014年第四季度入市的京通羅斯福廣場和通州萬達廣場的體量幾乎是之前通州集中商業存量的一倍。
而在城市副中心及國際新城規劃的利好帶動下,通州商業物業2014年第四季度成交價格同比上漲9.2%,近一年中的價格基本保持了穩中有升的趨勢。
人都去郊區了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的很長時間內北京只有5家百貨商場和1家購物中心——位于王府半島酒店的半島精品廊。”張平回憶,“2004年北京新增入市商業物業超過了90 萬平方米,自此北京商業物業市場進入了開業高潮。”
2005年至2010年,北京市每年的新增供應都超過100萬平方米。這期間共入市146個項目,超過900萬平方米,超過2003年存量的4.5倍。北京商業地產布局則開始逐漸由中心向外擴散。
通州的人口聚集并非孤例,目前北京全市有超過一半常住人口居住在五環以外。
2014年的北京市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三環至六環間聚集了1228.4萬常住人口,占全市的57.1%;四環至六環間聚集了941萬常住人口,占43.8%;五環以外有1098萬常住人口,占51.1%。
從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開始,北京二環以內的人口密度就持續降低,到1990年老城區人口下降了3.38%。而90年代開始的大范圍舊城改造活動,則加速促使了內城人口向三環四環遷移,到2010年中心城區人口較30年前已經下降了10%。
“除了通州,位于北京郊區的不少新興商圈和潛在商圈目前還是價值洼地。”張平認為,“大興、順義和房山長陽在政府大力推動下,有望隨著地鐵、快速公交等交通設施建設的加速,成為新的投資和居住熱點地區。”
而到2016年底,上海總新增商業物業供應總量約為430萬平方米,非核心商圈的商業物業供應245萬平方米,增量為現有存量的52%。
早在2010年,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上海近郊區、遠郊區的人口密度分別為每平方公里4684人、1388人,比2000年分別增加80.2%、61.4%。
占上海總面積不到十分之一的核心城區——黃浦、盧灣、靜安、虹口、長寧等地的人口不斷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黃浦區,減少四分之一。這顯示了上海中心城區核心區域的人口正向郊區、中心城區外圍區域遷移。
“這一變化的直接誘因主要是近年來上海舊城改造與新區開發之間的聯動。首先,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郊區新城建設不斷加快等因素,使得大批居民遷往近郊區、中心城區邊緣區域的新建居住區。其次,外來常住人口往往相對集中居住在近郊區域。”當時上海地方媒體分析說。
“廣州情況類似。”張平分析,“2016年廣州購物中心及百貨的存量將達到559萬平方米,由于中心城區可供新開發的地塊供應較少且地價較高,新進入廣州的開發商選擇市中心區以外進行拓展,這也導致了未來廣州商業物業新增供應主要來自外圍區域。”
不過與郊區激增的人口紅利相比,當前商業地產本身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更是把他們捆綁在郊區商業。
“拋棄”城區
在RET睿意德執行董事張家鵬看來,“現階段的郊區購物中心,是避開核心區傳統商圈擁擠式購物的新希望。”
“城市核心區域可開發的土地有限,用地緊張就需要引入更多高租金業態商家來平衡投資收益。”他向本刊記者解釋說,
傳統商圈受物業條件限制,商場硬件、車位等配套設施滯后制約且升級改造困難。與之相比,城市郊區擁有更加寬裕的土地提供,購物中心相關配套更加完善,具備相當的便利性優勢。”
比如廣州最知名的傳統商圈——天河城,商業總面積高于上海的徐家匯、淮海路、南京路及北京的西單、王府井、CBD核心商業區。
但目前天河城商圈10分鐘車程的街道往往要擁堵半個小時以上,且商圈內業態比較低端,幾乎看不見任何高端奢侈品品牌。
于是出現一種說法:要“養育”該商圈,天河路每天要吸引近150萬人次的客流——這是一個足以讓任何路網癱瘓的數字。
當地政府曾想通過商業網點的規劃布局保證市場有序競爭,但畢竟“先有網點后有規劃”,許多建筑已不可能拆除重建。
在這方面,郊區購物中心在規模與租金壓力上都優于市中心核心區。與傳統商圈高密度建筑不同,郊區土地不僅相對便宜,還可以承載更豐富、更多樣化的建筑形式。
當然,“除了地價比核心區便宜,郊區其他建設成本、日常運營、推廣、物業、人力、水電等并不便宜。但它還是相當于一張白紙。”李靜雅說,“早期國內業態品種有限,大部分品牌會優先選址核心區。但當下中國業態豐富度已經顯著提升,這就為郊區購物中心實現業態差異創造了良好機會,在引入體驗性業態方面可以做到更優。”
同時,汽車的普及化發展也大大擴展了人口的消費半徑,相當于拉近了城郊距離。
然而在王永平看來,“國內的郊區商業發展模式與國外很不一樣,國外多是出于城市規劃的合理布局,主動往郊區引導人流、車流。國內則是被動式外溢,承受不了市中心運營壓力,不得不一圈圈外擴。”
新城能拯救中國的商業地產和百貨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