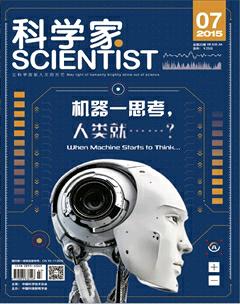王大珩的暮年壯心
張文雅
我們都知道王大珩是中國(guó)光學(xué)事業(yè)的奠基人、是“兩彈一星”元?jiǎng)祝瑓s鮮有人知道他可愛(ài)的一面。他在世的時(shí)候,當(dāng)有人問(wèn)他高壽,他會(huì)精確地告訴對(duì)方“我今天90.35歲了”;我們都看到他榮譽(yù)滿(mǎn)載、成就卓著,但卻很少關(guān)注到他常常以“小學(xué)生”的姿態(tài)面對(duì)新知識(shí)、年長(zhǎng)者;很多人想象老人的晚年應(yīng)該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jiàn)南山”,但王大珩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時(shí)光,都在不停地學(xué)習(xí)。
王大珩的科學(xué)精神
“什么是科學(xué)”,看似簡(jiǎn)單的一個(gè)問(wèn)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流利地回答。王大珩有一個(gè)通俗易懂的解釋?zhuān)础拔鍌€(gè)W”——what(何事)、why(何故)、where(何地)、when(何時(shí))以及who(何人),而科學(xué)要做的就是解決這“五個(gè)W”的問(wèn)題——對(duì)客觀事物正確認(rèn)識(shí)和理解的知識(shí)體系。
為什么要解答這個(gè)基本概念呢?王大珩在耄耋之年依舊無(wú)時(shí)不刻地關(guān)注著我國(guó)科學(xué)領(lǐng)域的動(dòng)態(tài),他關(guān)注到我國(guó)的科普工作成效不突出,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事實(shí),而忽略了對(duì)科學(xué)精神的解讀。因此,他在2003年撰寫(xiě)了《什么是科學(xué)精神》,并在起筆中自謙道:“自己很膽怯,也許談出來(lái)的觀點(diǎn)不夠科學(xué)精神,還請(qǐng)大家批評(píng)指教,我甘當(dāng)這方面的小學(xué)生。” 這篇文章于2007年在《北京日?qǐng)?bào)》刊登并被多家媒體轉(zhuǎn)載。
在這篇文章當(dāng)中,王大珩總結(jié)了六點(diǎn)科學(xué)的特征,以這六條特征來(lái)看今天的科技界,仍然十分受用。如,在解釋科學(xué)的同一性,即嚴(yán)密性時(shí),王大珩以中西醫(yī)為例,中西醫(yī)的“對(duì)決”也是2014年微博的熱門(mén)話(huà)題,他這樣解釋道:中西醫(yī)各有一套理論說(shuō)法,而且在實(shí)踐上都見(jiàn)成效,終究這兩種理論會(huì)統(tǒng)一起來(lái),舍棄當(dāng)中不確切的地方,補(bǔ)充應(yīng)當(dāng)補(bǔ)充的部分,這也是科學(xué)進(jìn)步的一個(gè)途徑。科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與文化同等的包容性,“求同存異”不僅是一項(xiàng)國(guó)策,更是我們對(duì)待不同思想領(lǐng)域的不同事物時(shí)應(yīng)具備的態(tài)度。這一點(diǎn),王大珩的“同一性”一語(yǔ)中的。
王大珩先生所列舉的一些非科學(xué)的表現(xiàn)形式,我們也能夠在2014年找到相似的案例。譬如發(fā)生在山東招遠(yuǎn)的涉邪教故意殺人案,常爆出的高校教授論文造假事件,以及披著科普的外衣傳播“偽科學(xué)”等事件,都是他所列舉的應(yīng)該嗤之以鼻的非科學(xué)行為,這些行為帶來(lái)的危害殃及全社會(huì),同時(shí)也從側(cè)面說(shuō)明“科學(xué)思想與科學(xué)精神不僅僅是科學(xué)技術(shù)工作者所需要的,而是全體公民都應(yīng)該樹(shù)立的”。
行文最后,王大珩意味深長(zhǎng)地講道:“半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我們國(guó)家發(fā)展經(jīng)過(guò)了許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針政策是不符合實(shí)事求是原則的,這方面我們有很深刻的教訓(xùn)。方針、政策是否科學(xué),是要通過(guò)實(shí)踐來(lái)檢驗(yàn)的。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當(dāng)科學(xué)化能夠搞得好一點(diǎn)的話(huà),大家的認(rèn)識(shí)就容易一致。在科學(xué)化的基礎(chǔ)上,我們最容易形成共識(shí),最容易團(tuán)結(jié)在一起。”
撰寫(xiě)這篇文章時(shí),王大珩已經(jīng)88歲高齡,視力嚴(yán)重下降,因此只能依靠本人口述、助手打字的方式來(lái)完成文稿。但他仍要保持每天“讀”報(bào)、“聽(tīng)”國(guó)家大事的習(xí)慣。“當(dāng)王老的秘書(sh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因?yàn)椴粌H要每天挑選他可能感興趣的新聞讀給他聽(tīng),他還會(huì)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些熱點(diǎn)話(huà)題。”曾擔(dān)任過(guò)王大珩助手的一位老師告訴記者,王大珩常常一個(gè)人戴著耳機(jī)聽(tīng)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的講話(huà)和政府工作報(bào)告;如果有什么創(chuàng)新的建議,他還會(huì)直接反饋給中央領(lǐng)導(dǎo)。王大珩的每一天都在為國(guó)家、為科學(xué)殫精竭慮。
王大珩的可敬之處
“我們走進(jìn)季羨林先生的病房,王老就像是一個(gè)小學(xué)生一樣畢恭畢敬地站在季先生的桌子旁邊,直到季老說(shuō)‘你坐吧,王老才落座。”這一個(gè)情景給王大珩的助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當(dāng)時(shí)的王大珩也已過(guò)鮐背之年。雖然是學(xué)習(xí)不同專(zhuān)業(yè),但王大珩仍然尊稱(chēng)季羨林為學(xué)長(zhǎng),加之王大珩十分尊師重道,因此,即使是面對(duì)只是大其幾歲的學(xué)長(zhǎng),也同樣敬愛(ài)有加。
晚年時(shí)候的王大珩雖然視力下降,但思維仍十分靈敏,他會(huì)把圓周率π背誦到小數(shù)點(diǎn)后100多位。而他鍛煉思維的方法也著實(shí)新穎,那就是每一天都計(jì)算自己的年齡,用一年當(dāng)中度過(guò)的天數(shù)除以全年的天數(shù),并保留小數(shù)點(diǎn)后兩位數(shù)。這樣,他每一天的年齡都是不一樣的。王大珩就是這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jī)會(huì),讓自己不斷地思考,他從不耽于已經(jīng)掌握的知識(shí),在他看來(lái),“已知”的東西也終將會(huì)落后、老化。因此,他堅(jiān)持每天看書(shū)讀報(bào)聽(tīng)新聞,讓自己緊跟時(shí)代的步伐。
為了更好地看書(shū)讀報(bào),王大珩還專(zhuān)門(mén)制作了一個(gè)放大鏡,時(shí)常掛在自己的胸前,以方便閱讀。這個(gè)放大鏡造型十分獨(dú)特,整體類(lèi)似于碗形的設(shè)計(jì),精巧而方便。“碗底”就是放大鏡的透鏡,看書(shū)的時(shí)候只要將“碗”倒扣在書(shū)面上,就可以避免手持放大鏡的抖動(dòng)問(wèn)題,同時(shí)還能夠自然對(duì)焦,非常實(shí)用。
除了每天“讀”報(bào),王大珩的興趣愛(ài)好也十分廣泛。他喜歡聽(tīng)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音樂(lè),也常常會(huì)聽(tīng)國(guó)粹京劇,怡情的時(shí)候還會(huì)寫(xiě)詩(shī)作詞。
“光陰流逝,歲月崢嶸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參馳,為祖國(guó)振興。光學(xué)老又新,前程端似錦。搞這般專(zhuān)業(yè)很稱(chēng)心!”
這是王大珩在70歲時(shí)所作的詞。人說(shuō)七十古來(lái)稀,本可以致事閑賦,頤養(yǎng)天年,但王老暮年,壯心不已,仍時(shí)刻準(zhǔn)備著為祖國(guó)振興而鞠躬盡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