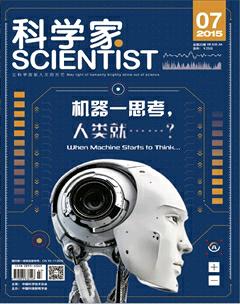是非·屠呦呦
2015年6月4日,哈佛大學醫學院官方網站公布2015年度華倫·阿爾波特基金會的授獎信息。中國中醫科學院(原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員屠呦呦因其在抗瘧領域的突出貢獻而榮獲此獎。該獎將于10月1日在哈佛醫學院舉辦的專場研討會上頒發。
據悉,屠呦呦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科學家。理論上,對于這種“中國第一位”的消息,其新聞價值即使上不了頭條,最起碼也會被排列在新聞網站的首頁。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好似都沒有“發現”這條消息,并未對此進行報道。只有屠呦呦的家鄉“浙江在線”及其工作單位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以主人翁式的驕傲,在6月中旬發布了相關信息。
同樣的獲獎者,相似的獲獎原因,對比2011年的大張旗鼓,如今的斂聲寧靜讓人摸不著頭腦。而更讓人唏噓的是,關于屠呦呦停不下來的爭議。
是,不可擋
2011年9月,屠呦呦獲得2011年度拉斯克獎臨床醫學獎,以表彰其對治療瘧疾的青蒿素研究所作出的貢獻。這是該獎項設立65年以來,首次頒給中國科學家,也是迄今為止,中國生物醫學界獲得的世界級大獎。
消息一出,各大媒體像炸開鍋一樣,開始追蹤報道屠呦呦的獲獎背景,研究專業,以及生平記事。
屠呦呦對青蒿素的發現有多重要?
我們先回到上個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以及越南戰爭時期。當時作戰士兵常常被瘧疾所累,戰斗力受到嚴重影響。于是,多國政府都不得不將大量精力投入到抗瘧藥物的研發上,但都一籌莫展。
1967年5月23日,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來自全國各地的科研人員聚集北京,就瘧疾防治藥物和抗藥性研究工作召開了一個協作會議,就此啟動了代號為“523項目”的計劃。該項目的短期目標是要盡快研制出能在戰場上有效控制瘧疾的藥物,長遠目標是通過篩選合成化合物和中草藥藥方與民間療法來研發出新的抗瘧藥物。
國家對“523項目”十分重視,特設仿造西藥或制造衍生物、從中藥中尋找抗瘧藥、制造驅蚊劑等幾大課題組,組織了來自60多個研究機構和單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員參與研發,這其中就有來自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的屠呦呦。她被分在了中醫藥協作組,主要從中醫角度開展實驗研究。
實驗的過程漫長而復雜。光調查收集這一個過程,屠呦呦和她的課題組成員便篩選了2000余個中草藥方,并整理出了640種抗瘧藥方集。他們以鼠瘧原蟲為模型檢測了200多種中草藥方和380多個中草藥提取物。這其中,青蒿素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
青蒿素是來自一種菊科艾屬植物的提取物,屠呦呦在實驗過程中發現,它對鼠瘧原蟲的抑制率可達68%。但這個抑制率十分不穩定,甚至在后續的實驗中,抑制率顯示只有12%-40%。對此屠呦呦猜測,低抑制率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份濃度過低的原因造成的。于是她著手改進提取方法。通過翻閱古代文獻,特別是東晉名醫葛洪的著作《肘后備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她意識到常用煎熬和高溫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壞了青蒿有效成分。
不出所料,改用乙醚低溫提取后,研究人員如愿獲得了抗瘧效果更好的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點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實驗室中觀察到這種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這個解決問題的轉折點,是在經歷了第190次失敗之后才出現的。”這一步,至今被認為是當時發現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關鍵所在。
后來,為了獲證青蒿素對人體瘧疾的療效,屠呦呦等人首先在自己身上進行實驗,實驗效果十分喜人。隨后,屠呦呦課題組深入到海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瘧原蟲的患者身上試用之后,發現青蒿素治療瘧疾的臨床效果非常成功。
青蒿素對惡性瘧疾、腦瘧強大的治療效果,挽救了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數百萬人的生命,飽受瘧疾之苦的非洲人民稱之為“中國神藥”。“在人類的藥物史上,我們如此慶祝一項能緩解數億人疼痛和壓力、并挽救上百個國家數百萬人生命的發現的機會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學教授、拉斯克獎評審委員會成員露西·夏皮羅如此評價發現青蒿素的意義。
屠呦呦因此被稱為“青蒿素之母”,并得到拉斯克獎臨床醫學獎的嘉許。
因為拉斯克獎還有一個“諾貝爾獎風向標”的別稱,人們便激動地預測,屠呦呦很有可能成為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個中國人。結果我們都知道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兩個美國人和一個法國人。雖然希望落空,但這也不影響人們給屠呦呦加冠另一個頭銜——離諾貝爾最近的中國女人。
非,池中物
屠呦呦獲獎后,在一片叫好聲中,人們漸漸發現了這位卓越的女科學家區別于傳統意義中獲獎者的獨特之處,她既沒有博士學位、留學經歷,也不是兩院院士,只是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員。
這讓人們不禁揣測猜疑,于是,一些針對“三無”教授的非議接踵而至。
縱觀輿論,關于屠呦呦的非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她為什么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為什么不是兩院院士,青蒿素歸屬之爭。
說到諾貝爾獎,這是中國人的軟肋。人們始終憧憬每年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能夠出現中國身影,包括當年屠呦呦的這次落選。
“諾貝爾的獎項發展到今天,更多是用來對科學家一生的貢獻做總結性表彰,而不僅僅是表彰近期的成就。”當時,《新京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不必為屠呦呦落選諾獎而失望》評判屠呦呦與諾獎的擦肩而過,文章從諾貝爾獎的表彰性質切入,講道當年獲得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三位科學家,他們在獲獎領域的決定性成果獲得承認,都比屠呦呦早得多。與之相比,青蒿素取得階段性成果也好,獲得業內和國際承認也罷,并無時序上的優勢可言。
如果說,諾貝爾獎的表彰性質是客觀因素,是我們無能為力的原因。那么,徜徉在中國坊間的另一種說法,只能讓人啞口無言,那就是青蒿素的歸屬之爭。
由于“523項目”是在援外備戰的背景下提出,具有軍事機密的性質,項目的研究結果不允許向外公布。加之“文革”期間,科研工作者不能公開發表科學論文。種種原因導致這項工作在當時并不被“523項目”以外的人所知。
沒有文獻,沒有出版記錄,便無從證明:屠呦呦是發現青蒿素的主要貢獻者。即使后來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還是有很多人站出來想要分一杯羹。畢竟,實驗發現是課題組團結合作的成果。人們紛紛抗議,獎項應該為集體所有,而不能只歸功于一人。
對此,輿論眾說紛紜。
而曾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的饒毅在其一篇名為《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得文章中給出了比較中肯的觀點。雖然對于青蒿素的歸屬問題爭議不斷,但有三點毋庸置疑:首先,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對于發現青蒿的抗瘧作用和進一步研究青蒿都很關鍵;其次,具體分離純化青蒿素的鐘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組的成員;此外,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組是在會議上得知屠呦呦小組發現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瘧作用以后進行的,獲得純化分子也晚于鐘裕容。
讓饒毅感到不平的還有:“他們(屠呦呦和張亭棟)作出的貢獻,在我看來,值得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而他們在國際國內的認可都遠低于他們的實際貢獻。兩位皆非院士,其中一人可能從未被推薦過。”
在傳統觀念中,院士身份是評判一位科研工作者成就的一張有力的名牌。而聞名國際的屠呦呦并未得到這張名牌。這與上文提到的青蒿素的歸屬爭議有關,還有來自街談巷語的“人品說”“權力說”等等。
返璞歸真,無論蜚語再多,屠呦呦的科學貢獻都無法泯滅。正如饒毅所說:最重要的是,這些藥物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我們應該推崇他們的工作、肯定他們的成就。科學,有著客觀的標準,通過爭論可以將我們帶近真理。
呦呦鹿鳴
初聞屠呦呦的人,都會被她的名字所吸引。
屠呦呦的名字緣起《詩經·小雅》的名句“呦呦鹿鳴”,意為鹿鳴之聲。而更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呦呦鹿鳴”的后半句“食野之蘋”,人們驚嘆于從取名開始,屠呦呦的命運注定要與這棵神奇的小草連在一起。
屠呦呦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植物化學研究人員,但作為一個在中國醫藥學寶庫中有所發現,并為國際科學界所認可的中國科學家,她感到自豪。“在我的童年,我親眼目睹了民間中醫配方救人治病的場景。然而,我從沒有想到我的一生會和這些神奇的草藥關系如此緊密。”
1930年年底,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寧波市。作為家中5個孩子中唯一一個女孩,屠呦呦一直接受著良好的教育。她的高中同學陳效中回憶說,屠呦呦在班上不聲不響,經常上完課就回家,成績也在中上游,并不拔尖。
盡管成績并不突出,但屠呦呦還是在1951年考入北京醫學院(后改名為北京醫科大學,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畢業后,被分配在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一直工作至今。
屠呦呦十分低調,即使是獲獎后,她都很少接受媒體采訪。在普通人看來,她有些神秘,有些不食人間煙火。但在朋友眼中,屠呦呦是個十足的“馬大哈”。“屠呦呦生活上是個粗線條,不太會照顧自己,一心撲在工作上。有一次,她的身份證找不到了,讓我幫忙找找,我打開她的箱子,發現里面東西放得亂七八糟的,不像一般女生收拾得那么停當。同學們見了后都笑話她。她家務事不靈光,成家后,買菜、買東西之類的事情基本上都由先生做。”陳效中回憶道。
雖然,生活中的屠呦呦“不拘小節”。但碰到自己喜歡的事情,她會表現出異于常人的堅毅。
在青蒿素研究上,屠呦呦花費了很多精力。接到“523”項目的時候,她已接近不惑之年,而她的女兒才3歲,為了不影響研究,她把孩子交給老母親撫養。由于當時長期做實驗,過勞的屠呦呦染得一身的病。
而在拉斯克獎評審委員會成員露西·夏皮羅看來,青蒿素這一高效抗瘧藥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屠呦呦及其團隊的“洞察力、視野和頑強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