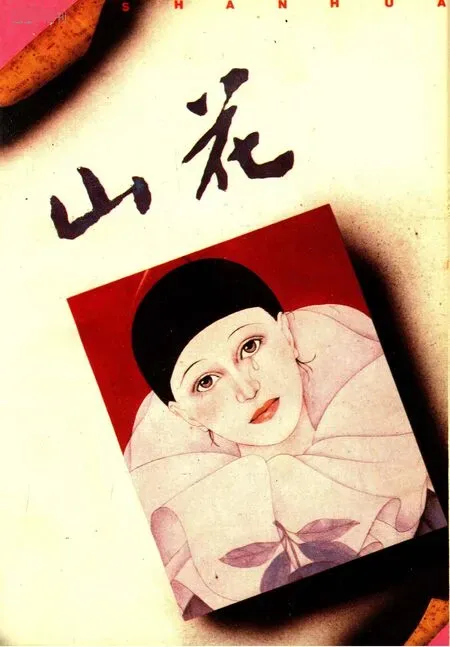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文學烏托邦意義的詩潮
小海++姜紅偉
姜紅偉: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小海:關于20世紀80年代,被談論得很多,其實不僅僅是在詩歌界,連知識界也在談論,很多人在不斷地“返場”(80年代的現場),有的人想的是回到80年代的原點去“重啟”,或者說重新出發,有的人是想重溫一段歷史,也有的人僅僅是一次次地謝幕。這就是我看到許多知識界人士關于80年代的回憶文字得出的印象。
我認為所謂的“80年代”,詩人、知識分子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的自由氣息,但還稱不上是一個黃金時代,最多是一個接受學意義上的黃金時代,是一個文學理想的烏托邦。
當然,不容置疑的是,80年代確實產生了一批優秀的詩人,以60年代及其前后出生的詩人為主體,成為當代中國詩歌的中堅力量。
進入90年代后,一直到新世紀,隨著時代節拍器與個人心靈律動的無法相應,甚至相背離,詩歌與生活、詩人與時代之間呈現出的“古老的敵意”也越發激烈,失落與茫然在所難免。但詩人和詩歌一直在前行,許多詩人尋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與力量,變得更加自信和從容。
我想,我們既不能低估80年代所擔負的“啟蒙”意義與任用,但也絕對不要陷入對80年代的集體意淫中去。
在當代中國,“運動”這個詞語有特定的含義,常常是和政治糾纏在一起的。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來,從上而下發動的大大小小的運動有數十次之多。“大學生詩歌運動”和這些政治運動不同,其實是民間發起的、從校園出發的一次詩潮。
“80年代”,也是一個具有文學烏托邦意義的時代。
姜紅偉: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革命生涯”。
小海:說到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我對“革命運動”其實是“后知后覺”的,相對于80年代初就已經嶄露頭角的校園詩人來說,我也屬于“后生晚輩”。雖然寫作起步很早,但進入大學已經是1985年秋季的事情了。在80年代初,當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和我打交道的一批詩友好多已經是大學生。
應當是韓東在山東大學哲學系讀書的時候,我們建立了通信聯系。那時候他是讀大二還是大三記不太清楚了。他后來跟我講,我的信讓他見識了一個狂放不羈的少年是怎樣的,用的是“煮酒論英雄”的口氣——“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我想不起來干過這樣荒唐的事,但在那個年齡又是完全可能的。這是和運動無關的個人意氣。而我的本名很容易被認作是個女生,那時韓東剛好和來自唐山的生物系女生小君(李毅君)正談著戀愛,也不敢回我的信,生怕引起誤會。這可能也是他后來在西安辦《老家》時建議我改筆名為小海的原因。這只是猜想。我知道韓東和他的一批同學發起成立過詩社,后來詩社被學校查封,那是我最早知道的大學生詩社之一。后來我還和東北的大學生詩人潘洗塵等人有過通信往來。韓東畢業后分配至西安財經學院任教,他在西安主編出品詩歌民刊《老家》,主要成員還是山東大學和陜西財經學院已經畢業和個別留校的一批大學生詩人。我也在《老家》上發表過詩歌習作,只有我還是中學生。同時,我還以通信和尋訪的形式陸續結識了韓東的大學同學和西安時期的朋友王川平、楊爭光、吳濱、沈奇等詩人、小說家。
1982-1983年期間,我在全國的許多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詩歌習作。記得和我發表在同一期刊物上不少人都是大學生,有的人還是我通信聯絡的筆友。
80年代初期,詩壇有一句流行語“好詩寄邊疆,老詩往中央”。可能與一大批詩人作家曾經“發配”邊疆,在當地的影響和形成的文藝小氣候有關。如艾青就曾下放在新疆石河子多年,后來,當地建有艾青詩歌館,并創辦了《綠風》詩刊。在朋友們的慫恿下,我的一批詩就寄給了邊疆和內地的文學刊物。一些邊遠地區的圖書館也有好圖書,韓東曾從陜西省圖書館幫我借到墨西哥作家魯爾夫小說集《平原烈火》、戴望舒譯的西班牙洛爾迦詩抄等書目,在外借期限內讀完,再郵寄給他還上。
1984年,我和華德民、鄭子等一批文朋詩友,一同去徐州、曲阜、濟南、北京等地漫游。年底,在北京還專程拜訪了陳敬容先生。年末,我去南京看望了新婚的韓東、小君夫婦,聽韓東詳細介紹了籌辦民刊《他們》的設想,看到了畫家丁方設計的封面小樣和各地詩友即將發表于第一期《他們》上的部分詩稿。一批作者就是曾經出現在蘭州封新城所編輯的《同代》上的大學生詩人。1985年春天,在韓東倡議下,創辦了“他們”文學社。像于堅、丁當、小君、王寅、普珉、呂德安、蘇童、陳寅等人其實都是國內各個高校走出來的校園詩人。我在這一年被南京大學中文系免試錄取,與賀奕、李馮、劉立桿、姜雷、曹旭、程士慶、章紅、謝倩霓、楊新等一批有文學理想的人成為同班同學。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南京大學最早的校園詩人是唐曉渡、崔衛平、周曉揚等一批人。我進校后,與前后屆校友高翔、朱燕玲、賈曉偉、張偉弟(程尚)、杜駿飛(杜馬蘭)、海力洪、張生、吳長纓、王青華、海馬(中學同窗)等人相識,有的還成為要好的朋友。
在校期間,我與同學們組織成立了南京大學南園文學社并創辦了《南園文學》。在南京財貿學院舉行過詩歌專題講座。我在《他們》文學交流資料l至9期(1985 -1995年)發表了大量的詩歌、詩論以及訪談。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少數作品有的是從《他們》上轉載的。
1986年,暑假里,我同韓東、賀奕結伴游歷,分別在西安、成都、重慶三地結識了丁當、楊黎、萬夏、馬松、石光華、宋渠、宋瑋、王川平等一批詩人。在成都時,我們仨曾被一個叫曾鵬的哥兒們介紹到四川大學的教工宿舍住過,川大放暑假了,沒有見到大學詩社的人。這一年,印象中詩人牛漢等人曾被請到我們學校的大學生俱樂部與大家座談交流。1987年,我們文學社也請外地來南京的《他們》作者,如小說家馬原、詩人丁當等在南京大學舉辦講座、小型文學討論會等活動。我也和韓東一起在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文學社團共同主持過詩歌講座等。在1985年秋至1989年7月的四年大學生涯中,我和南京其他高校的校園詩人一直也有來往,如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的吳晨駿、朱文,南京林業大學詩社的巖鷹等。外地來南京大學找我們玩的詩人也有不少,記得有楊黎、張小波等。當然,還有南京藝術學院,那里當時有畫家丁方、朱新建,蘇童從北師大畢業后,第一個落腳的地方也是在那兒當輔導員。
1989年7月,我畢業離校,被分配至蘇州市環境保護部門工作。同學中的文學伙伴留校的不多,杜駿飛(杜馬蘭)留校當老師了,李馮臨時做決定后,居然考上了本系的明清文學專業研究生(因為他不想分配回廣西)。海力洪因為低一屆還沒畢業。張生從武漢考進南大讀研究生后,經李馮介紹我們認識成為好友。有了他們幾個,偶爾返校,覺得那個氛圍還維系著,還會通宵達旦地“劇談”。
韓東曾在安徽《百家》雜志撰文評點第三代詩人群體10位左右的詩人(主要是大學生詩人群體中走出來的一批人),記得他對我的說法是:他無須創新,可以憑借自己天生的才能就能將任何一種形式發揮到極致。
姜紅偉: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是如何介入其中的?
小海: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值得說的主要一件事就是協助韓東編輯民刊《他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到韓東家碰頭,南大一群,南工一群,那個時候沒有電話先預約的事情,到了他家如果沒有人,就在他家樓下傻等;后來漸漸發展為,到他家遇不到主人,有時就自己捅開門鎖反客為主,甚至我們上門時,發現捷足先登的哥兒們己在他家安坐著等我們后一批到的上門了。我們也經常帶上詩稿到九華山、雞鳴寺茶館審讀,或者干脆是海侃一天。
四年的大學生涯,我能夠記住的幾件事,一件是1985年9月初,我在南京大學新生歡迎會上介紹并朗誦《他們》中的詩人丁當等人的詩歌作品,引發反響與爭議。許多人之前沒有讀到過這樣一種類型的詩,非常困惑、疑慮,甚至憤怒,在臺下高喊: “聽不懂,什么破詩,快下去!”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要看后面安排的招待電影了。而我的哥兒們、死黨們則在下面拼命鼓掌叫好——之后,我被中文系黨總支領導找去談話“教育”。
另一件是1986年暑假里,韓東、我同一宿舍的好友賀奕和我三個人的那次難忘的旅行。之前,我和賀奕為了積攢車票錢,吃干飯喝食堂免費供應的湯水,也硬著頭皮到女生宿舍去借錢籌集路費。我們從南京出發,經西安、九寨溝、成都、重慶,再回到南京,一路上的種種所見所聞,至今似乎依然歷歷在目。
再就是和志同道合的大學同學賀奕、李馮、劉立桿、姜雷、海力洪等人,因為文學趣味相投,也為了有別于校內其他的學生刊物,我們設計從學生會拿到一筆錢,倒騰出了一本我們自己的文學合集《大路朝天》,我至今還記得,我請于小韋為《大路朝天》設計的那個封面。
姜紅偉:1985年12月,那時,您剛被南京大學免試錄取為中文系學生。我曾經收到您的來信和您寄來的一本《他們》創刊號。在信中,您興奮地告訴我,您參與創辦的民刊《他們》是一本很牛逼的刊物。我看后,非常震撼。作為民刊《他們》的重要參與者,能否請您再給我們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他們》創辦的來龍去脈?
小海:說到《他們》就不能不提到《老家》,我甚至認為《老家》其實就是《他們》的前身。韓東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大概在他讀大二或者大三的時候我們開始通信聯系。1982年他被分配至西安財經學院工作后不久,就開始聯絡他在大學期間辦文學社團“云帆”時結識的一批同學和朋友,準備辦一個民間刊物將大家重新聚集起來,共同寫作并鼓舞士氣。因為大學時代他們那幫同學所辦的文學社刊物被學校有關部門粗暴地查禁了,這個事情甚至還影響到當時一些人的畢業分配。加上大家各奔東西后,天各一方,需要彼此溫暖,找到類似文學之家的感覺。我之所以這么說,是記得韓東當時來信建議我和他的大學同學們如楊爭光、王川平等人建立通信關系,第一次給他們去信時,我還很粗心地將分別寫給他們的信裝錯了信封,于是他們自行調換了一下后分別給我作了回復,弄得我很慚愧。因為我和他們之前并不熟悉.只是聽了韓東對他們的介紹,因而信的內容可想而知是大同小異的一番話。在韓東倡議下,就在西安辦起了一份叫《老家》的刊物。韓東是當然的主編。《老家》的主要成員基本上是山東大學出來的一批人,如小君、楊爭光、王川平、吳冬培、鄭訓佐等,本地的一開始就是丁當等一兩個人,除此之外可能就是我了。這個刊物因條件限制,應當說比較粗陋,我看到的就是用蠟紙刻寫后印的,20個頁碼左右,好像是一共出了三期。前面是發詩歌作品,后面有一點讀后感之類的言論,有大家的通信摘錄。1984年韓東調回南京財貿學院馬列教研室任教后就停刊了,也可能是之前在西安就不辦了。
《他們》是韓東回到南京后起意興辦的。因為當時他看到了蘭州封新城辦的《同代》等民刊后,讀到一些好詩,也結交了一些好詩人,他希望有一個共同的刊物能被這批詩人認可并將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呈現、共同寫詩。1984年6月,韓東因要照顧母親從西安調回了南京。這年下半年,他來信告訴我,己聯系了一批朋友,想在原來《老家》的基礎上,辦一個新的民刊。他在信中提到的一些人我已有所耳聞,有的還建立了通信聯絡關系。1984年底,是他和小君結婚后的那個冬天,我去南京藍旗新村他們的家,正好他剛剛從外面回來,取回了南京藝術學院的畫家丁方專門為刊物畫的一幅畫,就是后來用在第一期封面上的一個男人手托鴿子的素描。他和小君都很欣賞這幅畫,有點興奮,反復對我說“絕對棒”。然后就是煮酒論英雄的味道,談的名字就是丁當、于堅、呂德安、馬原、李潮、蘇童、乃顧(顧前)、李葦、丁方、王寅、斯夫(陳寅)、雷吉、斯微粒等一批人,韓東拿出他們的近作和我一起看,有的還讀出聲音來。他們夫婦也告訴我聽到的關于這批人的奇聞逸事。還聽說了許多朋友取的候選刊名,記得有乃顧取的“諾爾貝”、于堅取的“紅皮鞋”等等,當時我建議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就繼續叫“老家”,好像丁當和小君也有此意,認為這樣有延續性,但韓東堅決不贊同,說對其他沒有在“老家”時期認識的朋友和沒在“老家”上發過作品的人不公平,容易給人太小圈子和太小氣的印象。最后是由韓東自己確定了他為這本新刊物所取的刊名《他們》,后來被大家一致認同、叫好,事實上這個名稱也確實與眾不同,樸素大方,別有意味,體現了《他們》的一種共同審美趣味。在這以后的多次聚會中,韓東為這個刊名多次流露得意之色。回頭想想, 《他們》針對主流詩壇的“他者”意義和不同凡響確實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的。上述說到的這批人也就成了《他們》最早的基本作者。還有一點就是,當時我們收到的詩歌民刊大多是區域性的,就是說作者都相對集中于某一省份或者城市,而《他們》的作者分散于全國各地。 《他們》中的小說作者我猜測可能是由韓東的哥哥李潮推薦來的,因為他哥哥當時在南京的一家叫《青春》的雜志當編輯,《青春》當年是很有影響力的刊物,從天南海北的作者來稿中會發現好的稿子,至少我知道馬原、乃顧(顧前)、阿童(蘇童)就是通過李潮的關系認識的。為什么我后來在編《“他們”十年詩歌選》的后記中說韓東是《他們》實際上的主編和靈魂人物呢,就是基于這本刊物離不開他的一手打造和為刊物所設計的理念。他聯絡幾乎所有的人,也說服大家求同存異,事無巨細地全力操辦,還要承擔種種風險。
因為知道《他們》第一期的亮相很重要,這一期基本上是由韓東一個人在操持,南京的幾個主要成員出資湊了一點印刷費。1985年3月7日第1輯正式印出來,印數是2000冊,之前在我的回憶文章中我記成了1000冊,后來問了老韓幾個人,才知道記錯了。在第1輯的作品目錄前標有“他們文學社內部交流資料之一”的字樣,這也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的權宜之計。內文小說打頭,然后是詩,詩的分量重一些。小說有李葦的《我為什么進不了電視臺》、蘇童(阿童)的《桑園留念》、乃顧的《我的秋》、馬原的《拉薩河女神》。詩歌作者有于堅、小海、丁當、韓東、王寅、呂德安、斯夫(陳寅)、封新城、陸憶敏以及貝斯、述平、陳東東、李娟娟等。丁方為這期刊物設計的封面是一個男人手托一只鴿子的炭筆素描,封二是韓東為這期的主要作者每個人所寫的一句描述性的話,記得馬原是“馬原想獲諾貝爾文學獎”,于堅是“昆明于堅一輩子的奮斗就是想裝得像個人”,為呂德安寫的是“呂德安是個幸運的詩人沒有什么不幸的事情”,韓東本人則是“南京韓東有錢上得了賭場往后全憑運氣”,為我寫的是“蘇北小海還是老樣兒”。刊物出來后主要由韓東分別寄送各地作者。我在老家海安收到的一包雜志是從《青春》雜志社寄出的,韓東當時寫信給我用的信箋也是《青春》的。出乎意料的是這期刊物在各地引起了強烈反響。首先是各地未謀面的作者們為有了一個自己的刊物而歡欣鼓舞,其次是各地民刊和讀者紛紛來信來稿,還有從刊物上留下的聯系地址寄信要求轉給這一期的某個具體作者,有些信都沒轉到作者本人手上,記得我到南大讀書后收到一封信是開口的,就是說信己被哪位哥兒們或者幾個哥兒們打開集體傳閱過了,一定是比較好玩才再轉給我了。這在當時很正常。聽說也有一些作者要求加盟“他們”。隔了幾個月,我進南京大學讀書后,又領到了一些刊物到宿舍,給我的同學們看到了,一搶而空。對他們中一批有志從事創作的人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們》作為一個開放的平臺,前前后后有許多人參加,第2輯《他們》1985年9月出刊,作者就有雷吉、丁當、小君、于堅、李胡(李潮)、王寅、小海、韓東,在十一人集欄目中有柏樺、張棗、普珉、徐丹夫、李葦、吳冬培、菲可、陳寅、裴莊欣、陸憶敏、陳東東等,小說作者有張慈、乃顧、蘇童。封面仍由丁方設計,他和湯國、雷吉、莫鳴等人還為這期刊物作了一些插圖。 《他們》第3輯(1986年)由電腦打印,共印200冊,這一期沒有小說,全部是詩,作者有小海、于小韋、小君、于堅、任輝、普珉、呂德安、韓東和丁當,此外還有賀奕的評論《絕處逢生——從中國當代詩歌談起》。前面三期的作者基本可以歸于“他們”的第一個時期。從第4輯開始,應當說是“他們”的中期,也是最熱鬧的興盛時期。南京大學我的一批同學和南京工學院(現在的東南大學)的一批新生力量進來了,大家開玩笑稱作兩大方面軍。南大方面軍有杜馬蘭(杜駿飛)、賀奕、李馮(李勁松)、劉立桿(劉利民)、阿白(王青華)、海力洪以及后幾屆的張生(張永勝)等,還有同學姜雷、曹旭等人也是一個圈子里面的好朋友;南工方面軍有于小韋、任輝、吳晨駿、朱文等人。等這批同學畢業了后,在1989年至1993年間《他們》休刊了幾年。從1993年第6輯重新出刊到1995年第9輯終刊,應當算是“他們”后期了,除了我們這些老“他們”外,新的面孔是更多了,作者達到四五十人的規模了。有些作者我熟悉,有不少人我已經不認識了。
姜紅偉:在大學期間,您參加或者創辦過詩歌社團或文學社團嗎?擔任什么角色?參加或舉辦過哪些詩歌活動啊?
小海:在大學期間,我參加或者創辦的詩歌社團或文學社團,在校外就是和韓東等人共同創辦的《他們》,整個大學四年圍繞著《他們》有許多的文學聚會活動。
在南大校園內就是進校不久和一批與我一樣有著文學抱負的同學,共同發起創辦了南園文學社。當時的南大就在現在的鼓樓老校區,隔了一條漢口路,分南北園兩個校區,一個生活區一個教學區。記得我是南園文學社的社長吧,也組織了一些文學活動,并編輯了同仁刊物《南園文學》,主編是同學程士慶,他很熱心,編務主要是他干的吧。除了南園文學社之外,中文系還有一個辦了多年的南園詩社,編輯有自己的同仁詩刊,我剛入校門時就存在了,主要是高年級的學長們在辦,我的詩也在那本詩刊上刊登過。但我參加他們的活動很少,我的主要心思是用在《他們》上,畢竟這是有所區別的兩種刊物。
姜紅偉:當年各大高校經常舉辦詩歌朗誦會,給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詩會是哪幾次?
小海:1985年底或者1986年春天在南京大學禮堂記得有個詩歌朗誦會,是南京“對話時節”的周俊幾個人搞的,我和韓東、小君一起去參加過。請了一些電臺主持人來朗誦,也有作者自告奮勇自己上臺朗誦,是中規中矩的那種。
詩歌朗誦會比較小型的是當時南京的詩歌角,社會上的一些詩人和南京幾個高校的詩社一起弄出來的。記得是在距離雞鳴寺與南京市政府不遠的一塊小樹林里,我到南京工學院去找于小韋他們玩的時候順路去看過幾次,有四五個詩人參加,有時會將詩稿用夾子就夾掛在樹枝上讓行人“參觀”,現場會有一個人在朗誦,聽眾是像我這樣過路的或者是學生。有一次我還見到過一位據說是哈薩克族的詩人在那兒朗誦,挺有風度,吸一口自己用報紙卷的莫合煙,抬頭仰望天空,鼻孔里面噴吐出煙氣的同時,一個長句子也隨之飄蕩出來了——后來,有一群畫家和詩人在南京玄武湖草坪上搞了個名叫“曬太陽”的活動,“曬”畫的同時,印象中也夾雜過詩朗誦活動,我就碰到過我們學校外文系的一位詩社同學陪幾個留學生在那里讀唐詩。
姜紅偉:目前,詩壇上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是繼朦朧詩運動之后、第三代詩歌運動之前的一場重要的詩歌運動,您認為呢?
小海:我基本上贊成你說的,但似乎也沒有那么嚴格的區分。和朦朧詩人一起出現的或者出場的也有“文革”后最早恢復高考的那批大學生詩人,甚至有論者將他們也劃入朦朧詩人群體中去的。有的也將那些詩人劃入第三代群體。這么一來,第三代的跨度就太大了,概念的界限也就模糊了。我覺得關鍵是看具體的詩人和作品而不是看處在第幾代中,多少代其實都和詩沒有多大關系,可能有點“文學史”的意義。真正的文學史研究也不能這么因陋就簡圖省事兒。古往今來的好詩,不少是在“代”外的,按代站隊或者論資排輩其實都是詩歌之外的事情。好詩人甚至在“詩”外——過去被認為不是詩的東西,今天的課堂里面可能正逼迫著孩子們在背誦呢。
姜紅偉: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嗎?時隔多年后,大家都很關心您的近況,能否請您談談?
小海:得失就是所謂的詩好詩壞,得失寸心知。
我這幾十年基本上能堅持干下來的一件事,就是寫詩,中間雖有間斷,但都不長。在大學生階段和《他們》階段,主要還是一個學習寫作的階段,或者說是正在向成為一個自覺的詩人過渡與轉變的階段。
這么說又有點不對,說到校園,文學應當是我終生學習而不可能畢業的一所學校。
姜紅偉:目前,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這一現象已經引起詩歌研究者的高度關注,具體地說,我正在編著《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史》-書,請問,您對我編著大學生詩歌運動史有什么好的意見和思路嗎?
小海:哦,我沒有太好的意見與建議。
理由就是,任何一部歷史書作者也許都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因為任何一部書都只是構成“歷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在創造“歷史”。從人類產生以來,歷史命運就是人的命運的一分子。詩歌藝術史也許會為詩歌增加一點“肥料”和談資,留給有興趣的人。
對編輯家來說,熱情、眼力、胸襟、抱負缺一不可,主要的原則、編輯方針、人選、篇目和取舍,要由你來“獨裁”。當然,這也是承擔一份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