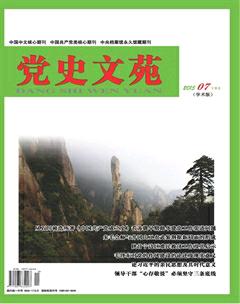從石川禎浩所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看蘇俄早期助華建黨工作渠道問題
金一馳
[摘要]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所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以極其翔實的資料考證了若干問題,其中涉及蘇俄早期助華建黨工作渠道問題的研究,但并不系統。鑒于這個問題有其獨特的考證價值,但在學界研究尚處于并不系統的狀態,筆者試圖以《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為藍本,梳理若干蘇俄對華工作渠道,剖析其發展,從中看到歷史的復雜性與必然性。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 蘇俄 建黨 工作渠道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同時,事物的發展有內因也有外因,蘇俄在這個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成功打倒俄國臨時政府,獲得勝利,成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即蘇俄,當時是一個獨立國家,1922年12月30日更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本文所指蘇俄皆特指更名前的國家。在1917年11月7日至1922年末,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蘇俄的對華工作分為好幾個系統,既有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共產國際系統,也有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員部系統,還有俄國共產黨的系統。這些系統不僅相互間關系復雜,而且因內戰局勢的發展而時常改組,僅弄清其變化過程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國遠東境內成立了一個緩沖的遠東共和國,其外交部門和地方黨組織相互間沒有充分協商就分別加入了對華工作,使得情況更加混亂”[1]p80。
為了有針對性地研究蘇俄助華建黨的渠道問題,筆者依托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所著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選取研究時間范圍上限為1920年,即遠東共和國成立之年,下限為1922年,即蘇俄更名之年,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1921年正被包含在內,試圖梳理分析中共建黨前后的若干鮮為人知的蘇俄對華工作渠道,從而理清蘇俄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作用。
一、俄共(布)系統
俄共(布)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興起的布爾什維克派,1903年與孟什維克派決裂后事實上成為獨立的政治派別。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裂,此后布爾什維克派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直至1925年更名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2]。因此,本文所說俄共(布)特指更名前的黨組織系統。1920至1922年間,俄共(布)在中國自身先進知識分子渴求救國的背景下,幫助建立共產黨,其渠道眾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也筆墨最多,具體有:
(一)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8—1921.1)。根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記載,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是在1918年12月17日成立的,作為黨中央的直屬機關貫徹執行在西伯利亞的所有工作,開始于托木斯克成立,后隨著軍事形勢的好轉,遷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現新西伯利亞)。“當時,伊爾庫茨克有許多僑居俄國的中國人、朝鮮人,他們也為了成立共產主義組織而開始了活動。”為了有針對性地對東亞尤其是中國開展工作,“俄共西伯利亞局則于1920年8月在伊爾庫茨克設立了東方民族處,并以此為對外工作的窗口”。關于東方民族處的組織和成員,根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有岡察洛夫、布爾特曼、加蓬,后來又加入了布龍斯泰因,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布爾特曼和布龍斯泰因兩個人。該處自一開始就按民族設置了下級科室,陣容頗整齊。下級科室有中國科(阿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朝鮮科(格爾舍維奇)等;因為沒有懂日語的人才,暫時沒有設日本科。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科里沒有中國人”。為什么在對華的中國科中竟然沒有中國人呢?石川禎浩這樣解釋:“據說阿勃拉姆松和霍赫洛夫金二人的漢語都很好;不過,也可能是因為在當地眾多的中國僑民中,找不到合適的共產主義者。”[1]p82
在該處組成人員中,布爾特曼是東方民族處首任主席。“作為與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最早進行接觸的俄國使者,布爾特曼這個俄國人的名字并不陌生。”[1]p74書中引用布爾特曼的傳記,介紹了他從哈爾濱到天津的革命活動,接觸了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考察了革命形勢,1920年離開天津后,“3月初到達上烏丁斯克(現烏蘭烏德),成為遠東共和國政府的一員,同年6月抵達伊爾庫茨克,在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工作,該局設東方民族處后,就任該處主席,主持該處的日常工作,直至去世”[1]p76。
根據相關材料,中國科負責人阿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的任務為:“1.首先和主要是在中國本土工作。2.在旅居俄國的中國人當中做聯合和共產主義教育工作,旨在培訓他們從事中國革命工作。3.在伊爾庫茨克的中國營紅軍戰士中,進行為中國革命工作的培訓。”[3]此外,根據檔案記載,東方民族處成立后,原歸于俄共遠東州委管轄的蘇俄向中國派出的第一位正式“使者”維經斯基也劃歸該處領導,所以維經斯基1920年8月以后的工作匯報都寄到該處,也曾回國到東方民族處匯報工作,參加該處召開的會議[4]。該處在1920年9月30日致電維經斯基,任命他為該處派遣到中國的工作人員的領導(全權代表)。東方民族處對維經斯基等人具體要求:向中國介紹蘇俄的遠東政策、遠東共和國情況;幫助中國分散的共產主義性質的團體集中起來,組織為統一的共產主義政黨;“召開一次全中國的革命代表大會”;變賣珠寶,用部分所得款項創建一個印刷廠;以上海為中心,聯絡中國各地的組織,聯絡日本、朝鮮等地的組織。這些指令,維經斯基都在中國逐步執行[5]。
1921年1月,根據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決定,東方民族處撤銷,其原有成員編入遠東書記處,即原屬于俄共的東方民族處撤銷編入屬于共產國際的遠東書記處,該工作渠道正式結束。
(二)俄共遠東州委(1920.3—1920.8)。根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記載,俄共遠東州委1920年3月3日成立于上烏丁斯克(現烏蘭烏德),后來遷到赤塔,目的是“為了管轄即將成立的遠東共和國境內的黨組織”。“遠東州委剛成立時是俄共西伯利亞局的下級組織,同時,因為遠東全境尚未統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設了分局。這個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內設有外國處,作為對外工作機關。”1920年8月,“遠東州委升格改組為與俄共西伯利亞局同級的俄共中央委員會遠東局”[1]p80。這個時間點不是巧合的,俄共遠東州委在東方民族處成立的同時進行改組,實現由地方黨委升格為中央直屬部門的轉變,其工作方針也進行了調整,對華工作權力大都劃歸東方民族處。endprint
根據石川禎浩的考證,“作為蘇俄向中國派出的第一位‘使者、其后數次出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給予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巨大影響的格里戈里·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原著譯為“魏金斯基”——筆者注),是于1920年4月從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國的”[1]p84。而派遣機構是“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的確,1920年1月,“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遠東州委(此時仍處于地下狀態)在1月剛剛發給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通報說,準備與中國革命家建立經常性聯系。在這種形勢下,威廉斯基不僅出席了在尼科里斯克召開的俄共遠東地區代表會議……后來還親自去了中國”,由于“當時的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勢力相當大”,而當時身負俄共政治局使命的遠東事務全權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又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因此威廉斯基肯定與派遣維經斯基一事有關,石川禎浩也認為“維經斯基一行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去中國,就是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指示的”[1]p73。
據此,“維經斯基來華,按上述蘇俄對華工作機關的演變來講,是在其中的主要機關即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成立以前”,又由于派遣維經斯基與威廉斯基有關,而威廉斯基又與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有著密切聯系,在當時消息不通、戰亂頻繁的歲月里,維經斯基來華“起初可能是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獨自進行的對外工作之一”[1]p84。事實上,在后來東方民族處遞交給莫斯科的報告中,維經斯基一行赴中國確實被看成俄國遠東和東西伯利亞城市在遠東獨自進行的行動之一。結合上文對東方民族處的分析,我們可以概括為,作為蘇俄對華工作的著名使者,維經斯基在1920年4月至8月期間,是作為俄共遠東州委的工作渠道來華的,在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則是作為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工作渠道來華的。
(三)俄國共產華員局(1920.6—?)。根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俄國共產華員局主要是由在俄的中國僑民組成,直屬俄共(布)中央并接受其領導的機構。1919年左右,當時,在俄國領土上,有40萬—50萬中國人居住在西伯利亞、遠東一帶。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勞工。十月革命后,這些中國僑民中的部分人也響應革命而成立了各種組織,其中比較活躍的就是劉澤榮和張永奎等留學生組織的“中華旅俄聯合會”(1917年4月成立于彼得格勒),以及十月革命后由該組織發展而成的“旅俄華工聯合會”(1918年12月成立于莫斯科,會長是劉澤榮)。這個聯合會得到蘇維埃政府的承認,一方面幫助貧困的中國工人回國,同時作為事實上的中國人的共產主義組織開展活動。其后,“旅俄華工聯合會”擴大了活動規模,并建議蘇俄政府向中國派遣代表,同時于1920年6月25日在會內成立了“俄國共產華員局”,7月1日得到俄共中央委員會承認,成為實際上的黨組織。
俄國共產華員局成立后,旅俄華人黨組織加快了發動中國革命和建立國內黨組織的步伐,開“中央黨校”“教育培訓班”,發行《震東報》《大同報》《華工報》《共產主義之星報》等報紙,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6]。與此同時,就在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地方黨組織的對外工作機關漸次形成的時候,俄共中央于1920年9月2日決定,把中國僑民團體在莫斯科成立的上述組織遷至遠東,改稱“遠東俄國共產華員局”,并令其與伊爾庫茨克的東方民族處直接聯絡、從事活動,該舉措擴充了東方民族處的人員,也實現了多渠道合作[7]。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并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后,為了解決跨黨問題,大批華員局黨員轉為中共黨員,其中一大批華員局黨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負責人,他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骨干力量,自覺地充當著橋梁和紐帶,推動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向前發展。而俄國共產華員局究竟于何時撤銷,由于筆者掌握的資料有限,因而未查到明確時間,留待后續研究。
二、共產國際系統
共產國際是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組成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于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又名“第三國際”,以別于第二國際。共產國際初成立時各國支部很多都是從第二國際原有的支部分裂出來的,即是說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發展為第三國際,正式拋棄改良主義,而號召世界革命。但在中國,與第二國際聯系的組織很少,內生分裂組建支部并不可取。因此在1920年至1922年間,本著“世界革命”的精神,共產國際在中國自身革命因素的依托下,大力開展對華工作,幫助扶持建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對此重點講述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但根據其他檔案,經過系統化補充,具體有如下渠道:
(一)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1920.4—1920.8)。1920年4月,俄共(布)派遣維經斯基來華,其后,共產國際正式設立指導中國革命的下屬機構,第一個即是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根據相關材料,該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書記處全會選出三人臨時執行局,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任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中國科的工作任務是:進行黨的建設、工會建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出版工作等,幫助“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8]。1920年8月,也就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前后,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即自行解散,相關工作移交東方民族處。由于該機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中并未明確提到,因此不作詳細介紹。
(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1921.1—1922.1)。對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這樣記載:“再來看共產國際系統,其對華工作的準備工作也是自年下半年正式開始的。如前所述,同年7月,馬林、劉澤榮、樸鎮淳等人曾于莫斯科就在上海設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一事進行過磋商,后來,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選出的執行委員會在8月決定,在世界各重要地區派駐駐外代表,并指定馬林為駐上海代表。9月15日,該執行委員會又決定在遠東設立共產國際書記處。”[1]p82這個在遠東設立的“共產國際書記處”也就是后來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事實上,根據檔案記載,這個機構的成立和東方民族處的工作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當時通信條件不好,對華各渠道都不便協調,而各路代表都想得到共產國際支持,派出的代表使東方民族處的工作呈現復雜局面,有能力的共產黨員數量不多。在此情況下,東方民族處主席布爾特曼于1920年9月15日建議將東方民族處改組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書記處,命舒米亞茨基和岡察洛夫立即到莫斯科。對比石川禎浩和相關檔案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布爾特曼建議改組東方民族處的時間與共產國際執委決定設立遠東書記處的時間一致,鑒于共產國際的組織架構和當時混亂的環境,因此可以認為這兩者事實上是一回事。endprint
對于這個即將成立的新機構設在何處,蘇俄各系統有一番爭執:“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遂反復要求把共產國際的書記處設在該處。開始時,共產國際書記處似乎準備設在遠東共和國首都、同時也是俄共遠東州委所在地的上烏丁斯克(或赤塔)。后來,圍繞遠東的書記處應該設在哪里,以及如何統一山頭林立的各機關進行了反復探索”;“最后,1921年1月,根據俄共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分別于1月5日和15日做出的決議和決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設在了伊爾庫茨克。”[1]p83根據前面的介紹,東方民族處也是設在伊爾庫茨克,其撤銷之時正是遠東書記處成立之時,且基本保留了東方民族處的人員,加上布爾特曼在其中發揮的特殊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是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合理繼承。“至此,原來分屬共產國際、東方蘇俄外交組織、黨組織的對華工作機關,基本上統一到了共產國際系統里。”當然,這個渠道的統一只是“基本”而已,還有許多矛盾和沖突蘊藏其中。
隨著形勢的轉變,共產國際要把中心移到莫斯科,于是該機構的工作和活動到1922年春便逐漸分散到其他部門去了,結合下文關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的記載,遠東書記處實際在1922年1月便逐漸事實上停止了活動[9]。
(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1922.1—1926.3)。根據檔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于1922年1月成立,并由伊爾庫茨克遷至莫斯科,由維經斯基任東方部部長,斯列帕克為副部長、考夫曼為中國顧問,并由這三人組成領導班子。新成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要任務是,代表俄共(布)和共產國際擔負具體指導與中國、朝鮮等國的革命者建立聯系和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具體工作主要有:編輯遠東通訊,按名單寄給各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成立外文圖書出版社,建立編輯室,出版科教刊物,開辦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圖書館等[10]。
1922年12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局收到了維經斯基等三位東方部領導人提出的書面報告,建議將東方部分成三個獨立的部門:近東部、中東部、遠東部。根據建議,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專門委員會討論修改后,1922年12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共產國際東方部直轄局,即史料所稱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部(遠東局),該部于1923年1月2日獲得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局正式批準。其任務是:向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工會提出建議;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報告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情況;對出版和政治運動給予指示;加強與中國的聯系,以及監督婦女和青年運動等[11]。
1926年2月3日,時任東方部部長的拉斯科爾尼科夫寫信給季諾維也夫,報怨東方部“一直處于不正常的工作條件下”,一個多月后,東方部被改組為近東書記處和遠東書記處,而其下屬的遠東部也隨之改組,該渠道正式撤銷。鑒于《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對上述兩個機構未有明確說明,加上成立和運作時間在蘇俄歷史中的邊緣性,在此不作詳細闡述。
三、遠東共和國系統(1920.8—1922.11)
遠東共和國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詞,它于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1922年11月15日宣布歸并蘇俄。它是蘇俄國內戰爭期間在遠東地區創立的一個與蘇俄政權并存的獨立共和國。作為日蘇之間的“緩沖國”,遠東共和國為保衛和鞏固蘇維埃政權起了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作為獨立的國家,遠東共和國曾與毗鄰的中國展開過積極、實際的外交活動,并幫助共產國際與俄共(布)傳遞情報,構成國際關系史上的重要一頁。因此,在蘇俄早期對華工作渠道中,遠東共和國系統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組成部分。在我們研究的歷史范圍內,具體渠道為1920年派往中國的遠東共和國使華代表團,《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對此說道:“遠東共和國雖說在蘇俄控制之下,卻在以獨立國家的地位開展對華交涉。遠東共和國的正式對華外交交涉,始于以優林為團長的代表團(名義上是商務代表團)訪華;該代表團于1920年8月26日到達北京。”[1]p83
但是,根據相關材料,優林代表團作為遠東共和國的合法代表,與當時的中國政府(即北洋政府)進行了大量交涉,主要關于政府外交層面的內容,比如中東鐵路的歸屬等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沒有公開的檔案提及該代表團對于在華建黨的幫助,但卻提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和《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提到的一個蘇俄早期對華“密使”是同一個人,在筆者有限的資料里,這個人將遠東共和國與蘇俄對華建黨工作相聯系起來,使其成為蘇俄對華網絡的有機組成部分。
這個人是阿格遼夫。根據“駐上海的日本武官1920年3月的報告稱,據駐滬俄國武官的情報,‘俄國人阿格遼夫正與李仁杰(李漢俊)、呂運亨等密籌,計劃發行俄漢兩種文字的《勞動》雜志。”我們知道,李漢俊是后來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人物之一,因此這個時候接觸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其寓意是深刻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也于同年5月報告說,‘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長阿格遼夫2月由上海經天津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數日后再度來華,5月15日旋又離開上海,經北京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看得出,這個時期的阿格遼夫頻繁穿梭于遠東各地。他的頭銜是‘原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長。”[1]p77事實上,阿格遼夫在1918年6月末蘇維埃被政變推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參崴)復活后,確實曾經做過市長,按黨派立場來說,阿格遼夫是孟什維克。在1920年5月作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臨時政府的非正式代表時,阿格遼夫雖然來到了北京,但因不能代表整個遠東地區而未能受北京政府的重視和接待。而“在俄共方面1920年12月的報告中,阿格遼夫是被當作維經斯基受派來華前獨自活動的俄國僑民之一來記述的。但他與維經斯基的活動有什么關系,卻完全不得而知”[1]p78。《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在此對阿格遼夫的介紹就此打住,僅憑以上內容,似乎無法把阿格遼夫與遠東共和國的對華工作聯系起來。但是,深入分析遠東共和國史,對比來看,阿格遼夫在遠東共和國使華代表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隱藏的助華建黨線索也若隱若現。endprint
根據史料,優林代表團1920年8月26日來京后即與當時在北京的阿格遼夫取得聯系。之后,阿格遼夫便與優林攜手合作,多方奔走,廣泛宣傳,努力向北京各界擴大自己的影響。在1920年10月底遠東各地方政府聯合大會召開后,各地方政府自行解散,所派北京的代表也組設了聯合委員會,由優林執正、阿格遼夫副之。1921年4月26日,優林和阿格遼夫一同面見中國外交部俄事委員會會長劉鏡人,正是在這次磋商中,阿格遼夫被列入參與會談的遠東共和國代表團一方人選,其名緊排在優林之后[12]。1921年10月,優林回國繼任外交部長,結束了前后一年多的來華入京活動,阿格遼夫便代理優林,最終正式接任遠東共和國駐華總代表,主持遠東共和國代表團的工作。1922年3月2日,阿格遼夫接到赤塔來電,奉令回國,另作任用。4月初,阿格遼夫調回赤塔。遠東共和國司法副部長巴谷勤接替阿格遼夫,繼任遠東共和國駐華代表。從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在1920年8月優林代表團來華至1922年4月阿格遼夫回國,阿格遼夫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八個月,這段時間對于風云變幻的當時來說,并不能算短。考慮到1920年初時阿格遼夫還在與李漢俊等社會主義者一起活動,而蘇俄幫助建立中共的“資金和情報必須經過北京——赤塔這條渠道,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了遠東共和國政府以及俄共遠東州委的介入”,因此在北京期間,阿格遼夫很有可能“借助當時在北京合法活動的優林代表團的力量”幫助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開展活動,“包括文件傳遞、匯款等技術方面”[1]p83。當然這只是筆者的合理推測,有待史料的進一步考證。
隨著1921年12月12日蘇俄代表巴意開斯來華和1922年8月蘇俄代表越飛來華,蘇俄國內外情況開始變化,中蘇外交也逐步開展,遠東共和國的歷史使命行將結束,遠東共和國代表團與中國外交部的交涉也進入尾聲。1922年11月15日遠東共和國宣布歸并蘇俄,該對華工作渠道正式撤銷[13]。
由于蘇俄早期對華開展工作的時候正值其國內戰爭時期,人員與組織變化和流動極大,因此除上述相對正式和長期的工作渠道外,還有一些其他工作系統和個人代表,例如波塔波夫、波波夫等人。波塔波夫原為沙皇俄國的高級將領(少將),十月革命后轉而擁護布爾什維克,開始向蘇維埃政權提供遠東的軍事情報。他“表面上像個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并未得到真正信任”,但根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考證,“他通過活動取得的情報肯定傳遞到了蘇俄方面,而這些情報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來蘇俄的對華工作”[1]p78;波波夫則是蘇俄阿穆爾軍區的現役軍人,其所委派組織并不確定,石川禎浩認為可能是阿穆爾軍區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或者是蘇維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東方司。鑒于《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對此僅有一些支離破碎的描述,夾雜在一些人員的活動中,而這方面的檔案也十分零碎,因此不作過多分析。
四、小結
綜上所述,在1920—1922年間,蘇俄依托其自身黨組織和政府機構、其控制下的共產國際、附庸遠東共和國等多套機構輪番對中國開展試探性和實質性的建黨及地下外交活動,其中涉及組織龐雜、人物眾多,且互相交織,要把這些完全梳理清楚是有相當難度的。為了簡要地說明蘇俄助華建黨工作渠道的發展,根據上文的分析,筆者做一結構圖以方便理解:
上面的結構圖只是一個很粗略的框架,事實上,上述機構的很多人員活動正如《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所說的那樣,“我們只能在零星的警方記錄或回憶錄中知道他們的存在;事實如何,撲朔迷離”[1]p74,而機構的變遷與互相關系更為復雜,各機關間經常變動,且存在派系矛盾,“東方民族處(以及俄共西伯利亞局)與俄共遠東州委(應該是改組后的俄共中央遠東局——筆者注)(以及其領導的遠東共和國政府)的關系卻并不協調。東方民族處屢屢向莫斯科遞函表示不滿,說由于遠東州委和遠東共和國政府的阻撓,無法與遠東地區取得聯系……又直接要求共產國際將該處納入共產國際系統,以避免遠東共和國從中作梗”[1]p82。毫無疑問,這些因素加大了研究的難度和復雜程度,而石川禎浩對史料的嚴謹態度,對考證方法的重視和靈活運用,為這個問題的研究帶來了新資料、新內容和新觀點。在此基礎上,筆者進行發散分析,初步建構這樣一個網絡,一定會有很多不足,希望能啟發和推動中國共產黨創立史的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M].袁廣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薛銜天.共產國際的建黨策略與中共建黨途徑[J].世界歷史,1989(4).
[3]王偉.論蘇俄對華政策及其演變[J].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8(4).
[4]李丹陽,劉建一.新視野下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研究——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評介[J].近代史研究,2006.(5).
[5]占善欽.一部精心考證的創新之作——評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J].中共黨史研究,2006(4).
[6]李玉貞.與中共建立有關的俄共(布)、共產國際機構和人員[J].黨的文獻,2011(4).
[7]黃紀蓮.遠東共和國代表團使華史略(三):阿格遼夫代理時期的遠東共和國代表團在華外交活動[J].黑河學刊(地方歷史版),1986(3).
[8]黃紀蓮.遠東共和國代表團使華史略(四):蘇俄代表團來華后遠東共和國代表團的在華外交活動[J].黑河學刊(地方歷史版),1986(4).
[9]李凡.遠東共和國始末[J].歷史教學,1998(1).
[10]黃紀蓮.遠東共和國與中國[J].世界歷史,1988(3).
[11]吳二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評石川禎浩近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J].高校社科動態,2007(1).
[12]時晨,衡朝陽.走進中共黨史創建史的史料之林——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簡評[J].學理論,009(13).
[13]И.Н.索特尼科娃,李琦.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J].黨的文獻,2011(4).
責任編輯 張榮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