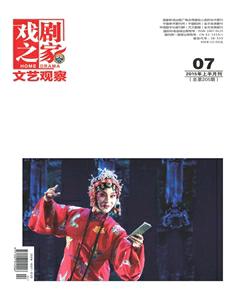“文化改制”后的戲劇院團路向何方?
張莉
【摘 要】目前,院團改制的階段性任務已初步完成,但大部分轉制院團處于“底子薄、包袱重、經費自給率低、贏利能力弱”的狀態,問題主要在于觀念難以轉變、缺乏競爭和創新意識、戲劇的評價體系問題、“狗熊掰棒子”現象嚴重等,在現有形勢下,院團只有在政府和其他社會資源的資金扶植下,立足打造“品牌”,打磨精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整合營銷方式,才能實現改制之后的完美過渡,才能走出戲劇的困境與危機。
【關鍵詞】文藝院團;改制;問題;策略
中圖分類號:J8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07-0015-02
截止到目前,文藝院團的改制在巨大的阻力下雖已初步完成。但是,改制會不會立馬讓中國戲劇院團走出危機?改制之后戲劇應該如何發展,院團應該如何演好新角色?政府應該承擔何種新職能?本文試圖對改制后院團存在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進行分析。
一、院團雖“改制”但羽翼未豐
截止到2013年1月4日,全國文化系統2103家承擔改革任務的國有文藝院團已完成2102家。雜技、話劇、歌舞類院團基本實現全行業轉企改制,以“企業為主體、事業為補充的新型演藝體制格局基本建立”[1]雖然,院團改制的階段性任務已初步完成,大部分國有文藝院團已按要求轉換角色,成為市場主體。但大部分轉制院團處于“底子薄、包袱重、經費自給率低、贏利能力弱”[2]的狀態,離建立真正現代化企業的要求還相去甚遠,而演藝市場發展程度也比較低,應對市場競爭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轉制院團仍面臨諸多“市場失靈”的問題。繼2009年政府為了配合改制而制定的五年規劃“扶上馬,送一程”到2013年,很多院團仍舊無法生存,只能依賴政府繼續五年“扶上馬,送一程”。然而,到了2018年,如果還是無法生存,是不是還要永久送下去呢?可見,這一自上而下展開的文化體制改革,各院團改制的實際效果與主導者的期望還存在較大落差,多數戲劇院團尚未制定應對這一重大轉折的計劃與措施。
二、“改制”后的院團為何困難重重?
(一)最大的問題是“改制”的觀念難以轉變,享受社會保障的離退休人員和從事藝術生產的創作人員的比例失調,導致劇團改革不堪重負。文化部部長蔡武說,“院團改制最核心的問題是人員身份轉換”。[3]院團演職人員長期在事業單位的體制內生存,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哈爾濱話劇院前院長車承濱說:“這樣的‘大鍋飯根本無法調動藝術家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但是你若一下子讓他們轉企改制,很多人從觀念上都無法馬上接受。”[4]演職人員的觀念不改變,改制的措施和改制的方法就難以得到大家的肯定與認同。
(二)“競爭意識淡薄,文化創意缺失”。國有文藝院團一直依靠政府圈養和體制保障,多年來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和生存慣性”[5]。可是,一旦這種保障體制不在,需要去迎接市場和觀眾考驗的時候,劇團驚慌失措,多年的積習使其嚴重缺乏在市場環境下生存的能力與勇氣。而劇團生存越困難,就越依賴于政府所提供的資金等各方面資助,它就越難以保持作為一個文化企業的獨立性與創造性。
(三)戲劇評價體系值得深思。“以節慶為平臺、以政府為核心、以評價為導向”的戲劇呈現方式和評價體系存在問題,沒有轉換成戲劇管理和戲劇演出的良性互動。目前,大多數劇團排戲“基本投資靠政府,基本觀眾是領導,基本目的是評獎”。[6]各種名目繁多的評獎機制不僅沒有起到促進劇團更好的發展的作用,相反,不少劇團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參加評獎,甚至出現許多僅為評獎而創作的作品。如果一味迎合領導意志、評委好惡,既偏離了藝術發展的規范,也背離了市場運作的規律,更與觀眾的審美與需求漸行漸遠。
(四)“狗熊掰棒子”現象嚴重,這是戲劇資源的極大浪費。為了使改制院團自力更生、順利過渡,政府將轉制院團納入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支持范圍。每年都會對院團的新創劇目按預算進行補貼,然后在演出方面按場次補貼。比如,重慶市對市級國有專業院團經審核確認的演出場次,由市財政按標準補貼:1-20場,每場補貼1萬元;21-100場,每場補貼1.5萬元;101-150場,每場補貼2萬元;151場以上,每場補貼2.5萬元。由于政府的補貼政策是按新劇目編排,按場次演出進行的,他們“排戲可以無視上座率,可以不問票房收入,甚至不計成本”,因此,無法調動演職員走向市場的積極性,也無法讓他們形成節約成本的意識。而且,院團每年拿到劇目和場次補貼之后,就轉向下一年的新劇目和新的補貼,這種演一個、丟一個的形式就如“狗熊掰棒子”一樣,這是戲劇資源的嚴重浪費,而且這種演出模式對市場機制的摸索與探討幾乎為零。長此以往,劇團永遠也不可能自負盈虧,走向市場。
三、“改制”策略——出戲、出人、出精品,發展、創新、走市場
改制并不是國家為了扔掉“包袱”,而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投入方式,通過市場機制,建構更有效率的政府文化管理與資助模式”[7]。
(一)“老人老辦法、新人新機制”
院團轉企改制后,應完全按企業方式進行市場化運營。不論人事制度、定薪方式、分配制度等都應作相應調整,以充分調動人員積極性與創造性,適應市場化運營模式。在這一點上,哈爾濱演藝集團做得很好。人員聘用方式上,他們采取“按崗聘用”的新政策,演員角色不再由導演和領導決定,而是競聘角色,由“專家委員會”評定角色人選;在定薪方式上,他們建立崗位與業績相結合的定籌辦法,以崗位工資為主,同時參與演出收益分紅,使員工報酬與崗位職務的責權利緊密結合;另外,演藝集團還針對不同職工的狀況制定人性化政策。如老演員將“在幕后、行政及銷售等崗位上”繼續發揮作用,年輕演員則“通過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以激發創造力和競爭意識。[8]
(二)輸血不如造血
對于轉制院團而言,勝任新的角色要求,成為合格的市場主體,關鍵在于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政府為了讓轉制院團盡快順利完成過渡,從2013年到2018年再“扶上馬,送一程”,可是這種“輸血”的機制應該有所調整,應該有配套制度保證院團自己造血。比如,政府每年都會對院團的新創劇目按預算進行補貼,在演出方面按場次補貼,這種方式無法真正調動劇團對市場、對票房的重視,如若將場次補貼調整為座次補貼,比如一場2萬元,分攤到購票的票價中,每張票補貼100元或者50元,直接在票面上標明,這樣也讓購票的觀眾感覺劃算,得到了政府的觀劇補貼,而購票的人多了,票房自然就高了,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嗎?
(三)著手解決院團資金短缺的問題
政府應出資設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平臺,積極為包括轉制院團在內的中小演藝企業融資提供擔保。這樣,有了貸款的資金,演職人員既有了資金扶植,又會盡量考慮節約成本,還會充分調動演職員參與創作的積極性,在這一點上,北京人藝小劇場做得挺不錯的。
國家發布的《關于支持轉企改制國有文藝院團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鼓勵各類資本依法投資演藝業,這是解決轉制院團資金短缺的重要途徑。多渠道資本的注入,有助于將現階段政府主導投資轉變為投資主體多元化,推動演藝業走向產業化。比如山東省呂劇院在政府幫助下,找到了一個文企聯姻單位——萊蕪鋼廠,萊蕪鋼廠每年贊助劇團100萬元,后來出了幾部精品引起強烈反響之后,萊蕪鋼廠的老總花四百萬元把工廠的舊劇院裝修一新,高興地派大客蓬拉著工人干部趕來觀看。
(四)打造精品、開拓市場、健全營銷機制
市場改制之后,不再以“專家叫好”為目標,而是以市場和票房為導向。應該立足市場打造精品,整合健全營銷機制,開拓演出市場。這種營銷模式完全可以借鑒一些比較成功的民營劇社。
比如,戲逍堂做戲劇,目標是“工業化的流水線產品”。早在2009年,戲逍堂就獲得了“北京楓藍小劇場的長期經營權”,在市場激烈的角逐和競爭之中,戲逍堂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小劇場運營的特色路線”[9]。關皓月在創建戲逍堂時,便開始工廠式的標準化生產,按照項目投資管理化模式來“生產”并“銷售”話劇。戲逍堂最與眾不同的是:獨創了“評嬸”制,并與“會員制進行相互借勢”。
戲逍堂創立之時就實行會員制,到2010年戲逍堂的會員人數已達3萬人。戲逍堂就在超級粉絲中選擇了50名觀眾評審,這50名觀眾評審就被稱為“評嬸”,目的是“保證話劇產品與市場需求的無縫對接”,參與整個話劇的標準化制作流程,如對劇本故事大綱提意見,對劇本提意見,對排練提出建議等等。所以,戲逍堂“從一開始就讓代表市場的力量”參與到創作之中。像《滿城全是金字塔》、《有多少愛可以胡來》等知名劇目都是在“評嬸”的參與下生產出來的。[10]
可見,在政府和其他社會資源的資金扶植下,立足打造“品牌”,打磨精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整合營銷方式,才能實現改制之后的完美過渡,才能走出戲劇的困境與危機。
參考文獻:
[1]楊雪梅.國有文藝院團轉企改制基本完成[N].人民日報,2013-01-05.
[2][5]言恭達.劇團改制之我見[N].中國經濟導報,2013-03-23.
[3][4][8]楊寧舒.哈爾濱市國有文藝團體轉企改制綜述[N].黑龍江日報,2011-04-07.
[6]劉桂成.戲劇團體改革出戲出人才是硬道理[EB/OL].http://www.xijucn.com/html/lvju/20100524/17102.html,2010-05-24/2015-06-15.
[7]傅謹.戲劇院團改制的困惑與前景[N].人民日報,2011-10-18.
[9]劉彥君.當代戲劇文化與中國城市發展[J].藝術百家,2010(06).
[10]姜蓉.戲逍堂:用院線模式搭建話劇平臺[N].中國經營報,2010-01-04.
作者簡介:
張 莉(1980-),女,湖北宜昌人,中國藝術研究院2013級在讀博士,北師大珠海分校藝術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