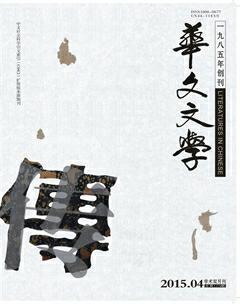失敗的高雅
摘要:在人文學科研究方面,如果你只是為了一個學位,為了一個專業,為了一個能觸摸到的成功的過程或者成功的目標,你這個學者絕對不是一流學者。人文學科是要晃蕩晃蕩慢慢積累的,從失落里面汲取經驗,最后慢慢發現,自己找尋的目標是什么?
關鍵詞:失敗;高雅;李歐梵;演講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5)4-0005-06
李歐梵,國際知名文化學者。現代文學及文化研究、現代小說乃至中國電影,都是他學術研究的范圍。1961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此后赴美留學,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他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等知名高校。這位在世人看來十分成功的學者,求學和任教路上其實磨難重重。學會和失敗相處,方能挫而彌堅。2015年3月,李歐梵先生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博群花節”,作了一場題為《失敗的高雅》(“The Nobility of Failure”)的演講。常言道,“失敗乃成功之母”,可失敗的價值是什么——這正是李歐梵要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經驗。
“失落”的靈感
任何時代都有一窩蜂——都有一種時髦,有一種社會壓力,有一種當時的社會價值。可每個人的生命里不可能只有一樣東西。你總有不同的興趣,不同的價值,要應對不同的壓力。你要問自己,到底喜歡什么。這應該是中學以上、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
小學六年級時,我成績非常好。那時,小學新換了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校長。用現在的話講,他在小學里就實施博雅教育。男生女生都要跳舞,每個學生都要學音樂、體育。雖然當時的臺灣和現在一樣,六年級要惡補、補習,因為要參加聯考考初中。我們已經忙得那樣了,可校長說,不行,你們要去運動、要去玩。
也許我不用功,也許我太自信,當我考新竹中學時,突然失常了:晚上太緊張,沒有睡好,第二天考數學的時候,我只得了40分。要進入當時的臺灣名校,數學一定要60分才行。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恥辱。我父母都在新竹中學當老師。中學的老師和校長都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馬上想,父母怎么辦,他們沒面子了。我跟我父親說,這次考試考太差了。父親沒罵我,說40分就40分吧,咱們想想辦法。父親帶我去見學校的教務長,教務長看著我,對父親搖搖頭說:“你的兒子我恐怕救不了了。”
沒想到發榜的時候,新竹中學多了一項叫“備取”。從前是沒有備取的,那一年設了“備取”,有人說,就是專門為我開的。備取一共12個學生,最后一名就是我。我那時大概10歲,感覺自己抬不起頭來。好在年紀小,過了不久成績就跟上去了,一帆風順到了高中三年級,又面臨人生的第二個考驗。
我的總成績當時是全校第四名,而全校前五名還是前六名就可以保送大學。我覺得自己太幸運了,但社會壓力馬上就來了。當時在臺灣,最好的保送生一定是上醫學院或是理工科,商科沒有人要念。可是我的興趣很明顯,不在理工科。我高一的時候就開始參加各種活動,把班級學生組織起來,組成一個合唱團,比賽的時候我當指揮,最后得了全校第一名。我那時就知道,自己的興趣是音樂、藝術、文學之類的東西,可是,到抉擇的時候,我該怎么辦?
我記得我和父母親第一次開誠布公地說這個問題。我的姨丈建議我學法律。可是法律沒有我想要感受的藝術的氣息。我想念的是文學,又不敢選文學,因為那時的臺灣,念文學出來只能當中學老師。于是姨丈又說,還有一個外文系可選。我就想,不如先把英文念好,到時候可以去當外交官。現在回想起來,我對于當時的大學制度有一個批評。因為當時的臺灣大學,文學院只有四個系,學生選的最多、最受歡迎的就是外文系,其他的是歷史系、哲學系、考古人類學系。其實,我和當時的潮流已經做了妥協。但是如果你現在問我,這四個系最喜歡什么?除了文學之外,我最喜歡人類學,可那時選考古學的人非常少。
當我回顧以前,回憶是跳躍式的,想到的都是片段。常常是老師講過的一句話,看書看到的某一頁,或者是哪里得到的靈感。而這些使我一生受用無窮的詞組、個人經驗,大多都是在我失落的時候發生的。
我進臺灣大學外文系時,一心要當外交官,所以認真練習演講,死背英文。和我同時進臺大的幾位同學,現在都是臺灣文學界真正有名的人物,其中就包括白先勇。大家知道白先勇是怎么上臺灣大學的嗎?那一年白先勇原本考上了,可是由于種種壓力,他跑到臺灣南部的工學院去念水利。念了一年后,他覺得自己實在不喜歡水利,喜歡的是文學,于是第二年又考了臺大。所以,白先勇是一進大學就決定要從事文學的。到大二時,白先勇說要辦一個雜志,這個雜志就是《現代文學》。當時沒有錢,他問家里親戚朋友借錢,全部投在這個雜志上,還把我們都拉了進去。現在大家把我說成《現代文學》的開創者之一,我有點汗顏,因為我當時只是做了一兩篇翻譯而已。
我常和白先勇開玩笑說,就是因為你們太厲害,所以我走了另一條路。不過回想起來,我中學開始興趣就在文學,特別是西洋文學。我現在把《現代文學》第一年的幾期拿出來看,發現有我幾篇文章在里面,那時我的筆名叫“李歐”,翻譯的主要是一些論文。比如托馬斯·曼的論文。時隔半個世紀,我回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學當客座教授的時候就講托馬斯·曼。可我翻譯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這篇論文在說什么,也沒有看過托馬斯·曼的小說。
我們的《現代文學》雜志最后失敗了。魯迅第一次翻譯《域外小說集》,也只賣了幾十本。我們賣了一兩百本,一半以上是白先勇的親戚買的,還有幾本是有些人在書攤上買去的。但是,有的人對于自己的理想真是有一種執著。明知道在世俗眼光里不會成功,但又總覺得,就算是失敗也有意義。我不自覺地從同學的經驗里得到啟示,但表面上還是很膽怯。畢業以后,當時一窩蜂地要到美國留學,我也跟著大家去申請。
現在各位要申請去美國,會到計算機上找很多數據,我們那時候沒有資料,美國大學在哪里也搞不清楚。我問自己,我要申請什么呢?我真正想要申請的是比較文學,可又不敢申請。于是我就亂申請,像釣魚般地亂撒網。
我心里想,我還喜歡看電影,不如申請去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念電影系。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有個老師教西洋戲劇的課,我非常喜歡。聽說美國最好的戲劇在耶魯,于是我寫信申請念耶魯的西洋戲劇。剩下就是選將來可以混碗飯吃但又跟文學稍微有點關系的專業,比如傳媒研究、大眾媒體等等。最后我想,我念外文系的目的就是當外交官,所以又申請了芝加哥大學的國際關系專業。
差不多都準備好了,我父親問我,為什么不試試哈佛。我想,沒有希望何必試。父親說,試試沒關系。結果我就去了,然后發現申請的大學幾乎全部落空,只有兩個大學有回信。一個是芝加哥大學,一個是哈佛。
哈佛給我的信寫著“Alternate for a Scholarship”。我以為“Alternate”是指另一種獎學金,“for”那個字忘記看了。后來知道,原來只是備取!哈佛回信的意思是,如果別的獲獎學金的學生不去,我可以被考慮。我們全家人都看錯了。
芝加哥大學給我的回信,明明寫了一個字叫“Scholarship”,結果上飛機前的幾個月我才知道,芝加哥大學的“Scholarship”只是免學費,沒有獎學金。當時,以我們這樣在臺灣的中產階級家庭,買一張飛機票是我父母全年的薪水。父母辛辛苦苦把錢湊足,買了一張單程飛機票,送我到美國去。
我迷迷糊糊到了美國,完全是失落的。芝加哥在哪里、怎么走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就買最便宜的灰狗大巴的票,一路玩到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就開始念書。美國天寒地凍,我沒有衣服,就到西爾斯百貨公司買一件最丑最便宜的外套。學校里老師講的完全是“天書”。國際關系當時是講理論,于是,我陷入到各種危機,覺得自己到美國完全是荒謬的,可能幾個月都支撐不住。
芝加哥大學的制度和哈佛不一樣,是Quarter制的,十個禮拜就是一個Quarter,學期很短。十個禮拜內要念幾十本書,念完還要寫一篇論文,這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好在那位教授說,你是臺灣來的,懂中文,那你試著寫一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關系。我當時根本沒有念過春秋戰國的歷史,只好去圖書館借書。我記得,我看到一本現在被尊為大師的呂思勉教授寫的關于春秋戰國的書。我就從那本書開始接觸中國歷史的。
這篇論文交給老師,竟蒙老師欣賞,甚至他后來還要留我。可我知道,我不能一輩子搞這個。我有兩條路。其實我想的是再到洛杉磯去學電影,因為在美國最失望的時候,我都坐著火車去看電影。意大利片、法國片、新浪潮片……都是那種怪怪的失落的片子,所以有很多認同感。
后來一個同學說,既然哈佛給過你一個“Alternate”,就再試試看吧。于是我就又試了一下。那個時候我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工作,館長錢存訓先生是在美國漢學界非常有名的教授。他為我寫了一封信,不知道寫了什么,竟蒙錄取。
成熟前要經過認同混亂的階段
也許是因為我在很好的環境讀書,從來沒有想到,我拿到博士學位以后要做什么。各位可能不相信,當時的環境和現在不一樣,現在念書,大概三年就要拿學位。可我們那時在哈佛念博士都是拖。有的人拖了十幾年,我算快的了,拖了8年。在這8年里,我感受到以前教育的不足,拼命念書。我總是覺得自己是不足的,當你覺得自己在這個方面做得不錯的時候,總發現,怎么有的地方還是不知道。
所以,我這里要說一點批評的話。在人文學科研究方面,如果你只是為了一個學位,為了一個專業,為了一個能觸摸到的成功的過程或者成功的目標,你這個學者絕對不是一流學者。可是,現在的制度往往使得一些非常有才氣的年輕同事受制于這個“監牢”,不得不這么做。所以我非常同情香港各大學人文學科的教授。人文學科是要晃蕩晃蕩慢慢積累的,從失落里面汲取經驗,最后慢慢發現,自己找尋的目標是什么?
甚至大學也是如此。我反對在大一時就分專業。我很崇拜心理學家Erikson,“認同”這個詞就是他發明的。大學的目標是什么?按照他的看法,人年輕時一定有認同危機,這段時間就是一個緩沖期,你在大學里可以隨意選課,隨意地找尋自己的興趣。你的一生里,只有大學這個時期可以讓你在教授的環境的保護下,找尋自己的認同。到了社會上,就沒有時間了。也就是說,在人成熟前,要經過認同混亂的階段。我的認同混亂,從大學一年級到博士班,至少10年。我的問題一直是,我是誰,我要做什么?
我最寶貴的一次學術經驗,不是在哈佛不是在芝加哥,是在普林斯頓。也可以說,那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了一年半后,突然收到一封電報,是普林斯頓大學請我去教課。我當時心中萬般不想去,因為我非常喜歡香港,可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說,為了將來的前途,一定要去。于是我到了普林斯頓。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人是飄飄然的感覺;一到普林斯頓就發現,好像又回到我剛來美國時的感受,壓力非常大。普林斯頓請我去教中國近代史,但是近代史里沒有文學,只有經濟史、外交史這些東西。我越教越沒有興趣。這個時候,普林斯頓東亞系知道我在香港教過比較文學課,他們就說,你不如試試教文學吧。我越教就越有興趣,我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也是從無形中得來的。
當我在普林斯頓教到第四年的時候,學校說要考慮永久教職(tenure)了。當時歷史系有名的教授開了一次集體討論會,覺得李歐梵的學術還可以,可是不夠普林斯頓要求的那么好。為什么呢?因為“他的心一半在文學”。我當時正好在寫魯迅,非常痛苦,不知道該怎么著手。歷史系教授看我寫的魯迅草稿,覺得寫得太差了。而東亞系覺得我是搞歷史的,不是搞文學的。最后歷史系主任說,你趕快打電話求職吧,普林斯頓不留你了。我當時傻眼了。那時候我有個女朋友,本來準備結婚了。她第一個反應是,“天哪!怎么辦?”本來我們連家具都買好了,房子都找到了,可她馬上離開了我。
在這種最絕望的關頭,我才知道,失敗的滋味是什么。失敗的滋味,有幾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當你在校園里走的時候,有些跟你熟的同事,見了面不打招呼了,因為你是一個失敗者。美國人的價值里,LOSER(失敗者)是很糟糕的。我后來反省,也許他們有道理,他們正好打中了我的弱點。我的心其實不在經濟史,不在制度史,我的心還是在文學。
最后,兩個朋友救了我。一個朋友為我在當時的一個女校找了一個職位,說我教什么都可以。另一個職位是在印第安納大學教中國古典文學。當時系主任臨時找的一個教授不去了,本來是讓他教元雜劇。于是系主任問我,能不能教元雜劇。其實我只看過一本元雜劇,叫《竇娥冤》,其他都沒有看過。不過我還是說,可以。當人受到極大挫折后,基本的感受就是要“生存”。我當時沒有錢回去,無顏見江東父老。這么多年在美國,怎么能以失敗收場呢?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接受了這個職位。可沒想到,我在印第安納大學如魚得水,因為這個大學的音樂系是全美最大的。學校有四個交響樂團,一個歌劇院,有無數個免費音樂會。我一直喜歡音樂,覺得這里真是天堂。音樂使得我在教學學術研究上精力百倍。
我精力百倍,只是為了爭一口氣。這口氣不是為了我自己,這就是講失敗的價值——要為一個理想,一個有意義的而不是亂七八糟的目的。我當時覺得,美國漢學界不顧現代文學是沒有道理的。他們認為,中國20世紀文學都是宣傳都是政治,那我說,如果這樣,魯迅難道只是一個政客嗎?
我不服氣。可是在美國,你要把一個學科帶上來,不像在華人地區這么容易,一切都要從頭做起。于是我出版了二三十本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和研究系列。沒有想到,我寫的教材還沒有出,已經使我在美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小有名氣了。因為大家要找教科書,就是找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的那本,一看就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這么多年失敗的經驗讓我知道,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的成功,一方面是僥幸,一方面是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湊合在一起。人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會開始反省,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敗。有一樣金科玉律免不了:沒有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你的成功都是虛的。我沒有看過一個馬上成功的例子,即使有,那個成功的人到了晚年也會感到空虛的。愛爾蘭劇作家、現代主義荒謬劇大師薩繆爾·貝克說過一句話:再試一次,再失敗一次,失敗得好一點。當你發現越失敗越好的時候,你就成功了,這是我得到的一個教訓。
朱光潛和維柯,
人文主義在當代中國的一個悲劇
為了準備這一系列的演講,我參閱了不少書,其中一本就是薩義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我閱讀時,發現他處處提到一個奇怪的名字:Giambattista Vico(維柯),這個名字我好像在哪里看過:多年前我曾買過一本書,是柏林(Isaiah Berlin)所寫的,薄薄一本,名叫Vico and Herder,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兩個怪名字──前者是十八世紀初,后者是十九世紀末的歷史學家,內容如何我則不得而知,因為買了沒有看。此次從薩義德書中又發現這個名字,但和上次相遇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了吧。這次倒是一鼓作氣,連帶把維柯的這本大作The New Science(原名是Scienza Nuova)也買了下來,立即翻閱,但不得其門而入。又突然想到:這本《新科學》,不是也有中譯本嗎?譯者正是鼎鼎大名的中國美學大師朱光潛。
朱先生曾在港大讀過書,多年后港大又授給他榮譽博士學位,所以和港大淵源很深。他也曾在中文大學小住過,擔任“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講者,時在1983年。妙的是就在上個月,我突然收到中大出版社贈送的一本小書,就是朱先生演講稿的重印本《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我大喜過望,這不就是偶合(serendipity)嗎?我從未想到研究朱光潛,然而這次偶合的機會卻令我不得不重溯人文主義在當代中國的一個悲劇。
原來朱光潛花了將近五年的功夫,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把這本譯文完成了,但所根據的卻是英譯本(和我買的譯本不同),因為他自稱不懂意大利文。不懂?他不是把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嗎?而且就因為他當年是克羅齊的“弟子”,使他的后半生“背黑鍋”,因為克羅齊的美學(所謂審美的“本能”說)是一種極端的“唯心主義”,和1949年后中國大陸風行的馬克思唯物主義不合。所以朱先生在五十年代率先自我批評,在官方授意之下,這個自我批評又引起了一場為期數年的美學大論戰,批評朱先生最烈的有兩位:一是蔡儀,一個庸俗又機械化的官方美學家,另一個就是八十年代后獨領風騷的李澤厚。
這段美學論壇上的恩怨,大概沒有人記得了,年輕一輩的學者似乎也沒有人研究(數年前浸會大學的文潔華教授編了一本論文集:《朱光潛與當代中國美學》,但可惜沒有討論那次論戰)。我還是有點好奇,為什么朱先生在他的晚年窮畢生精力翻譯這一本意大利的“古書”?
維柯的《新科學》的重要性,我在薩義德的書中有所體會,原來他最尊崇的德國學者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就是維柯的德文譯者,說不定他的曠世名著Mimesis(模擬)也受到維柯的啟發?薩義德從奧爾巴赫發現維柯,朱光潛卻從克羅齊發現維柯——原來克羅齊也是研究維柯的《新科學》的,這雙邊的繼承關系,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既是橫向又是縱向的連接,為什么沒有人文學者細加研究?(中國研究朱光潛的專家還是單邊的,完全忽略了奧爾巴赫─薩義德這條線。)如把這兩線加在一起,就可以重溯一條中西人文主義的比較系譜。
且讓我們先窺視一下維柯的這本書到底講的是什么。英文本前頁有張怪圖(朱先生的譯本中文照樣復制出來):據維柯自己的解說(見朱光潛譯本第3頁),此圖的右上角“登上天體中地球(即自然界)上面的,頭角長著翅膀的那位婦人就是玄學女神”,朱先生在腳注中說明“玄學女神即代表《新科學》的作者維柯本人”,這一個“主觀”的注解使我嚇了一跳,難道就是作者本人嗎?這位作者的地位何其崇高偉大,竟然站在地球之上,而她的“心”竟和天神相通,因為圖中左上角“含一雙觀察的眼睛的那個放光輝的三角,就是天神現出他的意旨形狀”。圖的左下方還站著一個老人的雕像,那就是荷馬,其他象征式物件很多,不能一一解釋了。
真是妙哉!看這幅圖就像看明朝的《推背圖》一樣,玄機重重,須要“解碼”,而維柯就是這個解碼人。看了這本書的序論和第一卷,再參看朱先生譯出的該書英文譯者Bergin和Fisch的序言,和朱先生在中大的演講稿,我們才大略有一個輪廓,原來此書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也只有人可以解釋。這句話現在讀來像是老生常談,但我們不要忘記,維柯生在一個神權甚張,上帝并未消失的世界。他信仰天主教的神,卻反對當時新興的一派哲學家,特別是笛卡兒(Descartes),笛卡兒認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客觀”的數學/科學系統,可以解釋宇宙一切,而維柯卻認為:自然界的科學知識應該留給上帝,但人創出來的世界則必須由人來解釋,這個解釋方法是什么?就是現在所說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維柯所謂的“新科學”就是指對于自然界以外的人的世界——包括歷史、法律制度,甚至遠古時期的神話——“仍可以有科學的認識,因為這個世界是由我們自己的人類心靈各種變化中就可以找到。不僅如此,這樣一種科學在完整方面比起物理學還較強,在真實程度方面比起數學還較強。”(中譯本第25頁)這當然是對我們這些人文學科的學者的一大鼓勵。
朱先生在他中大的演講詞中,對于維柯的《新科學》解釋的更詳細,并在這本中大重印的小書中特別把《新科學》第三卷(發現真正的荷馬)和結論篇放在附錄。原來荷馬代表的是遠古人類的詩性智慧,“荷馬并不是希臘的某一個人,而是希臘各族民間神話故事說唱人的總代表或原始詩人想像性的典型人物”。維柯又說:人類的歷史經過三個階段:神、英雄和人。而“每一個時代的語文又和當時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相應,所以從每一個時代的語文可以推測到當時所特有的文物典章制度和習俗”(朱著第22頁)。原來這就是薩義德推崇奧爾巴赫“語言訓詁學”(philology)的真正原因。我參看這三本書,邊看邊悟,悟出很多道理來,但時間有限,不能在此詳述了。
開始,有一件事我不得其解:到底朱先生翻譯此書要證明什么?維柯的偉大?此書方法的正確?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悟出的一個可能性就是朱光潛要用維柯來證明人文主義并非全是主觀或唯心的;維柯的《新科學》用的也是客觀的“科學”方法,只不過他把人的世界擴大了,甚至凌駕自然世界,十分崇高,所以朱先生故意把那個“玄學女神”說成是維柯本人。而在中國的美學研究領域中這個關鍵人物就是朱光潛自己!維柯和朱光潛都是站在客觀的自然世界之上來解釋一切。“玄學”用以翻譯Metaphysical,我認為并不太妥當。(原意應該是在“物界”或“Physical”之上),它和人的歷史一脈相承。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朱先生要在美學大辯論之后為自己平反,再次證明他的說法是對的,也就是心和物,主觀和客觀是“辯證統一而互相因依”,并非把“唯心”和“唯物”視為兩極,非此即彼,甚至把“唯物”誤解為自然界。其實李澤厚和蔡儀的論點背后是康德和黑格爾(當然也要加以批判),三家共同的出發點都是馬克思主義,在那種語境中,朱光潛勢必要重釋馬克思主義,并把馬克思主義和維柯拉上關系。
在這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美學——我認為朱光潛的貢獻遠遠超過他的兩個對手,因為他翻譯了馬克思的《經濟和哲學手稿》(1844年,又稱《巴黎手稿》),這是馬克思從人的“異化”事實得到的一種“人文”式的詮釋,由此推演出一套美學。朱光潛又發現:原來馬克思自己十分尊重維柯,而且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維柯的這本書。所以“維柯是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第49頁)朱先生在全文最后說了一句話:“我們都是人而卻否定人在創造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能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嗎?”(第50頁)真是語重心長。
朱先生逝世于1986年,距今有許多年了,中國已發生史無前例的社會和經濟大變遷。(但至少在中學課本中可能還讀到朱光潛的名文《談美》)。事過境遷,煙消云散,中國已進入所謂“后社會主義”社會,舉目四望,到處都在“唯物”──商品崇拜,而各種引進的西方理論卻都是偏向“唯心”的。總而言之,唯物和唯心之辯已經沒有意義;朱先生花了那么多年的功夫,卻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它和馬克思主義無關,那就是他用這本大書再次肯定了人文主義。這位現代中國的“玄學女神”,以他的切身實踐,為我們從西方取得一部偉大的人文經典,也以此照亮了半個世紀前中國思想界的混沌。然而,就朱先生自己的一生來看,這還是一個悲劇──這樣一位滿腹經綸又才華洋溢的人文學者,竟然被無謂而庸俗的意識形態折磨了大半生。
朱先生在他的譯本中,特別把《維柯自傳》也譯了出來,置于書后附錄。這個自傳是維柯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寫的,其實就是一部“心路歷程”的記錄,用第三人稱,顯得更可觀,也和笛卡兒故意用第一人稱的自我敘述恰成對比。可惜的是朱先生沒有用維柯的方式寫一本《朱光潛自傳》,但至少我們在他的譯本和腳注中探測到他的心聲。維柯何其有幸,他的《新科學》在中國有一個傳人。
講到此處,我的目的不全在學術——試問多少學者愿意用考證訓詁的方式寫一本大書?我們也無法像維柯一樣,從遠古一直寫到中古,把這個西方人文歷史分成一千多條規則。所以我說我們只能以跳躍的方式抓住幾個時空的連接點,探討下去。至于我個人,已經沒有精力寫大書了——在朱先生在天之靈面前實在慚愧——而只能“誤打誤撞”地作“小研究”(mini-research),也就是多看幾本書并找尋其“互文”關系,自得其樂。
(責任編輯:莊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