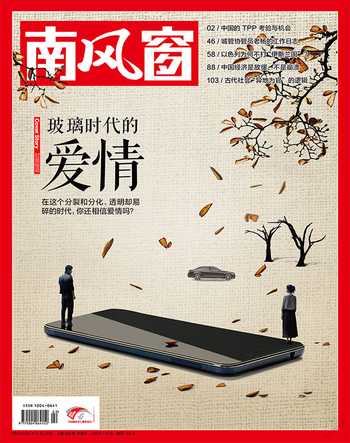臺灣抗戰老兵的親歷記憶
周浩杰

70年前的那場抗日戰爭,是兩岸人民共同的經歷和回憶。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在歷經日本整整50年的殖民統治后回歸祖國。1949年,不少參與過抗戰的老兵去了臺灣。
在紀念臺灣光復70周年的時刻,當時參與抗戰的老兵有不少已經往生,健在者也已經進入到耄耋之年。據臺灣方面統計,目前仍健在的抗戰老兵年紀較輕的近90歲,年紀較長的近百歲。當年參與抗戰的官兵高達300萬人,現在在臺灣的只剩不到4000人。
參與到那場戰爭中的,不僅僅是親自上陣殺敵的老兵,也有立志報國的軍校學員,以及更多的親眼見證日軍殘殺大量手無寸鐵的普通民眾的人。這些抗戰親歷者們對侵略者的痛恨一如當年。
本刊特約記者近日參加了廣州市臺辦組織的一個赴臺訪問團,對仍然健在的抗戰老兵進行了深入采訪。70年前的硝煙彌漫、眾志成城的場景再次變得生動起來。
今年87歲的章鴻茂祖籍江西臨川,抗戰期間他雖然沒有親自上陣殺敵,但從上小學到高中再到陸軍軍官學校學員,經常要躲避日軍的空襲警報,從江西到湖南、廣西,再到四川、重慶,因為戰亂而顛沛流離,對日本人侵略中國帶來的傷痛同樣感同身受。如今,身體還算健朗的他,熱心地為周邊的老兵服務。“很多人都老了,不愿意出來說回這些事。”
祖籍廣東普寧的詹兆浮是其中一位。今年已經93歲的詹兆浮在14歲時便開始從軍,后來主要在西南地區參與對日作戰,隸屬于國軍第五軍200師。只身一人來到臺灣的他如今生活的環境不算太好,逼仄的屋子里堆滿了雜物,顯得有點凌亂,小小的客廳容不了3個人坐下。由于很晚才結婚,他并沒有生下自己的子女。
盡管如此,一講起當年參加過的松山戰役,他便精神煥發。1944年6月,發生在云南省保山市的松山戰役,歷時95天,拉開了中國軍隊大反攻的序幕。
“那時行軍很苦,一邊爬山一邊掉眼淚,爬得手指都磨出一個個血泡,有時一天要穿破好幾雙草鞋。所以一有空我們就自己編草鞋。”詹兆浮一邊說一邊模仿編草鞋的動作,然后說,上戰場前,一個人先準備16雙草鞋。“子彈沒有了,我們就脫了草鞋扔過去,還跟日本兵進行肉搏戰!”
在數不清的戰斗中,讓他印象最深刻也最自豪的,是一次摸黑搶占敵人山頭的戰斗。那是一個下著雨的黑夜,詹兆浮與戰友30個人作為敢死隊,一個人帶兩顆手榴彈,摸黑潛行到敵軍陣營。“敵人有1000多人啊,我們用工具絞斷鐵絲網后,便扔手榴彈去炸,轟!”他做起扔手榴彈的動作,接著說:“炸死了日軍,我們才能沖上去,冒著槍林彈雨前進。”
與正面戰場浴血殺敵的部隊相配合的是敵占區的抗日活動。如今已有臺灣征信業祖師爺之稱的沈建強,當時在江浙一帶參與游擊隊從事破壞敵人后方的活動。
今年87歲的他親眼看到了日本人搶劫、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我感覺到我有責任出來對付他們。”正是由于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6歲那年他不顧父親的反對,離開了自己的小康之家,毅然加入了“滬嘉湖忠義救國軍”。
加入到“忠義救國軍”后,教官帶著沈建強和他的同伴在深山老林、破廟里對他們進行爆破、刺殺、偵查等技能培訓。3個月特訓后,他們便開始對日軍的倉庫、橋梁進行爆破式破壞。
沈建強對第一次任務記憶猶新。他與4個同伴組成一個小組,去炸嘉興的一個日本倉庫。由于年紀小,沈建強偽裝成農村小孩去偵查。“提著籃子,帶著鐮刀,牽著羊牽著牛進城了,查清楚了就回來布置工作。”爆破式破壞完成,等到日本士兵發現時,他們也已經撤退了。
這樣的工作沈建強做了兩年多,當然,他們也遭遇到了日軍的大掃蕩。“一個禮拜沒好好吃到飯,他們來了我們就走,走了就吃飯,一準備吃飯他們又來了。我們住在破廟里,池塘邊,里面有很多蚊子,還有人得了瘧疾。日子的艱苦是你們想不到的。”
在抗戰勝利前的一次爆破式破壞中,沈建強由于沒有算準逃跑的距離,被炸彈的碎片擊傷。“彈片打到大腿上受傷了,被同伴救回來,現在腿上還有一大塊傷疤。”他表示,當時只想著打擊日本軍隊,沒有考慮自己的犧牲,也沒考慮父母怎么想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們當時都很興奮。”已經因傷退下來的沈建強與游擊隊的隊友們第一次穿上了正式的軍裝,攀爬在汽車上進入蘇州城受降。
此時,詹兆浮所在的部隊在云南的一個基地休息。“聽到日本投降,我們都高興得舉起手來,大家呼喊,勝利了勝利了,我們贏了,那多高興啊!”
盡管抗日戰爭已成為歷史,但是日本軍隊殘害中國人,給中國人帶來的悲痛,依然存在于這些親歷者的心中。
雖然過去70年了,沈建強對日軍當年犯下的滔天罪行依然心存芥蒂。對于近年來有日本人否認侵略、美化歷史的行為,沈建強說:“日本人當年的所作所為,鐵證如山,無論如何也賴不掉。”
祖籍浙江大陳島的毛禮正就一次次目睹日軍的殘暴行徑。
大陳島,是位于上海與廈門之間的一座小島。民國年間,運送物資的船只經過大陳島時需要補寄物資,往來頻繁的商船也一度讓這個島富裕起來。1932年,毛禮正就出生在這個小島上。
6歲那年,毛禮正第一次目睹了日軍的殘暴行徑。當時,一艘大陳島的商船從沈家門買了紅棗、大米等貨物歸來,船上有7名船員和4名乘客。大陳島上的老百姓看到商船進港,正準備在碼頭迎接他們的家人時,商船卻被日軍的軍艦攔下。“按理說,這是運生活用品的船,應該放他們進港,但是日本兵卻說船上的人是中國軍人。”他遠遠地看到,日本兵將船上的人圍起來,按住他們的手,然后用釘子將他們的手釘在船的木板上。“最后他們失血過多致死。”船上的11人中,有兩人見勢不對,跳船逃走,有一個人在水上被日軍打死,只有一人回到港口碼頭。“岸上的人本來是迎接親人回來,沒想到卻看到他們被釘死。”
直到抗戰結束前,日本軍隊殘害無辜百姓的行徑不斷發生。有的是日本軍艦在海上舉行撞船比賽,撞沉大量漁船,撞死大量無辜漁民;有的是島民由于被日本軍人置辦貢品不力為由而殺害;還有二十幾個島民僅僅因為小腿硬而被日軍懷疑是中國軍人而槍殺—甚至當日本宣布投降后,大陳島上不愿投降的日本兵集體自殺前還要拉無辜的中國百姓陪死。“13個日本士兵逃到一個屋子里,圍住8、9個老百姓,拉了手榴彈,讓他們一起陪葬。”
對于他的這些回憶,毛禮正的子孫都已經不大相信。“我的子孫都說,日本人不會這么殘暴,是不是您記錯了,但是這些卻是我真真切切所看到的事件。”
在抗戰勝利之后,這些抗戰親歷者們因為種種原因而遷往臺灣,其后各奔前程。戰爭過后,生活依舊要繼續。離開戰場的他們,有的在商界闖出了一片天地,有的卻經歷了大起大落,也有的成為普通的工薪階層,還有的生活并不如人意。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隨著時間的流逝,健在的老兵逐年減少。仍然健在的,多數依然對當年抗戰的崢嶸歲月保留著深深地記憶,以及對故土、戰友和當年戰斗過的地方的深深留戀。
“雖然在臺灣成長,還是念念不忘故鄉,現在每天做夢都是家鄉的事情,家鄉的晚輩,有生之年,如果身體健康的話,我一定會回到大陸去。希望祖國強大、興旺、統一。”兩岸開放探親后,章鴻茂曾多次回大陸,如今雖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期待落葉歸根。
詹兆浮也曾回過廣東普寧老家,“以前的家還在,就小小的一個房子,但是親人都不在了。”他曾浴血殺敵的第二故鄉云南,也沒能回去一趟。“很想念云南,只是現在已經老了,也回不去了。”
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加上業務繁多,沈建強已實現了落葉歸根的夢。在上海,他也購置了房產,基本上一個月回一次大陸。如今,他還有一個弟弟留在大陸,而父母和兩個姐姐早已過世。
對于抗日戰爭的那段歷史,沈建強說:“中國人是不能給日軍欺負的,日軍侵華我們就會萬眾一心對抗他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士是無名的,能活下來就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