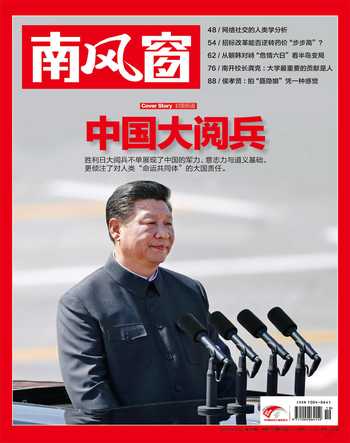黑馬迭出的美國兩黨隱形初選
刁大明
“他們去了華盛頓,然后就軟弱了……我絕對不會這樣,我保證。”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在8月29日全美共和黨團體聯合會年會上,矛頭直指華府圈內人。在6月16日正式跳入人滿為患的共和黨選戰池塘之時,特朗普未必預料到將收獲夢幻般的崛起:從7月中旬至今始終領跑在全美以及艾奧瓦、新罕布什爾等關鍵州的初選民調。在與其他16位參選人對比中,特朗普的某些民調支持度竟然高達25%以上,超過了杰布·布什、本·卡森或者斯科特·沃克、泰德·克魯茲等第二、三名的總和,頗令具政治經驗的黨內對手唏噓不已。

特朗普在民調中異軍突起,驚呆了一眾正統的參選人。
與特朗普意外領先同樣令人訝異的還有民主黨的吊詭選情。根據最新民調,佛蒙特州國會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正在加緊縮短與希拉里的差距:在全美范圍內,桑德斯的支持率已可迫近30%,而希拉里則滑落到50%的紅線以下。即便是在關鍵州艾奧瓦,希、桑兩人以37%對30%幾近打成平手,而這個數字在3個月前還是極為懸殊的57%對16%。
特朗普和桑德斯兩匹“黑馬”的躍出,攪亂了以往關于布什家族對決克林頓家族的選情預判,但仔細看卻并未跳脫近年來美國政治的運行慣性,只能用“形勢比人強”來形容了。
截至7月30日,勝算渺茫的弗吉尼亞州前州長吉姆·吉爾莫搭上末班車,2016年大選的共和黨初選已擠入了17位主流參選人,為1970年代共和黨采納初選制度以來參選人數量之最。對照政治光譜,這些參選人可分幾類:具州長執政經驗的溫和務實派,代表人物如杰布·布什、克里斯·克里斯蒂、喬治·帕塔基等;具國會立法經歷的意識形態派,代表人物如馬可·盧比奧、泰德·克魯茲、蘭德·保羅甚至里克·桑托勒姆等;身為州長、價值觀又極保守的跨界參選人,如斯科特·沃克或鮑比·金達爾等。此外,像特朗普、卡森、卡莉·菲奧莉娜等非政治人物的“亂入”曾一度被認為是純粹的“打醬油”行為,直到特朗普在民調中異軍突起,驚呆了一眾正統的參選人。
特朗普的躥紅與其具有其他政治人物并不具備的跨界知名度與影響力大有關系。根據針對熟悉度的民調顯示,即便是頭頂著“總統世家”光環的杰布·布什也被26%的受訪者認定為“沒有太多聽說過”,而像沃克這樣的一州之長在威斯康星之外的認知度更為可憐,不熟悉他的民眾達到了37%。頗具諷刺的反差是,對特朗普了解不多的受訪者在同期內只有8%。特朗普的名字,在聳立于城市中心的特朗普大廈上、在電視真人秀或脫口秀節目中、在一本本講述實現“美國夢”的成功學傳記里耳熟能詳,足夠鎖定特朗普在隱形初選中的先入為主。8月6日共和黨總統初選首場辯論因吸引到2400萬觀眾而位列收視率最高的非體育電視節目,也得益于公眾對特朗普的狂熱關注。
雖然特朗普不具備傳統職業政治人物的穩健臺風,還多次口無遮攔地發表“政治不正確”言論、甚至把政見演說直接弄成了搞笑脫口秀,但他身上也的確潛藏著某種無可替代的競選特質。比如,這位40億身家的成功商人完全能夠在聯邦法規的允許下“自給自足”地確保競選經費的持續支撐。雖然富商競選公職往往失敗,比如執掌世界摔角娛樂公司(這里“摔角”有別于“摔跤”)的林達·麥克馬洪,兩度角逐康涅狄格州國會參議員席位均惜敗,但至少如今的特朗普不必像其他對手那樣殷勤地跑到加州去拜見因揮金如土而招致罵名的科赫兄弟了。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巧妙地積聚起共和黨陣營各派系的最大公約數:他出身商業,自然能夠滿足傳統商業利益溫和派的要求;他言論激進保守,恰好符合意識形態宗教保守派的口味;而他非華府圈內人甚至是“政治素人”的身份標簽又迎合了公眾反感美國政治極化僵局、迫切渴望徹底改革的內心狀態。甚至,特朗普不尊重女性、歧視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的言論,也被不明是非地認定是“真性情”的表露,頗令共和黨草根基本盤心醉。
特朗普的民意崛起,基本上與2012年大選隱形初選期間佩里、赫爾曼·凱恩、紐特·金里奇、桑托勒姆4位參選人從2011年8月到2012年3月之間接連領先米特·羅姆尼、占據民調榜首各一個半月左右的狗血連續劇如出一轍。其時,4人的先后接棒領先凸顯了共和黨陣營對政壇老將羅姆尼的不認同甚至拒絕,希冀推出反傳統、反建制派候選人的狂熱傾向。
與前次相比,特朗普目前也只是以兩個月的時間領跑民調。他可能像2012年的4位參選人一樣,在不久的將來被喜新厭舊的民意替換下來。孟莫斯大學8月31日公布的一項地方民調已顯示,卡森在艾奧瓦州以23%追平了特朗普,這極可能是領跑者接棒的預備發令槍。如果特朗普在共和黨內出線無望,可能會以獨立人士或第三黨的身份直接投入總統大選環節。
客觀而言,無論特朗普以哪種形式繼續競選,都絲毫無助于共和黨奪回總統大位。如果特朗普被民意拋棄、自己也過足癮而不再戀戰,則可能是造成傷害最小的情形。不過,數月來面對一個“怪咖”作祟束手無策的杰布們,又如何能讓選民相信他們具有能力與資格來領導國家應對內外挑戰呢?如果特朗普奇跡般地獲得提名、在總統大選中與希拉里們對決,他目前的初選優勢都難以在大選兩黨對比中延續,甚至會淪為嚇跑中間選民的軟肋。更為嚴重的是,與特朗普相比,目前任何一位民主黨參選人都享有更多政治經驗,這也會讓共和黨的2016年總統競選更像是一個庸俗笑話。而如果特朗普最終選擇獨立參選的話,他勢必將明顯分散共和黨的票倉,進而讓民主黨人躺著也能進白宮了。
在特朗普領先共和黨初選民調1個月后,民主黨選情在暗流涌動中突遇拐點。8月11日,富蘭克林·皮爾斯大學和《波士頓先驅報》共同進行的民調顯示,桑德斯在新罕布什爾州以44%對37%首次超越希拉里。8月16日,桑、希、特3人同天在艾奧瓦造勢。桑德斯不但吸引了明顯多于希拉里的支持人群,而且在民調中以52%比41%再次擊敗前第一夫人。就在17日,桑德斯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造勢活動竟吸引到了2.8萬人,其中有9000人在無法進入會場的情況下決定留在場外,通過同步揚聲器聆聽了桑德斯的演講。
這位現年73歲的資深國會議員,從參選之初就被認為是所謂的“議題候選人”,即并不謀求也毫無希望謀求最終提名,只是以自身存在來強化選舉議程對某些具有平民主義色彩議題的關注。桑德斯始終以與民主黨結盟的“獨立身份”示人,實則代表了自由派政治勢力中的民主社會主義立場,強調對中低層平民權益的捍衛,從就業到收入不平等,從規制華爾街到阻斷金錢對政治的控制,從徹底的移民改革到真正的族裔平等,等等。
桑德斯的親民立場,同與華爾街維系密切關聯的希拉里形成了鮮明反差,一定程度上也收編了原本推舉馬薩諸塞州國會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參選的左派群體。更令人驚喜的是,由于政治生涯起步于1960年代,桑德斯依然保留著某些那個激蕩時代特有的批判精神與運動熱情,這種帶有“革命范兒”的競選足以令民主黨年輕選民找回那種澎湃的新鮮感。
面對自今年3月持續延燒的“郵件門”,本來已背負著“王朝政治”、“奧巴馬烙印”等負面資產的希拉里逐漸陷入了新的且深不可測的泥潭之中,民眾信任度也大打折扣。隨著希拉里選情變數的擴大,桑德斯這廂也就水漲船高。但冷眼看去,桑德斯顯然無法成為第二個奧巴馬:他長期抨擊金錢對政治的控制,因而競選經費主要來自小額捐款,缺乏大金主支持,可謂杯水車薪,難以長時間維持全國范圍內的競選活動;他目前的民意斬獲大部分得益于同樣存在于民主黨群體內的反主流、反建制的思潮影響,而他本人的政治立場過于極端與理想化,未必能令民主黨主體選民接納;更為關鍵的是,年長希拉里6歲的桑德斯根本跟不上民主黨新世代的視野與訴求,與奧巴馬的“變革魅力”可謂天壤之別。

桑德斯始終以與民主黨結盟的“獨立身份”示人。
正是由于對希拉里白宮前路的愈發擔憂以及對桑德斯可選性的強烈質疑,民主黨黨內才相繼傳出關于現任副總統拜登、甚至是卸任15年的前副總統戈爾有意出手的小道消息。由于2016年總統大選的揭幕戰即艾奧瓦初選被推遲到2月1日舉行,從而在理論上還是為拜登創造了一些閃轉騰挪的時間與空間。相比戈爾隱退太久而難以組織有效動員,在過去6年中繼續推高副總統權勢的拜登還是有實力放手一搏的。
當然,一旦拜登參選,民主黨初選天平的砝碼將落到曾表達期待“像里根那樣有一個老布什接盤”的奧巴馬手中。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拜登遵從早逝長子遺愿而宣布參選、并得到奧巴馬背書,也未必能搖身一變,充當起希拉里白宮路上的攔路猛虎。反而,希拉里甚至可以將奧巴馬政治遺產中的負面因素統統切割給副總統拜登。真若如此,TPP傷害的工會利益、伊朗核協議疏遠的猶太裔選民、美古復交得罪的古巴裔美國人,至少不會將賬全部算到希拉里頭上了。
不論是特朗普還是桑德斯,目前兩黨隱形初選中涌現出的“黑馬”現象,不約而同地流露出公眾對現行精英政治的不滿與反抗。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前后,美國政治運作顯然難以及時而高效地回應國家內政外交的諸多挑戰,甚至釀成了茶黨、占領華爾街等抗爭性社會運動。
即便社會運動暫且偃旗息鼓,其思潮依然縈繞于美國政治舞臺,并塑造著最近數次總統和國會選舉的基調。其中突出的傾向就是對在位政治圈內人的極度失望與不信任,希望選出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即圈外人來換取有效的變革。這一趨勢不但適用于茶黨由社會運動轉為政治勢力的蛻變及其推動的共和黨黨內的新陳代謝,也部分解釋了2008年奧巴馬擊敗希拉里的初選勝利。而今,這種浪潮并未因“變革者”奧巴馬的親歷親為而退卻,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比較而言,奮力重返白宮的共和黨黨內顯露出頗為濃烈的憤怒情緒,直接的表現就是對特朗普、卡森甚至菲奧莉娜等人的無厘頭追捧。
時至今日,美國兩黨政治中反傳統、反主流、反在任者以及反建制的趨勢,尚未釀成重大的政治失靈,即并未在總統等關鍵職位的選舉中遴選出毫無政治經驗、僅僅代表民粹潮流的候選人。不過,面對這種愈來愈近的可能性,美國政治精英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有必要開啟針對初選制度的新一輪改革。
自1972年民主黨首次采納總統初選以來的40多年中,兩黨各自都曾對各州初選時間的前置問題、黨內精英權重與基本盤參與的平衡問題進行了多次改革與調整。作為一種黨內民主的體現,如何有效保障民意表達,又將民意控制在理性向度內,始終是初選制度設計的最大難點。
首當其沖的兩個爭議是:一方面,在各州初選制度的門檻設置上,到底是采取關門方式從而確保所謂的政黨意識形態純潔性,還是采取開門方式進而讓參選人更多接受中間選民的考察?另一方面,在初選票數的分配上,到底有多少票分配給黨內精英以便糾偏民意,又有多少票要直接交給民意決定?在民粹主義甚囂塵上、媒體曝光度驅動民意支持度的今天,這些幾乎如影隨形的問題再次進入了矛盾焦點。如何避免選出一位最差的候選人,已是美國初選政治下一步躲不開的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