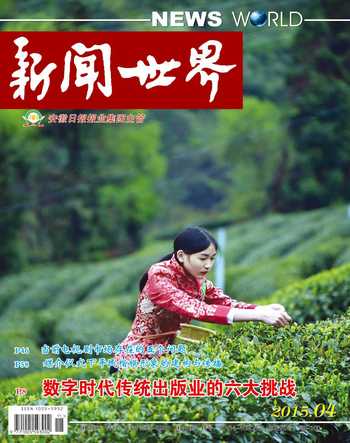電視節目低俗化傾向及其治理
張蕊
【摘要】近年來,隨著電視市場化的深入,電視節目越來越趨向于娛樂化、低俗化;為了提高收視率,吸引觀眾眼球,各電視臺通過各種手段吸引觀眾,在此過程中,電視節目的質量難以保證,逐漸呈現出快餐化特征,品位也逐漸降低。為了提高電視節目品位,加強行業自律和政府監管,提高受眾素養成為當務之急。
【關鍵詞】電視節目 低俗化 治理
近百年來,人類傳播技術有了前幾個世紀從未有過的巨大進步。從個體傳播來講,相聚數千公里的個人可以實現幾乎無障礙的同步通話;從大眾傳播技術來說更甚,當下真正可以做到足不出戶,目觀千里。然而,傳播技術的高速進步,是否帶來的都是進步與文明?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我們獲取信息的量越來越大,方式越來越便利,我們卻越來越容易被控制?
這個問題絕不是危言聳聽。赫胥黎曾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機械文明下的未來社會中,人的“人”性被機械剝奪殆盡,處于“幸福”狀態的人們以幾種種姓產生于工業化的育嬰房,接受種種安于現狀的教育,熱愛機械化的工作與生活方式。娛樂化的生活方式占據了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人們在毫無知識性的信息中娛樂至死。不可否認的是傳播技術的進步對于社會整合、凝聚群體有著不可否認的作用,但這種凝聚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無論是獨立的個體還是群體,一旦他們處于暗示影響的狀態之下,那么他們的思考功能就會徹底喪失。從一個念頭進入大腦到付諸行動,這期間沒有任何的時間間隙,幾乎是立即就變成了行動。群體所采取的行動與其思維邏輯產生了直接性的對立。”在現代傳播技術面前,人類看起來似乎是全知全能的,但又卻是空前脆弱的。
電視傳播技術的崛起,不僅對思想自由進行了蠶食與侵犯,也改變了我們日常的思考方式。邏輯與論辯顯得不合時宜,情感的宣泄才是正確的表達:“電視之所以是電視,最關鍵的一點是要能看,這就是為什么它的名字叫‘電視’的原因所在。人們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動感的畫面——成千上萬的圖片,稍縱即逝然而斑斕奪目。正是電視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要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追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電視節目的娛樂化傾向,迫使我們放棄思考,追求視覺的刺激與享受。加拿大著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認為,“電視是人的聽覺與視覺的同時延伸。”這一延伸帶來的結果卻是,我們的信息載體——大腦承受了比以前更大量的信息洪流,在短時間內無法理解的前提下,我們就會更加傾向于接受簡明扼要的、具有感官刺激的內容。電視藝術逐漸“以直接訴渚于人的感官和感性經驗為特點,注重感官享受、視聽感官的刺激甚至震撼。”我國的廣播電視亦不能例外。“電視大眾文化在物質話語僭越的當代中國社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大眾文化的商業性稀釋消解著高雅文化的藝術性,具體表現為那些具有大眾文化傾向的電視文本以商業目的的直接功利性替代著高雅文化的無功利性;以程式化、復制化、平面化、無深度感對抗著高雅文化的個性、獨創性、典型性;以情感策劃的虛假性拆解著高雅文化的情感判斷的真實性和深沉感;以享樂性、消遣性置換著高雅文化的啟蒙性、先驅性。”
近年來,廣電系統為凈化熒屏,抵制低俗之風下了大力氣。從某電視臺選秀節目《第一次心動》被叫停,《星氣象》的消失,到廣電總局一紙“限娛令”,足可見國家治理低俗化電視節目的決心。然而,低俗類節目卻屢禁不止。
就筆者看來,低俗化的節目主要表現在這樣三個方面:情色內容,挖掘隱私,挑戰道德。這幾個方面,無一不是滿足了人類最根本的欲望訴求。弗洛伊德認為,人格結構分為“本我、自我與超我”三個方面,其實“本我”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滿足的一切本能的驅動力,它的指向是“快樂原則”。由于電視信息量大,節奏快,觀眾會在觀看電視節目時本能地追求感官刺激。在《娛樂至死》中,尼爾·波茲曼警告美國人可能會成為沒有思想,只會接受娛樂的木偶,現在看來,這些警告同樣適用于國人。國內的許多娛樂類節目,都致力于滿足觀眾的“本我”本能,從而爭奪收視率。
1、情色內容
從“黃孩子”的時代開始,這一手法就一直長盛不衰。臺灣著名娛樂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小S,多次在節目內性騷擾男嘉賓,提問出位,表演大膽,滿足了受眾獵奇心理,從而帶來了高收視率,而高收視率又帶來了高廣告回報率,從而使得同類節目克隆迅速,傳播廣泛,帶來一股低俗之風。這種風氣傳到大陸,就出現了諸如《星氣象》這樣的低俗情色節目,主持人在曖昧的燈光下,穿著曖昧的服飾進行天氣預報。
2、挖掘隱私
挖掘明星隱私,極盡窺探之能事,讓明星當場尷尬現形,是一些娛樂節目的拿手好戲。國內“娛樂立臺”的某檔衛視的王牌節目,常常就邀請各路明星參與現場節目制作,在現場對其進行調侃、互動或是惡搞,從而迎合觀眾趣味,滿足觀眾探尋明星隱私的欲望。
3、挑戰道德
這是國內大部分低俗類節目的常用手法。發掘所謂的“丑聞”、“丑態”,像“芙蓉姐姐”之流,其貌不揚卻極其自戀,借助電視一躍成為“明星”,迅速走紅。同時,“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等也是這些電視節目的慣用伎倆,各式各樣的選秀類節目層出不窮,向底層民眾兜售著“一步登天”的浮躁思想。更有的節目,堂而皇之地宣揚拜金主義,金錢至上。這類節目,往往本著獵奇心理,突破道德底線,宣揚低俗道德追求,嚴重抵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給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帶來了負面影響。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低俗化節目出現,需要推行怎么樣的治理措施?筆者認為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電視臺,受眾與政府。從電視臺角度來說,中國電視的娛樂、低俗化與世界電視泛娛樂化、新型消費主義的盛行是分不開的。在新型的消費主義面前,電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受眾的眼球,在節目越來越同質化的今天,面對相對固化、還未形成成熟細分市場的受眾,沒有收視率就意味著沒有廠一告,而沒有廣告就宣告節目或是頻道的死亡。在現實利益驅動下,電視臺為了追求收視率用盡手段,什么節目能夠吸引最廠‘大的觀眾就推出什么節目,行業自律被束之高閣。在對大眾的盲目迎合之中,電視臺迷失了自我。
在這種情況下,受眾對娛樂化的追求繼續為電視的墮落推波助瀾。弗洛伊德認為,人所有本能的目標都是降低自身的緊張感,“享受與放松”是人類行為的內在驅動力。有需求才有市場,正是由于觀眾對娛樂化節目的無節制追求,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電視臺泛娛樂化的進程。
在電視臺與受眾共同進行著這場媒介盛宴的同時,政府卻沒能及時采取措施。監管部門面對電視節目低俗化,著重采取的是方針政策和相關行政手段,人治痕跡明顯。由于相關新聞管制法律的缺失,當問題出現時,有關部門無法可依,只能臨時“一刀切”,按下葫蘆浮起了瓢,各電視臺依舊鉆空子、打擦邊球,更有甚者,由于行政命令時效性、穩定性的缺失,往往會出現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情況,對低俗化節目的治理只能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
那么,面對這樣的情況,如何才能有效地對中國低俗電視有效地進行遏制呢?其實只要找準了原因,對癥下藥,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從低俗節目的制作方,即各個電視臺人手,規范電視臺經營,實行有管制的市場化和有限的商業化。電視臺管理者始終要明白,作為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電視臺的一舉一動時時刻刻在向千千萬萬個受眾傳遞著信息,改變著他們的思想,不恰當的節目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著消極的作用。在電視業中,經營性的部分可以推向市場,但必須保證公益性的內容份額,加大資金與技術、人才投入力度,發揮好電視的教育性作用。在當下消費主義盛行、電視庸俗化日趨嚴重的語境中,電視娛樂傳播只有不斷創新傳播策略,從追求形而下的快感邁向形而上的美感,致力打造富有品格內涵的綠色娛樂,才能開拓新的生存發展空間。
在受眾上層面,在筆者看來,只有通過教育來提高受眾思想文化水平,讓更多的人了解到長期沉迷于低俗化電視節目、單純追求感官娛樂的危害,并自發地參與到對電視節目的監督中來,防止低俗化節目的出現。同時,受眾品味提高,會自發追求相對更為高雅的娛樂形式,擠壓、限制低級趣味節目的市場,從財源上砍掉低俗節目的發展空間。
至于政府方,則應該盡快完善相關管理法規,出臺廣播電視新聞法,讓整治有法可依,提高管理權威性,同時保證管理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同時,監管部門應聯合調查公司,形成“社會美譽度”、“媒體公信度”等指標,與“市場占有率”、“收視份額”等形成平衡,同時確立好“低俗”電視節目的評判標準,當相關電視臺逾越了界限,就按照已有規定進行對應的處分。當然,健全這一監管體制也需要,一大公民受眾的響應與參與,政府應鼓勵公眾自發抵制不良媒體的低俗化行為,參與到監督與督促的程序中來。這樣才能真正對媒體形成全方位的壓力,促使其真正地做出改變。
總之,媒介技術的發展帶來的并不一定是理性與繁榮,也有可能是無序與混亂。一方面,我們受益于技術帶來的生活便利,我們的信息來源空前廣闊,我們對于知識的接觸也比前人要容易無數倍。在現代傳播技術的幫助下,我們足不出戶就能了解天下事,也可以將自己的觀點傳播給更多人。另一方面,我們卻有可能變成技術的奴隸。如何正確對待傳播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正反兩方面影響,更好地正確應用新傳播技術,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與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