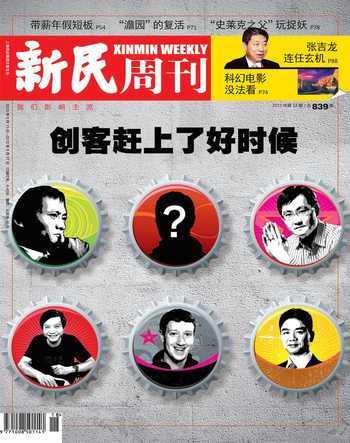轉(zhuǎn)行吧,記者?
王碧穎

2015年4月20日,美國紐約,《紐約時報》自由攝影師Daniel Berehulak因報道非洲埃博拉危機(jī)獲得專題攝影獎。
也許沒有什么比這更諷刺的了:這一邊,普利策大獎剛頒給了默默無聞的地方小報,媒體正驚嘆、祝賀;那一邊,卻曝出獲獎報道的主筆人,已因為薪資問題早早地離開了記者一行,轉(zhuǎn)投公關(guān)懷抱。
這也讓《普利策獲獎人因生活所迫轉(zhuǎn)行公關(guān)》這則新聞,代替本應(yīng)鼓舞人心的《2015年普利策獎公布》,一躍成為各大媒體頭條,畢竟,這實在讓太多記者扼腕嘆息——曾幾何時,記者這份職業(yè),成了“虛有榮譽(yù)、難以為生”的行當(dāng)?
小報獲大獎,記者卻轉(zhuǎn)行
相比同樣獲獎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來說,《每日微風(fēng)》真的是一份太不起眼的小報。在普利策獎公布之前,沒有人能預(yù)料到今年的地方新聞報道獎會被這份6.3萬發(fā)行量,只有7位記者的報紙拿下,即使他們的報道曾讓一名學(xué)區(qū)主管離職、或是已獲得過另一項新聞報道獎。
《每日微風(fēng)》編輯部坐落于加州托蘭斯,該報刊由前藥劑師S.D. Barkle創(chuàng)辦于1894年,于2006年成為洛杉磯新聞報刊集團(tuán)的一員。本次獲獎的報道是由記者Rob Kuznia、Rebecca Kimitch和Frank Suraci完成的關(guān)于當(dāng)?shù)馗咧袑W(xué)區(qū)腐敗現(xiàn)象的報道。這一場調(diào)查最初源于記者Rob Kuznia一條簡單的教育條線新聞,隨后在記者Rebecca Kimitch和編輯Frank Suraci的共同努力下,該報成功挖掘?qū)W區(qū)管理員的薪酬記錄,前后進(jìn)行50多篇追蹤報道,并最終迫使貪腐的學(xué)區(qū)主管離職。同時,該系列報道還促成加利福尼亞州政府重新修改相關(guān)法律以填補(bǔ)漏洞。
普利策委員會在評語中強(qiáng)調(diào)其為“發(fā)人深省的報紙網(wǎng)站”,它是小報,但而其在評審最后階段的競爭對手是《芝加哥論壇報》和《塔爾薩世界》。《每日微風(fēng)》的確讓人看到了地方報紙的力量與紙媒的影響力,但同時也讓大家看到了紙媒的落寞。
直到普利策新聞獎名單公布后,人們才發(fā)現(xiàn),發(fā)起并主導(dǎo)著這份金牌報道的記者Rob Kuznia早已在半年前離職,甚至離開了他從事多年的新聞行業(yè),轉(zhuǎn)而成為南加州大學(xué)大屠殺基金會的公關(guān)部門工作人員。而當(dāng)記者問起他原因時,居然是因為記者工作薪水太低,無法支付房租,導(dǎo)致Kuznia只好另謀他路。

獲得今年普利策獎的《每日微風(fēng)》記者Rob Kuznia。
根據(jù)Rob Kuznia的個人主頁及USC網(wǎng)站報道,他在2013年開始著手調(diào)查高中學(xué)區(qū)主管Jose Fernandez的貪污問題,并最終查證該主管年薪離譜地高達(dá)63.3萬美元。Kuznia的調(diào)查最終引起了FBI和洛杉磯政府對此事的調(diào)查取證,成功扳倒了這只“大老虎”。此外,這一系列報道,也讓Kuznia于3月17日贏得了Scripps Howard基金全國新聞獎,而這一獎項的獲得者向來都是普利策新聞獎的預(yù)備生。
Kuznia曾說,他從未期望能獲獎,畢竟他的競爭者們有許多一線大報,但是他相信他的獲獎會讓大家知道記者的力量。“這提醒著我社區(qū)報道的重要性,以及媒體對于社會的意義。如果沒有人看著這個社會,誰知道會發(fā)生什么呢?”
可即使是這樣,他依舊選擇了離開。在普利策新聞獎名單出來之后,便有美國記者已經(jīng)采訪了Kuznia,他承認(rèn)不再身為記者的心痛和懊悔,但他說薪資實在微薄,以致他無法支付在洛杉磯地區(qū)的房租,所以轉(zhuǎn)向了公關(guān)行業(yè)。獲得了新聞界最高榮譽(yù)的記者卻因為覺得紙媒行業(yè)太難維持生計而轉(zhuǎn)行,還有什么比這更打臉的?
美國記者究竟有多窮?
在大眾眼里,記者也許是風(fēng)光無限的,但Kuznia的例子卻告訴我們,就算寫再多有名的報道,記者也有可能養(yǎng)不活自己。
其實一直以來,記者都是美國各種人力資源和薪資調(diào)查公司發(fā)布的最差職業(yè)排行榜評為榜上嘉賓。根據(jù)薪酬調(diào)查公司payscale今年3月份做的最新發(fā)布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美國記者的中位收入僅3.8萬美元,而一名木匠的中位收入是4.1萬美元。而記者對未來收入的期望值也不高:5-10年工作經(jīng)驗的記者,期望的年薪中位數(shù)是4.2萬美元。payscale的數(shù)據(jù)也顯示,全美記者的年薪范圍大概在2.2萬美元到7萬美元之間。美國求職網(wǎng)站最近評出的2015年十大最差職業(yè)中,記者以工作任務(wù)重,壓力大,收入低,升遷前景不好,被列為十大最差工作之首,進(jìn)入十差之列的還有攝影記者和播音員,也跟新聞記者有關(guān)。
“美國新聞評論”網(wǎng)站上有一個統(tǒng)計,2013年全美新聞記者的平均薪酬是44360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10.7%。可是在這段時期內(nèi),全美平均薪酬增長28%,物價水平上漲了26.6%。也就是說,相對全社會的收入水平,記者的收入在大幅下降。可是,即使是這樣一個相對于其他行業(yè)已經(jīng)明顯偏低的數(shù)字,也引起了很多記者的抱怨,他們說自己賺的遠(yuǎn)遠(yuǎn)沒到這個數(shù)。這是因為,一小部分資深或者有名望的記者收入通常會比較高,拉高了平均水平。
就美國記者的薪資情況而言,不同地區(qū),記者的薪資也有所差別。比如在首都華盛頓,記者的薪酬比全國平均收入高35%,是全美記者最理想的去處。此外,紐約以高于全美27%位列第二,然后是舊金山和芝加哥。
可是Kuznia所在的這些不那么“中心”的地區(qū),記者的收入可能就不那么美麗了:據(jù)說月薪差不多只有2000多美元。2000多美元大概是怎樣的經(jīng)濟(jì)水平呢?舉例來說,在美國,一瓶礦泉水的售價是1美元,也就是說Kuznia的收入不吃不喝不繳稅也只夠買2000瓶礦泉水。換算到中國的物價,一瓶礦泉水售價人民幣1元,2000瓶礦泉水也就是2000元人民幣,農(nóng)民工都能輕松賺到。由此可見,單就薪水待遇方面,美國的記者們其實是很苦逼的。
其實相對來說,并不是所有記者都會像Kuznia這般窮困潦倒到付不起房租的,但是所有的記者都需要面對高強(qiáng)度的工作、不規(guī)律的生活作息以及潛在的外部威脅。
工作時間長,加班是家常便飯,常常需要通宵趕稿;需要耗費極大的腦力,神經(jīng)幾乎永遠(yuǎn)處于繃緊的狀態(tài);危險性很高,尤其是做調(diào)查的新聞記者,還可能面臨潛在報復(fù)。以Kuznia的獲獎報道來說,揪出一個貪官,并且要揪出其背后的勢力網(wǎng),除了要不斷潛入調(diào)查、還很有可能面對威逼利誘。再看2015年獲獎的這些新聞作品里,無論是《華盛頓郵報》的美國特勤局安全漏洞,還是《紐約時報》關(guān)于團(tuán)體如何動搖國會領(lǐng)導(dǎo)人和國家總檢察長的報道,抑或是《華爾街日報》對美國醫(yī)療提供商的數(shù)據(jù)揭秘,哪一個精彩報道的背后,都有著無法忽視的調(diào)查困難與危險。
其實記者的高危問題一直都是媒體主要的關(guān)注點,早前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hù)記者委員會”發(fā)布的2014年度報告就稱,過去一年全球至少有60名記者因公殉職。雖然該數(shù)據(jù)主要針對戰(zhàn)地記者的安全問題發(fā)出警示,但也從側(cè)面反映了記者這一職業(yè)的未知風(fēng)險。畢竟除了戰(zhàn)爭,還有地震、疫情等自然災(zāi)害,還有諸多機(jī)密數(shù)據(jù)、貪腐問題的揭露,因這些報道而受傷的記者,并不在少數(shù)。
更不用說,美國新聞行業(yè)對記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要求極高,寫出來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需要反復(fù)確認(rèn)、找到出處 ,還要找到其他人進(jìn)行反復(fù)求證,還有各種各樣規(guī)避利益沖突的嚴(yán)苛規(guī)定。可是所有這些辛苦,回報卻完全不成比例。同時,報道的真實性決定了在美國做記者是不可能有任何灰色收入的,哪怕收人家?guī)资涝紩兂沙舐剶嗨吐殬I(yè)前程。所以也難怪Kuznia轉(zhuǎn)向公關(guān)行業(yè),起碼人家穩(wěn)定、安全、收入高啊。
公關(guān),記者的最后出路?
由記者轉(zhuǎn)公關(guān),已經(jīng)并不是一件新鮮的事兒了。早在2013年,深藍(lán)財經(jīng)的專欄作家張威就曾盤點過那些從媒體轉(zhuǎn)行做公關(guān)的人。
當(dāng)時該文提到,21世紀(jì)經(jīng)濟(jì)報道的前記者中,徐繼業(yè)成了百度公關(guān)總監(jiān);朱平豆成為騰訊MIG電腦管家等業(yè)務(wù)公關(guān)市場負(fù)責(zé)人;許揚(yáng)帆進(jìn)了騰訊在線媒體事業(yè)部;顧建兵成了阿里巴巴集團(tuán)公關(guān)總監(jiān);顏喬成為天貓公關(guān)部負(fù)責(zé)人;楊磊成了阿里巴巴集團(tuán)總監(jiān);郎朗加入了騰訊電商。

2015年4月20日, 美國紐約,彭博社雇員與記者Zachary R. Mider一起慶祝彭博新聞社獲得了普利策新聞該年度的解釋性報道。
如果說,財經(jīng)記者的工作背景和人脈背景與企業(yè)有很多交集的話,越來越多的調(diào)查記者、時政記者轉(zhuǎn)行做公關(guān),的確體現(xiàn)了這個行業(yè)的沒落。
羊城晚報的張軍,進(jìn)了騰訊公司公關(guān)部;南方日報的陳亮,成了支付寶公關(guān)總監(jiān);南方周末的曹筠武去了聚美優(yōu)品;新京報的調(diào)查記者楊繼斌、黃玉浩也去了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做公關(guān)。新華社前記者寧樹勇1998年跳槽,先后在摩托羅拉(中國)、索尼愛立信(中國)、陶氏化學(xué)公司亞太區(qū)做公關(guān),2010年加入沃爾沃汽車集團(tuán)中國區(qū)。
而不僅僅是現(xiàn)役記者們的集體奔公關(guān),連預(yù)備役的新聞學(xué)子們也紛紛表示“心不在此”。據(jù)武漢晨報報道,一份由華中科技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廣東校友會發(fā)布的“30年來新聞傳播學(xué)專業(yè)畢業(yè)生職業(yè)狀況調(diào)查報告”顯示:媒體從業(yè)人員存在大量流失現(xiàn)象(從事與媒體相關(guān)工作的新聞畢業(yè)生僅53.6%)。同時,近年來從事公關(guān)和營銷的新聞學(xué)畢業(yè)生大量增加。
可是為什么是公關(guān)?因為對于寫不了程序、做不了美工、不會和客戶討價還價、空有文筆和諸多媒體資源的記者來說,公關(guān)是最省事、最能上手的選擇了。寫好宣傳軟文,找好投放資源、策劃一下媒體發(fā)布會、與老同事記者們搞好關(guān)系,不用日夜顛倒、風(fēng)雨兼程地跑采訪,不用起早貪黑、加班加點地排稿件,還能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資和有盼頭的加薪……這么一比較,公關(guān)比之記者,就個人生存、養(yǎng)家糊口方面有了太多的優(yōu)勢。
不過,習(xí)慣了揭露真相的記者們都放下身段成為八面玲瓏的公關(guān)么?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擔(dān)當(dāng)著公眾的“眼”與“喉”的記者們,都成為了公關(guān),還有誰為我們監(jiān)督社會、發(fā)掘黑暗、報道我們最需要的新聞呢?
就像愛情和面包的選擇題一樣,記者的榮譽(yù)與現(xiàn)實的生存,切切實實地擺在那里。對于Kuznia,他選擇了讓生活繼續(xù)。而我們其他仍在堅守著信念的記者們,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