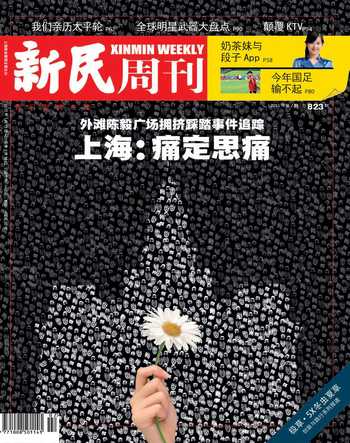記者殉職最多的年份
王碧穎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時局動蕩、地域沖突、小規模戰爭,“戰地記者”成了媒體報道中的熱詞,而與之相應的除了“戰爭”,還有“死亡”。東方衛視戰地記者就曾在一次采訪后寫下“如果沒有明天”感慨戰地采訪的危機重重,曾幾何時,記者已同“高危”畫上了等號?
全球至少60名記者死亡
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上周發布2014年度報告稱,過去一年全球至少有60名記者因公殉職,另有18名記者的死因仍在調查中,尚不清楚是否與工作有關。即使排除這部分不確定因素,過去三年仍是“有報告記錄以來記者殉職人數最多的年份”。其中中東、烏克蘭、阿富汗等地區的沖突使記者成為高危職業。
據統計,2014年幾乎一半的死亡事件發生在中東地區,敘利亞第三次“榮膺”最危險的國家,至少有17名記者在該國死亡。根據該委員會的統計,自2011年內戰爆發以來,在敘利亞遇難的記者人數達到了79人。
保護記者委員會自1992年開始進行對死亡記者人數的年度盤點,過去三年是死亡記者人數最多的年份。整體來看,2014年遇難的記者中有三分之一曾受到死亡威脅,40%的記者因蓄意謀殺殉職;近四分之一的遇難者為國際特派記者,該比例達到往年的2倍;此外,攝影記者死亡人數比文字記者多一倍。
由于局部沖突和戰爭不斷,記者在采訪重大事件時遭極端組織綁架并殺害的現象也越來越頻繁,記者已經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人群。2010年和2011年對記者威脅最大的地方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今年,敘利亞和伊拉克成為最危險的采訪地。
烏克蘭東部危機發生以后,已經有多名新聞記者在報道現場被打死,年僅30歲的意大利攝影記者安德烈·羅瑟勒與60歲的俄語翻譯安德雷·米羅諾夫在烏克蘭東部城市斯拉維揚斯克報道政府軍與親俄武裝猛烈交火時被打死。俄羅斯廣播電視公司VGTRK記者伊戈爾·科尼勒亞科在烏克蘭的盧甘斯克附近被烏克蘭軍隊殺害。俄羅斯“第一頻道”電視臺攝像師安納托雷·克蘭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遭烏克蘭政府軍火力擊中而不幸身亡。而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歷時50天的戰爭也至少造成包括法新社記者西蒙·加米勒和翻譯員阿里·舍哈達·阿布·阿法施在內的四名記者和三名媒體從業人士死亡。
而近年來美國的中東政策,也讓不少恐怖分子瞄準了美聯社記者下手。《華爾街日報》記者珀爾在報道巴基斯坦時被綁架,并于2002年被綁架者斬首。今年4月,美聯社資深女記者安佳·尼德林哈斯與搭檔乘車在阿富汗東部報道地區選舉時被一名阿富汗警察射殺,當場身亡。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先后在網上公布兩段斬首視頻,顯示其在敘利亞綁架并殺害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和史蒂芬·索特洛夫的畫面,以報復美國對該組織的空襲。
女記者危險更甚
在眾多國際記者中,還有一群特殊的存在——“戰地玫瑰”,從人們所熟知的閭丘露薇,到東方衛視記者袁文逸,國際媒體中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記者出現在戰事報道之中。相比她們的男性同時,女記者們在戰地中的安危似乎更讓人擔心。
2012年2月22日,著名的“獨眼女記者”瑪麗·科爾文和法國《巴黎競賽》雜志社攝影師雷米·奧奇力克在敘利亞霍姆斯的臨時媒體中心遭炮擊身亡。這位美國籍女記者是著名的戰地新聞記者,無數次地穿梭在生死線上,哪里有戰亂,哪里就會出現她的身影。2001年4月,科爾文在采訪斯里蘭卡內戰時被手榴彈炸傷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獨眼形象幾乎成為新聞界的一面招牌,傳奇事跡還曾被搬上熒屏。從斯里蘭卡逃生以后,她依然繼續著自己戰地報道的事業,動蕩不安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都被劃入了她的采訪版圖,2011年,科爾文還是最后一位采訪卡扎菲的記者。之后的8月20日,日本著名的“戰地美女記者”山本美香在敘利亞阿頗勒報道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沖突時中彈身亡。
2013年3月24日,年僅21歲的女記者阿卜杜卡迪爾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街頭遭人射殺。阿卜杜卡迪爾生前是索馬里一家電臺的記者,她的工作重點是關注人權,特別是婦女權益。她在工作完畢返回家中的路上遇害,兩名持槍男子瞄準她射擊,目擊現場的同事說,她被射中5槍。
同年11月2日,法國51歲的女記者吉斯蘭·杜邦和一名同事在馬里遭綁架后被處決。杜邦供職于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她和同事克洛德·威爾龍當天抵達馬里北部重鎮基達爾對當地的部族武裝領導人進行專訪,采訪結束后,兩人就遭到了四名槍手綁架,被強行帶上一輛黃色面包車駛向了沙漠地帶。當地安全部隊接到消息后迅速出動搜尋,但最終在沙漠中發現了兩位法國記者的尸體,尸體上布滿了彈孔。
而除了要面對戰火波及之外,女記者嗎還有更多的潛在危險——例如,女記者在到外國報道國際新聞事件時,甚至可能遭到被訪者或者熟人的性侵犯。據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稱,在埃及,女性新聞工作者在對示威抗議活動進行采訪報道時,最容易遭到性侵犯。而負責本地新聞采寫的女記者則可能出現家庭私生活遭到暴力威脅的情況,例如在某些案例中,敵對方通過損害女記者的名聲來達到降低其報道可信度的目的。
2012年2月11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39歲的女記者萊拉·洛根在埃及首都開羅解放廣場,采訪示威者歡呼總統穆巴拉克下臺時,遭到200名暴徒包圍,進行性侵犯和毆打長達20~30分鐘之久。
也許對于許多普通民眾而言,戰地記者的采訪并沒有那么危險:有軍方保護,當地人對記者敵意較小,并不是在交火集中地區……但真實真當如此?
“如果沒有經歷過戰爭,你會覺得我講的和戰爭電影里差不多。但你如果親身經歷,你會知道原來火箭彈在你200米外爆炸,它不僅帶來了巨響和硝煙,它還用它巨大的熱浪裹挾著撒哈拉沙漠里的沙子撲到你的臉上。你會知道,子彈從你頭頂上面劃過的時候,不僅是“嗖嗖”作響,還會振動著撕裂空氣。你會知道,即便你臥倒在地、即便身邊有你的同伴按住你的腦袋、即便你覺得自己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你也能體會什么叫做真正的無助,因為你不知道下一顆炮彈它會落在哪里。”當一名記者在采訪中突然被子彈擊中,當記者們被扣押著行走在荷槍實彈的武裝人群中,當記者被斬首的視屏被恐怖分子放出,也許人們才會驚懼。
也許我們永遠無法體會記者穿梭在戰場的不安與彷徨,但我們的確可以不僅僅做一個屏幕外的旁觀者。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呼吁,讓穿越著火線的記者們能得到更多的保護,愿新的一年,我們的“戰地英雄們”能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