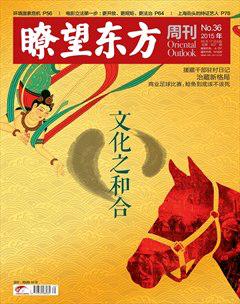電影立法第一步:更開放、更規矩、更法治
劉遠航

2015年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建國大業》編劇王興東提交提案建議,加快電影立法進程,嚴禁“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2015年9月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這意味著12年電影立法長跑到了最后的沖刺階段。
所謂“沖刺”,是因為按照法律程序,這部草案還須在2016年春天的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才能生效并進入實施階段。然而,目前的進展已讓許多電影人感覺到,電影立法的春天終于來了。
最早提議電影立法的老一代導演謝鐵驪已于兩個月前去世。當他在1983年的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發出這個聲音時也許沒有想到,實現這一目標要經過30多年努力。其間,中國電影業已從改革初期的“淺灘”駛入市場的“深水區”。
中國電影票房令人驚嘆地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10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296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36%。截至8月31日,2015年內地累計票房已超290億元。
伴隨著電影業成為中國文化產業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領域,國家的扶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大。據統計,2009年以來與電影相關的政策發布有15條左右,“對電影產業的重視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著名編劇汪海林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他認為,《電影產業促進法》肯定了電影產業對于國民經濟的重要戰略意義,也說明影視行業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如能審議通過,它將為快速發展的電影產業護航。
在目前的立法規劃中,已有8部文化法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網絡安全法》《公共圖書館法》《電影產業促進法》《著作權法(修改)》《文物保護法(修改)》以及《廣播電視傳輸保障立法》。
這被全國人大法工委相關負責人稱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電影第一法
雖然《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的具體細節還沒有正式公布,但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了解,它較2011年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的最大差異是對若干內容進行了更加明確的細化,而主要架構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不過,全國人大的立法審議,將決定它的最終面貌。
根據國務院法制辦此前公布的信息,該《征求意見稿》在起草和審查過程中,主要遵循了以下總體思路。
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便利各類市場主體、社會資本進入電影產業。對社會資本投資電影攝制等業務不作限制,減少行政審批。
通過采取財政、稅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激勵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個人從事電影活動。國家設立電影專項資金、基金,從事國產電影的創作、攝制、發行、放映等活動,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享受稅收優惠。
加強監督管理,規范市場秩序,促進電影市場健康發展。電影院不得偷漏瞞報票房收入;依法懲治侵犯與電影有關的知識產權的行為。
此外還包括加強電影公益服務,滿足農村地區居民、城鎮低收入居民、進城務工人員、未成年人等的基本文化需求。
此前受到關注的分級制等問題并未涉及。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曾參與過幾次立法討論。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不同于《電影法》,《電影產業促進法》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的,更多關注政府對電影行業的扶持,以及在公共事務方面應擔負的責任。對于審查制度等方面,暫時無法兼顧。

電影《烈日灼心》劇照
“盡管如此,這部草案仍然可以看做是文化立法的標志和突破口,具有積極的象征意義。”他說。
相比之下,編劇汪海林更關注這部法案對于電影創作者的意義,“比如對影視編劇的優惠政策、版權的保護”,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開放和保護
知識產權和影視文化傳媒專業律師王軍,在“瓊瑤訴于正抄襲案”中曾作為瓊瑤的代理律師幫助其最終勝訴。
王軍認為,這部草案與之前的電影管理條例相比,在具體細則上有著許多值得注意的變化。
首先是投資攝制主體更為開放。根據《征求意見稿》,外資企業在中國進行影視攝制,可能從不被允許變成合法,“當然,這還需要其他相關規定的變更或取消,比如《外商投資準入管理目錄》。”王軍告訴本刊記者。
其次是合拍片的問題。根據《征求意見稿》,境內企業如果對某部合拍片享有著作權,這部電影可以享有國產片待遇。“這對于中方在合拍項目中分享著作權以及IP的長期開發權益,有積極意義,國產企業的投資和版權等權益也有了一個法理上的保障。”他解釋說。
最后是對國產電影的政策保護問題。《征求意見稿》規定,電影院每年放映國產影片的時間不能少于總放映時間的三分之二。
雖然目前國產電影的票房以每年約30%的速度增長,但整體的制作水準還不穩定。
王軍認為,此項規定對國產電影的發展是利好,有助于避免其生存空間在未來市場進一步擴張之后受到擠壓。“以前這些并沒有成文的規定,立法之后,國產電影的發展有了基本保障。”
更規矩、更法治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聯系到王軍時,他正在韓國參加由韓國電影產業振興委員會(KOFIC)舉辦的電影產業論壇。
最近幾年,他一直擔任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總部駐北京代表處的法律顧問,目睹了韓國在促進電影產業方面的諸多措施——近年來韓國電影取得長足進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電影振興法》和韓國電影產業振興委員會的推動。
這是一個類似于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的機構,其前身是創建于1973年4月3日的電影促進會,1999年改名為電影振興委員會。同年,韓國《電影振興法》再次修訂,并確立了電影分級制。
王軍認為,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除了行政職能之外,“主要是為了推動產業振興”。
該機構會專門為在中國的韓國電影創作者提供法務和商務支持,比如在北京設立了韓國電影中心。
除此之外,它每年還會舉辦兩次電影項目交流論壇,這對于中韓政府簽署合拍協議推動極大。“近年來中韓合作的流行,與背后相關機構的作用分不開。”王軍說。
與韓國《電影振興法》不同,中國《電影促進法》并沒有提及分級制。但在《征求意見稿》中,將電影禁止的內容條例化、明晰化,這說明電影審查仍將是主管部門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汪海林認為,這并非表明管理機構對創作題材和內容加強了管制,而是把現在的行業規定用法律的形式強調了一遍。
“審查標準的不確定可能會導致不公平,甚至文藝腐敗。”汪海林認為,無論如何,“法制”取代“人治”是一種進步。
尹鴻認為,目前的任務是要用法律的形式確立審查的程序與合法性。從這個角度看,《電影產業促進法》以及未來相關法律的出臺或許更加值得期待。
娛樂法律師鄭厚哲注意到,《征求意見稿》對于偷漏瞞報票房收入有所涉及,但目前并未規定具體的處罰措施。
“其實這些問題以前就存在,立法只是重述、確認和補充。”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下,中國電影市場的繁榮與監管不力造成了秩序混亂,“還是要靠執法監管跟上”。
邁出第一步
1963年,當導演謝鐵驪拍攝《早春二月》的時候,他不會想到,那位在小鎮風波里難以脫身的主人公竟會成為自己后來命運的寫照。
在那樣一個法律常常缺席的年代,這樣的影片只能接受被批判的現實,成為“異類”。也正是幾十年的電影從業經驗,讓謝鐵驪體悟到出臺一部電影行業法律的必要性。
轉眼數十年過去,政治迷霧消散。愈加寬松的社會環境下,電影創作者卻不得不轉而與市場這只巨獸周旋。導演曹保平便經歷了這種語境劇變。
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改革開放以前,市場對于中國電影而言幾乎不存在。而現在,各種行業的人帶著各自的目的,紛紛進入電影市場,都想要分一杯羹。”
從編劇到導演,曹保平不斷在電影管理部門和市場之間周旋,并逐漸游刃有余,“我認真地做電影,也擁抱市場,同時也感受到了電影管理機構的不斷變化。”
最近,他執導的影片《烈日灼心》上映并獲得口碑票房雙豐收,這部電影看起來有一些“敏感內容”,很多觀眾驚訝,“廣電總局的尺度是不是放寬了”。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管理局局長在微信朋友圈發表的如下感言,或許能傳遞一些信號:“一部電影有好口碑,取得成功,不在于躲過了什么,繞過了什么。哪有那么多的不幸和僥幸?成功的理由只在于,你表達了有價值的東西,而你的表達又如此豐富、如此自洽。”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法律法規總數約3.8萬多件,文化法律法規1042件,占全部法律法規總量的2.7%。其中,文化法律僅占全部法律的1.7%。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文化法律僅有4件,分別是1982年的《文物保護法》、1987年的《檔案法》、1990年的《著作權法》和2011年《非物質文化遺產法》。
《法制日報》近期表示,在《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提速的同時,《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和《文化產業促進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第一檔項目。
三檔立法項目的區別是:第一檔是本屆內應提請審議的,第二檔是條件成熟時提請審議的,第三檔是繼續研究論證的。
《法制日報》說,“原來《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和《文化產業促進法》都是放在第三檔的”。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明確地提出“加快文化領域的立法”的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和《文化產業促進法》作為文化領域的基本法,“立法條件比較成熟,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很充分,它們的及時出臺將為我國公共文化發展和文化產業促進提供較完備的法制保障,而且作為上位法,也為其他相關法規規章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據。”
曹保平告訴本刊記者,電影創作者希望看到一個更加規范的市場,以及更加寬松的創作環境,《電影產業促進法》可能只是邁出了第一步。“這部草案肯定是積極的,具體如何落實,還需要走著看。”
“事情總是慢慢起變化,在此過程中,電影人仍需要冒雨趕路。”曹保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