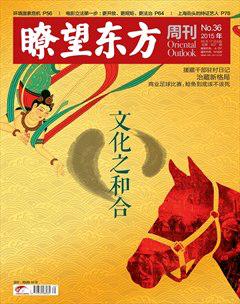商業(yè)足球比賽:鯰魚到底該不該死
高海博

2015年7月30日,上海, 皇家馬德里奪得2015年ICC 國際冠軍杯中國賽冠軍
“商業(yè)賽事到底是什么狀態(tài),大家在今年似乎終于明白了。”北京時博國際體育賽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時博國際)總經(jīng)理張震鵬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他口中的“商業(yè)賽事”,是指大牌歐洲足球俱樂部在夏季聯(lián)賽休賽期到中國進行的商業(yè)比賽。2015年7月到8月間,在中國至少舉行了11場此類比賽,一改多年來商業(yè)比賽遇冷的境況。
不過,如今的問題是,在這個剛剛發(fā)熱的市場上,“攪局的鯰魚”未來到底會怎樣。
小圈子里的博弈
從2014年10月開始,張震鵬明顯感受到歐洲賽事圈子的異常,“整個市場非常亂,主要來自國內(nèi)的需求。”
資本的涌動以及體育產(chǎn)業(yè)的利好政策,成為新一輪商業(yè)賽事的助推器。眾多賽事公司頻繁與歐洲豪門對接,尋求在國內(nèi)舉辦賽事的機會。同時,在2014年世界杯以及2016年歐洲杯間隙,2015年成為國外俱樂部到中國開拓市場的好時機。
于是,除了大牌俱樂部要價飛漲,中小俱樂部也會收到多份來自中國的邀請。
張震鵬說,歐洲足球俱樂部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小圈子里,具備賽事最終落地能力的公司不多。具體運行時,成熟的國內(nèi)公司更安全,但收益相對較低,新公司則兼有可觀收益和風(fēng)險。
2013年,西班牙巴塞羅那俱樂部在與一家中國公司談判時,收到了另一家新成立公司的更高報價,最終選擇了后者。
然而,新公司卻沒能按時支付定金,巴塞羅那俱樂部最終取消了這次中國行。

歐迅體育承辦了2015年夏天廣州恒大與拜仁慕尼黑的比賽。圖為2015年7月23日, 廣州恒大隊球員保利尼奧(左)與拜仁隊球員萊萬多夫斯基拼搶
“一場夏天進行的商業(yè)比賽,需要在前一年的年底敲定。窗口期很短,因為這直接關(guān)系到后續(xù)的招商與場地問題,錯過了就很難了。”張震鵬說。
中國足球商業(yè)比賽起伏不定。2003年皇家馬德里俱樂部中國行、2009年意大利冠軍杯以及2014年南美德比,成為眾多商業(yè)賽事中屈指可數(shù)的成功案例,除此之外多會遭到冷遇。
忽冷忽熱的市場也清洗了一部分操盤者。時博國際留下來的原因離不開其股東北京市國有資產(chǎn)經(jīng)營有限公司——擁有鳥巢、水立方等核心賽事場館,成為時博國際承辦商業(yè)賽事的重要籌碼。
但面對要價越來越高的歐洲俱樂部,張震鵬的選擇是:不談了。2014年底的兩個月“窗口期”,他沒有回復(fù)一封有關(guān)郵件。
他斷定,中國市場還無法承載起價格如此高、數(shù)量如此多的賽事,“一個夏天北京只能承載一場高水平賽事。”
事實上,在充分轉(zhuǎn)播歐洲足球賽事,商業(yè)比賽又屬于友誼賽、表演賽的情況下,其平均票價仍接近600元。
為了行業(yè)存在感
一個無法忽視的事實是,商業(yè)比賽很難做成一個固定的比賽。歐迅體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歐迅體育”)董事長朱曉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一支球隊在休賽期的比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如主教練、俱樂部主席的更換等,很難保證日程。
他舉例說,如果想主辦一場中德聯(lián)賽冠軍挑戰(zhàn)賽,需要說服兩國聯(lián)賽方、相關(guān)俱樂部,但每年的聯(lián)賽冠軍可能都會不同。
“國際冠軍杯”改變了這個局面。這項賽事本來由美國公司高價打造,并且形成了廣泛影響力,樂視體育于2015年將其引進中國,成為其中國承辦方。
“外方負(fù)責(zé)談定俱樂部,我們負(fù)責(zé)讓比賽落地。”樂視體育賽事運營中心副總裁邱志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樂視體育對接海外俱樂部的龐雜工作。
“國際冠軍杯”所進行的3場比賽分別選址廣州、深圳和上海。據(jù)樂視體育官方提供數(shù)據(jù),3場比賽總計約11.6萬名觀眾到現(xiàn)場觀戰(zhàn),在線直播覆蓋用戶超過1000萬。
邱志偉告訴本刊記者,雖然4年合同期只用了不到兩個月就簽約成功,但對于半年后就要開始的比賽,招商依然有些捉襟見肘。他坦承,盡管有西班牙皇家馬德里俱樂部這樣的一線豪門參賽,但盈利還需要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冠軍杯”的比賽并沒有在央視體育頻道進行播出,這對其影響力擴大是個損失。
歐迅體育承辦了2015年夏天廣州恒大與拜仁慕尼黑的比賽,也未能盈利。朱曉東說,“為了能形成影響力,也為了行業(yè)存在感,我們還是需要做商業(yè)比賽。”
歐迅體育是國內(nèi)首家在新三板上市的體育營銷公司,手握亞足聯(lián)版權(quán)、澳網(wǎng)等新媒體版權(quán)資源。朱曉東表示,做商業(yè)比賽更多是為了與歐洲豪門俱樂部的后續(xù)業(yè)務(wù)合作。
一場商業(yè)比賽的收益主要來自招商贊助、球票收入與電視及新媒體版權(quán)出售,支出則包括球隊出場費、場租、安保等。一線歐洲俱樂部的出場費在250萬歐元到300萬歐元。
在中國,由于播出平臺對于商業(yè)比賽的重要性——贊助和廣告會根據(jù)播出平臺的質(zhì)量進行投入,對其的爭奪也就成為商業(yè)比賽最大的博弈。
朱曉東告訴本刊記者,由于國內(nèi)電視臺的強勢角色,比賽主辦方幾乎沒有電視轉(zhuǎn)播收入,最主要的收入是門票,占70%左右。
國內(nèi)全國性的電視體育媒體只有央視體育頻道。雖然有樂視體育、PPTV體育、騰訊體育等新媒體平臺出現(xiàn),但對于廣告主并沒有充分的說服力。朱曉東告訴本刊記者,商業(yè)比賽的新媒體版權(quán)收入并不高,只有幾十萬元。
鯰魚終究是要死的
“廣告主看重的還是央視平臺。”一位從事商業(yè)賽事運營的資深人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想讓央視播出商業(yè)比賽,基本都要找中視體育來做電視信號,費用需要幾十萬。”中視體育是中央電視臺唯一的體育賽事商業(yè)運營機構(gòu)。
多位人士證實,體育圈里流傳著“有央視沒樂視”的說法。2015年央視直播的拜仁慕尼黑對廣州恒大的比賽等分別在PPTV、騰訊體育播出,樂視體育并未直播,而樂視主辦的超級冠軍杯也沒有出現(xiàn)在央視平臺上。
版權(quán)是問題的核心。樂視體育在2015年初購買了一系列獨家版權(quán),以“攪局者”的形象在體育版權(quán)市場上攻城略地。
曾有人說,“樂視就像是鯰魚,而鯰魚終究是要死的。”
樂視體育想要打造新的付費模式,勢必要對版權(quán)進行控制,這與現(xiàn)有的行業(yè)規(guī)則發(fā)生了沖突。樂視體育副總裁于航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版權(quán)價格抬升只是表象,一切都是為了建立最終的商業(yè)模式。”
“有央視沒樂視”更像是一場新舊媒體間的角力。數(shù)據(jù)顯示,央視體育頻道播放的恒大對拜仁的比賽共計有600萬人收看,而樂視體育平臺播出的3場“國際冠軍杯”比賽,覆蓋用戶近1000萬。
新媒體辦賽怎么玩
“我們希望有更多電視臺播出。”邱志偉說,第一年在國內(nèi)舉辦的“國際冠軍杯”,首先考慮的是能讓更多球迷看到。
“受關(guān)注的體育賽事本來就不多,加上版權(quán)都有周期,我們就像是租客,房子始終不是自己的。”邱志偉認(rèn)為,僅依靠購買版權(quán)不是長久之計,需要到上游去自創(chuàng)賽事IP,這也是樂視體育切入賽事運營的根本原因。
越來越多的新媒體公司開始切入賽事運營領(lǐng)域,“這是好事,能讓大家看看商業(yè)賽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雖如此說,張震鵬言語間仍流露出對新媒體介入賽事運營的懷疑。
朱曉東則明確表示,不看好媒體平臺承辦賽事。他認(rèn)為商業(yè)比賽是另外一個產(chǎn)業(yè)鏈,籌備一項賽事需要長期運營推廣,與媒體平臺本身的屬性“左右互搏”。
一般賽事在初期都需要藉由報紙、門戶網(wǎng)站、電視媒體推廣,通過長期培育讓更多觀眾了解。但倘若媒體平臺作為賽事的承辦方,其他競爭媒體則不會對其賽事進行報道與推廣。
樂視體育的國際冠軍杯就遇到了類似情況——一家門戶網(wǎng)站的體育記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國際冠軍杯”的消息不會出現(xiàn)在其供職的網(wǎng)站上。
“NBA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朱曉東介紹說,在NBA進入中國時都是免費給電視臺,通過媒體傳播提升影響力,逐漸帶來了電視轉(zhuǎn)播收入,“如果在早年就獨家賣給某一家網(wǎng)站,NBA的價格一定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高。”
“其他平臺不播,沒有贊助,IP就長不大。”朱曉東說,“頂級賽事是不會由媒體舉辦的。”
不止樂視,這是所有新媒體都面臨的問題。邱志偉的設(shè)想是,依靠賽事IP將樂視體育旗下的轉(zhuǎn)播、智能硬件、增值服務(wù)打通,賽事本身可以不賺錢,但能夠帶動其他業(yè)務(wù)的增長。
當(dāng)然,來自新平臺和老平臺的賽事主辦者,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共同面對。
2014年10月,國務(wù)院出臺的《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體育產(chǎn)業(yè)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表示,取消商業(yè)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但邱志偉告訴本刊記者,至少到目前“國際冠軍杯”的比賽審批相較之前一份文件都沒有少,依然需要上報中國足協(xié),通過地方體育局協(xié)調(diào)公安進行安保管理。
事實上,舉辦商業(yè)比賽依然需要強有力的政府關(guān)系。“如果沒有政府背書,公安部門會認(rèn)為商業(yè)公司無法承擔(dān)責(zé)任,即便合同里明確注明后果由公司承擔(dān)。”邱志偉說。
朱曉東則表示,雖然明確了 “取消賽事審批”,但舉辦比賽必然需要公安審批,而公安則需要其他部門的審批,“沒有任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