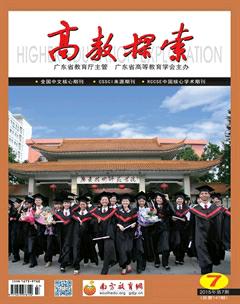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進路論略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學術史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科研究”(DAA100188)研究成果。
摘要:清末,教育學課程設置主要移植日本,教育學學科形成了幾門主干課程;到民初,教育學學科轉而模仿美國,并伴隨歐美教育科學化運動,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也呈現出科學化、專業化,學術性越來越強;到20世紀30年代,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走向中國化和本土化,大批鄉村教育課程和民眾教育課程出現,課程設置更加豐富,并形成了一定的學科課程體系。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進路就是教育學學科學術發展之路。
關鍵詞:近代中國;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從最初的幾門“教育學”主干課程到形成教育學學科課程體系,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模仿各國的課程設置到努力進行本土化的歷程。在某種意義上,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的演進理路,其實就是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學術發展之路。但目前學界對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的研究還不多見,本文試圖通過課程設置的演進理路窺探教育學學科的學術發展軌跡,從而揭示教育學學科近代化歷程。
一、羽翼初成:清末大學教育學學科主干課程設置
中國傳統的學術體制,主要研究經、史、子、集為主干的“四部”之學,在知識分類體系中并沒有教育學之說。清末,隨著西學東漸,教育及教育學之名開始導入中國。但最初國人對教育學并不認可,著名學者梁啟超都認為“教育”一門,“至其所以為教之道,則微言妙義,略具于《學記》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1]。可以想見,普通國人對教育學的態度了。但甲午一戰對清末朝野上下刺激太大,取法日本已成為時代指向。當時有識之士普遍認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2]而日本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師范教育,學習日本師范教育自然就要學習日本的“教育學”。
最早對日本教育學進行詳細介紹的是王國維,他翻譯了日本文學士立花銑三郎講述的《教育學》一書,該書在《教育世界》(第9-11號)連續刊出,其中小序中曾提到:“我國古代無固有之教育學,而西洋則學說甚多,頗難取舍。就中德國教育學,略近完全,故此講義,以德國教育家留額氏所著書為本。氏之教育學不但理論而已,于實際亦為有名者,則其決非在紙上空談,可比也。”[3]雖然,王國維指出了清末引進的日本教育學是借鑒德國的,但是當時部分人士認為,日本對西方教育學進行了吸收、消化和融合,中國直接學習日本可以少走彎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之后,從日本引進了大量有關教育學、教授學、教育史、學校管理等專著和教材導入中國。
在大學中最早設置教育學課程的是京師大學堂師范館。1903年《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師范館課程門目表為:“倫理第一,經學第二,教育學第三,習字第四,作文第五,算學第六,中、外史學第七,中、外輿地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學第十一,外國文第十二,圖畫第十三,體操第十四。”[4]《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把“教育學”明確定為第三,而且規定教育學課程分4年,按一定的順序開課:第一年教育宗旨,第二年教育之原理,第三年教育之原理及學校管理法,第四年實習。教育學課程的課時數占師范館總課時數的9.7%左右。但由于種種原因,該學制并未在全國實施。而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對教育學學科的課程設置作了更為細致而明確的規定,優級師范學堂的課程分為公共科、分類科和加習科。分類科為四大類:第一類系以中國文學、外國語為主,總共13科;第二類系以地理、歷史為主,共12科;第三類系以算學、物理學、化學為主,共12科;第四類系以植物、動物、礦物、生理學為主,共14科。在這四類學科中,教育、心理為必修課,“一概通習無異致”[5]。教育學課程具體有“教育理論及應用教育史”、“教育史”、“各科教授法”、“學校衛生”、“教授實事練習”、“教育法令”等。在各分類科課程中,教育學所占比重較大。以第一類中國文學、外國語為例,“第一學年開設普通心理學,每周2小時;第二學年開設教育理論和教育史每周4小時,應用心理學每周2小時;第三學年開設教育史、各科教授法、教育法令、學校衛生以及實事練習,每周8小時。教育和心理類課程3年總學時中所占比重為14.81%。”而對加習科,《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因分類科畢業后,自覺于管理法教授法其學力尚不足用,故自愿留學一年,擇有關教育之要端加習數門,更考求其精深之理法。”[6]加習課具體課程為十科:“一、人倫道德;二、教育學;三、教育制度;四、教育政令機關;五、美學;六、實驗心理學;七、學校衛生;八、專科教育;九、兒童研究;十、實驗心理學;但教育演習缺之亦可。修加習科者,于此諸科目所選修,須在五科以上,不得過少;畢業時須使呈出著述論說,以考驗其研究所得如何。”[7]由此可知,加習科已經開設了許多教育學專業的課程,而且這些課程為“教育之要端”,必須選五門課以上,還必須撰寫論文,以考查其研究水平。但加習科課程可學可不學,聽憑自選。
隨著學制的頒布,各優級師范學堂把課程分為公共科、分類科和加習科三種,教育學科已成為公共必修課程。如南京兩江師范學堂教育類課程有教育學、倫理學大要、學校管理法、教育史、教育令、實地演習等。教育及心理學第一年每周2小時,后兩年每周4小時[8];再如北洋女子師范學堂開辦之際,“學堂一方面設置了在當時較為完整的教育課程,如教育史、應用心理學、倫理學大意、教育原理、教授法等;另一方面在所有的科目中,都設置了該科目的學科教授法,如國文有國文教授法、理科有理科教授法,等等”[9]。
這一時期,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課程設置主要在優級師范學堂,借鑒了日本高等師范教育課程,主要有教育原理、教授法、學校管理法、教育史、學校衛生學、教育實習等課程;教育學科課程普遍受到重視,各學校已充分認識到“教育為師范學堂之主要科目,師范生不諳教育,即使通曉各科學,將來決不能應用,故部章所規定之教育科授課時間,萬不可減少”[10]。因此,在具體開設的課程中,教育學學科課程所占比率一般都比較高。第二,由于“日本新學界現最重心理學,為教育之基礎,故高等師范四學部中課程表第一年皆無教育一門,然未有無心理學者,蓋心理倫理諸科為教育之預科也”[11]。因此,清末各優級師范學堂也都設有心理學和倫理學課程。第三,各優級師范學堂雖然大都開設了所謂教育之要端的“加習科”,科目多至10余門,但實際上并未真正執行。
二、雨后春筍:民初教育學學科科學化課程涌現
民初,新教育運動在歐美各國開展得如火如荼,姜琦在《現代西洋教育史》一書中認為:20世紀初以后,西方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傾向是由“教育學”向“教育科學”的轉化。[12]確實,當時教育科學化已經成為世界最強音,許多學者對此都進行過表述。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貝爾納評價道:“過去的教育學只能是哲學的教育學,而不是科學的教育學。教育學具有科學氣味并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是由于智力測驗引進到教育學中了。”[13]而美國的霍爾、桑代克、杜威、吉特、孟祿等人進一步把教育科學運動推向了高潮。例如,桑代克曾說:“教育科學,當它在發展的時候,就像其他科學那樣,有賴于對教育機構的影響作直接觀察和實驗,并且有賴于以定量的精確性研究出來和加以描述的方法。”[14]
世界教育學科學化運動對民初中國的教育學學科的科學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大批留美學生的回國,他們高舉科學大旗,大力提倡科學。蔣夢麟曾在《高等學術為教育學之基礎》一文中指出:“自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以來,西洋學術,莫不以科學方法為基礎;即形而上學,亦以此為利器。至今日一切學問,不能與科學脫離關系;教育學亦然。故今日之教育,科學的教育也。舍科學的方法而言教育,是鑿空也,是幻想也。幻想鑿空,不得謂二十世紀之學術。”[15]與此同時,杜威、麥柯爾、推士、克伯屈等人先后來到中國,把教育“科學化”運動推向了中國教育研究的各個方面。陳友松曾客觀地評價道:“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的領導下,我國聘請了杜威、麥柯爾、推士、克伯屈等大師講學,教育學才開始從傳統因襲的氛圍中超脫出來。實驗、統計、調查,成了時髦的名辭。”[16]隨著多種科學方法的應用,新興的課程設置不斷涌現。例如,教育統計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從描述統計發展到推斷統計,教育學學科遂出現了教育統計、教育調查、教育測量、教育實驗等課程;再如,隨著生物學的發展,部分教育學者開始關注遺傳、環境對人類生長和發育等多方面的影響,于是教育學學科又出現了有關環境和遺傳的課程。
隨著科學化運動的推進,民初各大學教育學學科的課程設置科學化、豐富化,一大批新興課程在各大學涌現。如南京高等師范教育專修科的課程設置,據1919年秋入學的教育學科學生章柳泉回憶,“我入學的第一學期,就有一門介紹科學常識的課,陶老師在這門課中給我們講遺傳學,從達爾文到德弗里斯,特別是孟得爾的雜交試驗。第二年我們就學‘科學的發展史(張子高老師教的),生物學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課程(秉志老師教的)。心理學是教育學的重要科學基礎,我們學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實驗心理學是重點,共學兩年,做過很多實驗,還開設‘心理學史課程(都是陸志韋老師教的)。此外還有‘教育統計學(陶老師教的),‘測驗之編制與應用(是以麥柯爾等人為主任教的)”[17]。教育學科大量科學課程的開設,使南高師成為當時中國科學教育的重鎮。再如1920年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經北京政府教育部核準開辦教育研究科,招收高師和專門學校畢業生及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開設的課程達24門之多,其中就設置有大量的科學化課程,具體為“哲學、美學、心理學、教育學、教育史、教授法原理、生物學、社會學、教育統計、教育行政、心理測量、社會問題、道德哲學、各國教育制度、教育調查法等”[18]。除了高等師范學校設置教育學學科課程,隨著科學化運動的展開,教育學術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在一般的綜合性大學也開設教育學課程。如1917年,暨南大學設置了教育學課程;1922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課程分為三組:即哲學、教育與心理。1924年,教育學系成立,必修科目為教育哲學、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史、科學概論、論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教育史、心理學、教育與兒童心理學、普通教學法、教育行政、學校管理、教育測驗及統計、實習。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出現了新的特點:第一,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除了幾門主要的課程如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學、教育社會學等外,民初還出現了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實驗教育學等課程設置,教育學學科不斷走向科學化。第二,隨著教育學課程設置的科學化,教育學學科的專業性和學術性也越來越強,學科地位也越來越高,教育學學科課程不僅在高等師范,而且在一般的綜合性大學也開始設置,教育學學科地位逐漸在各大學得到認可。第三,這一時期的課程設置主要模仿美國,與國際接軌也非常密切,各國出現的教育學學科課程,在中國各大學都可找到相應的課程設置。
三、走向本土:教育學學科鄉土課程大量增設
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一開始就借鑒國外,從移植日本到模仿歐美,適合本土的課程設置并不鮮明。雖然從一開始引進就有中國化、本土化的聲音,但一直引進的聲音占了主旋律。到20世紀30年代左右,本土化開始壓過引進的聲音,占了主導地位。
這時,正如近代國人所描述的:“各大學教育科系的教授們,雖然有不少的人在做研究,辦學的人也在注意當時社會研究教育的空氣,確是欣欣向榮;但大部分力量用于介紹美國教育思想和方法”,“充其量做的是搬運和驗證的工作”。[19]開始有一部分學者發出本土化的呼喚,如有學者曾提到“現在中國教育界還有一些的覺悟,覺悟的是:中國的教育必須是中國的,必須是中國教育者自己研究出來的,深閉固柜固然是不可能的,東抄西襲也是徒勞而無功。所以現在國內研究教育的人,尤其是在歐美日本習過教育的留學生,他們研究教育的工作漸漸踏實了,他們高瞻遠矚的眼光也漸漸回顧到本國民族性的優點和劣點,以及本國社會一般民眾的實況和需要了”[20]。
隨著教育學科本土化的呼聲,教育學學科課程本土化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如張栗原明確指出,“我們的教育哲學應該是中國的教育哲學,從我們民族出發的教育哲學”[21];雷通群指出,“使教育社會學成為中國化”[22];羅廷光對教育行政提出要求,指出:“我們不能把國外的教育制度移植過來,同樣也不可把外國教育行政書籍直接拿來應用……我們要做開創的工作,要本著遠到的目光,深邃的見解,認清本國教育行政的問題,運用科學的方法和專門的智能以解答,更當就教育行政之‘學與‘術本身做進一步研究,以樹立本門學術之深厚的基礎。”[23]
為了使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進一步符合中國教育本土,一些教育學科研究者和教師開始直面中國教育現實,參加了鄉村教育運動和民眾教育運動,設置有定縣平民教育實驗、鄒平鄉村建設實驗、無錫民眾教育實驗、華西實驗區鄉村建設實驗等。在此基礎上,具有本土特色的鄉土教材出現,鄉土課程開始廣泛設置。如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育學科設置了民眾教育史、民眾教育原理、民眾教育學、成人學習心理、比較成人教育、民眾教育實施法、民眾教育行政、民眾教育教材教法、民眾教育測量與統計、民眾教育視導等課程;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育學科設立了成人學習心理、國民教育、鄉村教育、補習教育、推廣教育、民眾教育館、鄉村建設、社教教材等課程。當時甚至連教會大學都參與到鄉村建設運動之中,紛紛設置了農村實驗區,開始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如燕京大學教育系設置了鄉村教育專業,開設的主要課程涉及面較廣,有“鄉村教育”、“教育經費”、“教育社會學”、“定縣的實驗”、“農村經濟學”、“農村合作社”、“農村運動比較”、“地方政府”、“農村問題討論”等。
盡管鄉村教育和民眾教育的課程設置隨著鄉村教育運動和民眾教育運動的衰落而消亡,但20世紀30年代以后,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形成了一種鮮明的特色:第一,隨著大批鄉村教育和民眾教育課程的設置,課程本土化和實踐性越來越強,這也意味著教育學學科已從模仿走向中國化、從理論走向實踐、從外爍轉向內生。第二,課程設置越來越豐富。各校又結合地方和學校的特點,設置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課程,如北平師范大學教育學課程1932年就已達到50門,西南聯大教育學系1939年課程設置達49門,同年,教育部部頒課程也達到46門。可見,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已相當豐富。第三,隨著課程設置的增加和豐富,許多學者對課程設置的形成進行歸納整理,并形成了一定的學科課程體系。如有的學者以研究對象為標準進行分類;有的學者以研究方法為對象進行分類;有的學者從教育活動形態的角度出發對教育學科進行分類;等等。
總之,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經過了清末、民初到民國三十年代,教育學學科課程設置從最初的幾門主干課程,到大量科學化課程的設置,再到本土化課程的追求,課程設置越來越完善。當然,在課程設置過程中,問題還是存在的,如課程設置缺乏統一的標準、課程設置與培養目標不完全契合、課程設置內容重復等。[24]但整體來說,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學科課程在國際化、本土化的過程中,課程結構明確,課程體系已基本成形,課程設置之路就是教育學學科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林志鈞.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 北京:中華書局,1989:37.
[2] 陳學恂. 中國近代教育文選[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09.
[3][日]立花銑三郎. 教育學[J].王國維,譯. 教育世界,1901(9).
[4][10][11]實業教育 師范教育[M]//璩鑫圭等.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561,612,717.
[5][6][7]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684,683,692.
[8]蘇云峰. 三(兩)江師范學堂[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47.
[9]崔運武. 中國師范教育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51.
[12] 姜琦. 現代西洋教育史[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447.
[13][英]貝爾納. 歷史上的科學[M]. 伍況甫等,譯.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41.
[14]康乃爾. 20世紀世界教育史(英文版)[M].1980:100.
[15]蔣夢麟.高等學術為教育學之基礎[J]. 教育雜志,1918(1):13-18.
[16]陳友松. 五十年來美國之教育科學運動的貢獻[J]. 教育雜志,1940(9):11-14.
[17]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 紀念陶行知[M].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32-333.
[18]北京師范大學校史編寫組. 北京師范大學校史(1902-1982)[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62-64.
[19]羅廷光. 教育科學研究大綱[M]. 上海:中華書局,1931.
[20] 劉天予. 我們應當自反的一個重要問題[J]. 現代教育,1929(1):26.
[21] 張栗原. 教育哲學[M]. 上海:三聯書店,1949:72.
[22]雷通群. 教育社會學[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3] 羅廷光. 教育行政(上冊)[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
[24]項建英. 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科研究[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6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