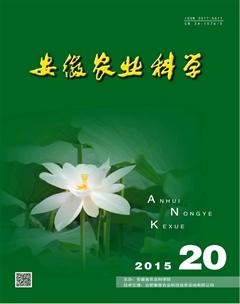我國(guó)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的影響因素研究
馮穎 黨夏寧


摘要 根據(jù)1978~2013年我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建立了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的影響因素雙對(duì)數(shù)模型。結(jié)果表明,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對(duì)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有著顯著的負(fù)影響;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以及時(shí)間參數(shù)對(duì)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為全面提高農(nóng)民收入,應(yīng)重視提高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效率,適度集中零散耕地尤其是農(nóng)村大量的撂荒耕地,走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有序轉(zhuǎn)移農(nóng)村剩余勞動(dòng)力。
關(guān)鍵詞 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影響因素;雙對(duì)數(shù)模型
中圖分類號(hào) S-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0517-6611(2015)20-305-03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model between farmers income and its impacting factors with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19782013 of China.It could be found, two factors of fiscal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first industry employment population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ed on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on the other side, four factors of crop planting area, chemical fertilizer amou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ice index and time parameters have an obvious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To improve farmers income, the efficient of fiscal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reasonable concentrating production way in rural especially a large number of abandoned plough, and a new urbanization way to orderly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Key words Farmers' income; Growth; Impacting factors; Double logarithmic model
繼1982~1986年連續(xù)5年中央一號(hào)文件以“三農(nóng)”問題為主題后,2004~2015年又連續(xù)12年的中央一號(hào)文件聚焦“三農(nóng)”,可見“三農(nóng)”問題在我國(guó)社會(huì)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而農(nóng)民增收問題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1978~2013年,我國(guó)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了約66倍,呈現(xiàn)出持續(xù)增長(zhǎng)的趨勢(shì),但仍然低于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增速,城鄉(xiāng)差距較大,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平均為2.9,農(nóng)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shù)也一直高于城鎮(zhèn)。農(nóng)民收入問題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huì)問題,降低了農(nóng)民作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主體的積極性,加劇了糧食安全隱患,制約了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不利于全社會(huì)的穩(wěn)定和諧發(fā)展,農(nóng)民增收已成為我國(guó)各級(jí)政府農(nóng)業(yè)政策的首要目標(biāo)。
促進(jìn)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必須要分析農(nóng)民收入的影響因素,從而設(shè)計(jì)切實(shí)有效的政策路徑。王紅蕾研究發(fā)現(xiàn)非農(nóng)勞動(dòng)力占鄉(xiāng)村勞動(dòng)力的比重對(duì)農(nóng)民增收的影響最為顯著[1];蔡飛鳳等運(yùn)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從農(nóng)民收入4個(gè)構(gòu)成部分上選取了9個(gè)相關(guān)要素進(jìn)行分析[2];楊申通過主成分分析確定農(nóng)民收入影響的主要因素[3];楊靜等采用逐步回歸對(duì)長(zhǎng)春市農(nóng)民經(jīng)營(yíng)性及工資性收入的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分析[4];呂玲麗等對(duì)廣西農(nóng)民收入的影響因素及增收貢獻(xiàn)進(jìn)行了分析測(cè)算[5];姚麗虹等分析了影響廣東農(nóng)民純收入的因素[6];陳艷采用通徑分析法和生產(chǎn)函數(shù)法分別測(cè)算了農(nóng)民農(nóng)業(yè)收入及非農(nóng)收入的影響因素及程度[7];熊吉峰運(yùn)用PLS回歸方法,對(duì)影響農(nóng)民增收的12個(gè)因素進(jìn)行了分析[8];此外,羅東等[9]、吳振鵬等[10]、杜玉紅等[11]、蘇月霞等[12]就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對(duì)農(nóng)民收入的影響進(jìn)行了分析。
現(xiàn)實(shí)中,不同因素會(huì)引起農(nóng)民總收入中不同組成部分發(fā)生變化,致使農(nóng)民各收入組成部分之間呈現(xiàn)此消彼長(zhǎng)的關(guān)系,要研究它們引起農(nóng)民總收入的變化情況,需要全面考慮農(nóng)民增收的影響因素進(jìn)行綜合分析,從而設(shè)計(jì)有效的農(nóng)民增收政策路徑。綜上所述,筆者根據(jù)1978~2013年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建立全面的農(nóng)民收入水平及其影響因素之間的計(jì)量模型,對(duì)影響農(nóng)民收入水平的因素進(jìn)行綜合研究,以探尋有效的農(nóng)民增收路徑。
1 指標(biāo)選取、數(shù)據(jù)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指標(biāo)選取
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按收入來源的性質(zhì),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jīng)營(yíng)純收入、財(cái)產(chǎn)性收入和轉(zhuǎn)移性收入。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主要是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得;工資性收入是從事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獲得的收入;財(cái)產(chǎn)性收入主要來源于家庭擁有的動(dòng)產(chǎn)和不動(dòng)產(chǎn)所獲得的收入;轉(zhuǎn)移性收入則與農(nóng)業(yè)補(bǔ)貼等相關(guān)。
因此,以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分析其影響因素可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得取決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投入要素,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對(duì)改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條件、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水平有重大作用;化肥的施用可增強(qiáng)土壤肥力,適度施肥對(duì)提高糧食產(chǎn)量有重要的作用;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直接影響農(nóng)業(yè)收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直接影響農(nóng)民經(jīng)營(yíng)投入。以上4個(gè)要素均對(duì)農(nóng)民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產(chǎn)生重大影響,因而選取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化肥施用量、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作為解釋變量。勞動(dòng)力作為最基本的人力投入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主體,不僅影響農(nóng)民的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剩余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還會(huì)影響農(nóng)民的工資性收入;城鎮(zhèn)化率可以間接測(cè)度其吸納農(nóng)村剩余勞動(dòng)力的能力,從而也可以間接標(biāo)度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員的市場(chǎng)需求強(qiáng)度。因而,選取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城鎮(zhèn)化率、第一產(chǎn)業(yè)占GDP比重作為解釋變量。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政策與農(nóng)民的工資性收入、家庭經(jīng)營(yíng)收入與轉(zhuǎn)移性收入均具有密切的關(guān)系。我國(guó)政府一向重視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近年來也出臺(tái)了一系列措施,不斷加大財(cái)政支農(nóng)力度,因此將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納入模型。將農(nóng)村居民人均居住住房面積作為衡量農(nóng)民財(cái)產(chǎn)性收入的指標(biāo)納入到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影響因素模型。
1.2 數(shù)據(jù)來源
根據(jù)以上分析,采用上述指標(biāo)1978~2013年的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進(jìn)行計(jì)量分析,其中第一產(chǎn)業(yè)占GDP比重、農(nóng)村居民人均居住房面積來源于《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其他數(shù)據(jù)來自歷年《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年鑒》以及《中國(guó)農(nóng)村統(tǒng)計(jì)年鑒》。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剔除過通貨膨脹因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是以1978年為基期的指數(shù),以保持?jǐn)?shù)據(jù)的一致和穩(wěn)定。所收集到的相關(guān)變量數(shù)據(jù)見表1。
1.3 模型設(shè)定
根據(jù)已有文獻(xiàn),采用傳統(tǒng)的雙對(duì)數(shù)形式來設(shè)定模型,對(duì)變量取對(duì)數(shù)不僅可以做到無量綱化,減少異方差,還具有明確的經(jīng)濟(jì)含義,即解釋變量變化1個(gè)百分點(diǎn),導(dǎo)致被解釋變量變化的百分位數(shù)。模型表示如下:
式中,α為各投入要素的產(chǎn)出彈性系數(shù);μ為隨機(jī)項(xiàng);t為時(shí)間;Y表示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X1為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X2為農(nóng)業(yè)機(jī)械動(dòng)力;X3為化肥施用量;X4為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X5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X6為農(nóng)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X7為城鎮(zhèn)化率;X8為第一產(chǎn)業(yè)占GDP比重;X9為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
2 結(jié)果與分析
由于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可能具有自相關(guān),在簡(jiǎn)單的OLS估計(jì)下可能會(huì)引起偽回歸問題,必須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相關(guān)檢驗(yàn)。該研究采用小樣本模型下的杜賓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該研究所采取數(shù)據(jù)不存在一階序列相關(guān)。
采用Stata12.0對(duì)模型進(jìn)行估計(jì),結(jié)果見表3。
由表3可知,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X1)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影響顯著,但呈現(xiàn)負(fù)方向影響。意味著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并不是農(nóng)民增收的主要原因,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每提高1%,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將會(huì)降低0.26個(gè)百分點(diǎn)。可能的解釋是,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規(guī)模已經(jīng)超過一定的拐點(diǎn),呈現(xiàn)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所支持的農(nóng)業(yè)款項(xiàng)并沒有產(chǎn)生預(yù)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激勵(lì)作用。比如說,農(nóng)戶生產(chǎn)努力程度是為了達(dá)到一個(gè)目標(biāo)產(chǎn)值,但過高的補(bǔ)貼使得較低的產(chǎn)出就能達(dá)到該目標(biāo)。可見,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改善農(nóng)業(yè)收入水平的作用,不在于一味擴(kuò)大規(guī)模提高絕對(duì)金額,而在于提高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的效率。這樣,既可以提高整體財(cái)政支出效率,更能將其中的農(nóng)業(yè)支出作用發(fā)揮到最佳。
化肥施用量(X3)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呈現(xiàn)顯著的正向影響,即化肥施用量每提高1%,則農(nóng)民人均收入將會(huì)增長(zhǎng)0.92個(gè)百分點(diǎn)。表明化肥的使用極大地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產(chǎn)量,對(duì)農(nóng)民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的增長(zhǎng)起到促進(jìn)作用。但在進(jìn)一步的研究中要注意,化肥施用量的最佳狀態(tài),過度使用化肥不僅對(duì)農(nóng)民增收無益,還會(huì)帶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危害。
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X4)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呈現(xiàn)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來說,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每擴(kuò)大1%,農(nóng)民人均收入將會(huì)增長(zhǎng)2.69個(gè)百分點(diǎn)。農(nóng)民的直接經(jīng)營(yíng)性收入與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有極大的關(guān)系,2013年中央一號(hào)文件提出,鼓勵(lì)和支持承包土地向?qū)I(yè)大戶、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民合作社流轉(zhuǎn)。隨著一系列針對(duì)農(nóng)民工進(jìn)城務(wù)工及其子女就學(xué)問題的政策出臺(tái),大量農(nóng)民工選擇外出務(wù)工,致使農(nóng)村大片耕地撂荒,將小規(guī)模零散不連片以及撂荒土地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集中、整合,有利于形成農(nóng)業(yè)規(guī)模化、機(jī)械化、集約化,進(jìn)而促進(jìn)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且能保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可持續(xù)性,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X5)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呈現(xiàn)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來說,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每提高1%,則農(nóng)民人均收入提高0.47個(gè)百分點(diǎn)。近年來,我國(guó)農(nóng)村普遍出現(xiàn)了“增產(chǎn)不增收”現(xiàn)象,通常來說,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的上漲,會(huì)帶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成本的增加,降低農(nóng)民收入。但從另一個(gè)角度來說,農(nóng)資價(jià)格上漲,農(nóng)民外出務(wù)工等工資性收入與進(jìn)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收益差距增大,使得農(nóng)民種植的積極性降低,理性農(nóng)民較多的選擇外出務(wù)工,從而最終增加了農(nóng)民總純收入。但必須引起重視的是,農(nóng)資價(jià)格的上漲必然會(huì)影響農(nóng)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從一定程度上削弱國(guó)家支農(nóng)的政策效果。因此,梳理農(nóng)資價(jià)格、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與農(nóng)戶收入之間存在的較為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對(duì)農(nóng)資價(jià)格進(jìn)行監(jiān)控,維護(hù)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保證糧食安全十分重要。
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X8)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增長(zhǎng)呈現(xiàn)顯著的負(fù)向影響,具體來說,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每提高1%,農(nóng)民人均收入將會(huì)降低0.91個(gè)百分點(diǎn),意味著第一產(chǎn)業(yè)勞動(dòng)力飽和且過剩,需要推進(jìn)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dòng)力的轉(zhuǎn)移。這與現(xiàn)實(shí)相符合,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會(huì)帶來農(nóng)民收入的增長(zhǎng),主要在于促進(jìn)其工資性收入提高。未來應(yīng)加大對(duì)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的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有序轉(zhuǎn)移剩余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
時(shí)間參數(shù)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增長(zhǎng)呈現(xiàn)顯著的正向影響,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農(nóng)民收入在逐步改善。
其他指標(biāo)如農(nóng)業(yè)機(jī)械總動(dòng)力(X2)、農(nóng)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X6)、城鎮(zhèn)化率(%)以及第一產(chǎn)業(yè)占GDP比重(X8)對(duì)農(nóng)民人均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承包責(zé)任下,我國(guó)耕地人均僅0.1 hm2,農(nóng)戶戶均土地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約0.6 hm2,遠(yuǎn)遠(yuǎn)達(dá)不到農(nóng)業(yè)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的門檻,而農(nóng)業(yè)機(jī)械的推廣較適用于集中大片平整連片的土地,小規(guī)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下不利于使用農(nóng)業(yè)機(jī)械,農(nóng)業(yè)機(jī)械對(duì)現(xiàn)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帶來的規(guī)模效益未能凸顯;農(nóng)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代表了農(nóng)民擁有的不動(dòng)產(chǎn)情況,在模型中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農(nóng)村住房較少用于租賃流轉(zhuǎn),即使賃租租金也非常低,且農(nóng)村住房的市場(chǎng)價(jià)值遠(yuǎn)遠(yuǎn)低于城市住房市場(chǎng)價(jià)值,未能對(duì)農(nóng)民的收入產(chǎn)生明顯的促進(jìn)作用;1978~2013年,我國(guó)城市數(shù)量從193個(gè)增加到658個(gè),建制鎮(zhèn)數(shù)量從2 173個(gè)增加到20 113個(gè)。京津冀、長(zhǎng)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大城市群,以2.8%的國(guó)土面積集聚了18%的人口,創(chuàng)造了36%的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目前,我國(guó)東部地區(qū)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達(dá)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區(qū)分布只有48.5%、44.8%,地區(qū)差異明顯。此外,城鎮(zhèn)化不應(yīng)只看農(nóng)業(yè)人口的轉(zhuǎn)移,還應(yīng)考察城鎮(zhèn)基本公共服務(wù)、基礎(chǔ)設(shè)施、人口素質(zhì)是否能跟得上,有效的城鎮(zhèn)化方能對(duì)農(nóng)業(yè)收入彰顯正面效應(yīng)。
3 結(jié)論與討論
運(yùn)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建立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因素模型,根據(jù)1978~2013年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結(jié)果表明,財(cái)政農(nóng)業(yè)支出、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對(duì)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有著顯著的負(fù)影響,化肥施用量、農(nóng)作物播種面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價(jià)格指數(shù)以及時(shí)間參數(shù)對(duì)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