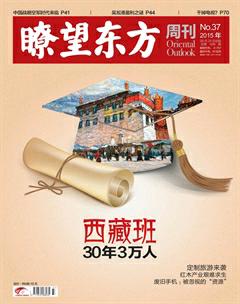維也納:美好之道
沈璐

維也納斯特凡廣場
100個人眼中有100個維也納。
游客沉醉于這座城市的古風,藝術家折服于這里的先鋒精神,居民在這里享受愜意的人居環境。
作為這個城市曾經的居民,霍夫堡或是茜茜公主早已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但我卻時常在街頭巷尾被一個小廣場、一個小花園或是一個小門面所感動。
美好的維也納之城,是如何煉成的呢?
歐洲文藝中心
由于地處東西歐的交界處,交流、沖突、融合是維也納城市史的關鍵詞。
具體來說,維也納首先是一個商貿城市,失去了自由流通、文化交流的功能,城市的活力和魅力也就喪失了;其次,它在歷史上還兼具首都和邊陲的雙重功能;同時,兼具防御和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在其發展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這在歐洲城市中極為少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維也納不僅是奧地利的政治中心,除了冷戰時期之外,還一直是歐洲的文化、藝術中心,這是地理區位賦予它的“地位”,也是其在歐洲政治格局演變過程中逐漸積累的“成就”。
這種跨越中西歐的特殊地域文化,使得維也納在世界城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基底的構建
公元10世紀,巴本堡王朝在羅馬守備軍駐地的基礎上建造了城墻,開始了維也納的建城史,在如今的皇宮和步行街一帶形成了城市的雛形。由于地勢的關系,維也納的水系從西北部的維也納森林流向多瑙河,水路呈現扇形。根據這個地貌特征,城市道路格局也大體呈現這個自然形狀。
同時,依據羅馬建城的傳統,城市的幾何中心形成了十字形中軸線,其中的主要商業道路垂直于多瑙河,便于貨物的運送。街道也基本保持垂直相交的網格形態,呈圓環放射狀。直到今天,這依然是維也納城市結構的重要特征。
此外,外來人口居住在城外也是維也納的一個特殊傳統。就連從德國帕騷來的大主教也不例外,他下令建造的著名的史蒂芬大教堂就在當時的城郊。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后,維也納由于吸納戰俘的原因,人口增長迅速,巴本堡王朝用戰爭賠款進行了城市擴建,將城墻和護城河拓建在今天的內環路位置,城市中心十字形的中軸線也隨之向西南位移。為了抵御外敵,尤其是土耳其人的進攻,城墻和護城河數次加高擴建。
這里不得不提到被譽為“維也納的建造者”的魯道夫四世,他在1365年建立的維也納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魯道夫四世還改擴建維也納的斯蒂芬大教堂,并開始建造教堂廣場和塔樓,使之成為歐洲教堂的典范。
進入輝煌年代
18世紀后,維也納進入了輝煌的建設時代,為現代城市格局打下了堅實基礎。
隨著手工業的出現,維也納建立了第一批工廠,并鋪設了城市下水道和街道清潔系統,城市衛生條件得以大幅改善。
維也納也是歐洲最早引入住宅標號制度和國家郵政系統的城市。
此外,被稱為“奧地利國母”的瑪利亞·特雷西亞及其后的皇帝約瑟夫一世為了順應時代的需求,還對帝國作了一些變革,引入城市公務員制度,大大推動了教育和科學的發展。
與此同時,維也納對主要商業街進行了重建,繼續展現巴洛克藝術風格,保存至今。貴族們也紛紛在城外建造花園和宮殿,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貝爾佛第宮和美泉宮,為了保護這些私有財產,貴族們還建造了“外環線”。
社會繁榮和科技進步帶來了文化藝術大繁榮時期,幾乎沒有一座歐洲城市像維亞納這樣熱衷于文化生活。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幾個世紀以來既無政治野心,也無軍事行動,為其贏得了和平的繁榮昌盛,使其可以專心追求藝術的卓越。可以看到,博物館、歌劇院、圖書館等公共設施都被安排在城市和社區最重要的區位。
城市骨架的最終形成
19世紀中葉,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維也納的城市化進程也駛入了快車道——周邊34個鄉村劃入維也納的行政范圍內,城市人口大幅上升。
為了擴大城市規模,維也納拆除了城墻、護城河以及軍事工事,在城市中形成了第三條城市環路,基本奠定了現代維也納的輪廓。
3條環路中,以包圍老城的環線路最為著名。其改建歷時20多年,于1888年完工。環線路的總里程6.5公里,路寬75米,由雙向四車道和兩行林蔭道組成。由于當時建設的規格等級高,“偶然”并“帶有預見性地”為后來的小汽車和有軌電車預留了道路空間,實屬難得。
環線路上至今還常見馬車往來,當然其功能早已變成觀光旅游。但馬車先行,車馬混行的特殊交通規則也成了維也納的一道風景。
環線路周邊建筑以新古典主義為主要特征,如國家歌劇院、國會大樓、自然和文化史博物館、城堡劇場、伏地福教堂,以及以金色大廳而聞名世界的音樂之友協會大樓等。還有一些維也納分離派建筑,最典型的當屬分離派博物館。這些建筑完好地保留至今,當時的先鋒作品成為傳世之作,被后人稱為“環路風格”。
除了建筑之外,環線還串聯了城堡公園、人民公園、市政廳公園和城市公園等公共開敞空間,大大改善了城市環境。
推行積極的公屋政策
隨著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解體,奧地利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進入左翼溫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時期,提倡“慢速革命”,認為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在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逐步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廈。
比如,“紅色維也納”推行積極的“公屋政策”,著名的“卡爾·馬克思大院”就是那一時期公屋建筑的代表作。
延續溫和、慢速的施政風格,“馬克思大院”并未打破歷史形成的布爾喬亞城市形態,而是讓新型的公共空間與傳統的私有空間互相滲透、重疊,使封閉式的、暮氣沉沉的城市空間逐漸開放,生長出一種適應基層勞動階層生活的居住空間,構建生趣盎然的社區環境。
按照“紅色維也納”制定的公屋條例,其每戶住房面積為38~48平方米;每戶有自己的廁所和廚房,包括煤氣爐和自來水龍頭;所有的房間(包括廚房和廁所)有充足的天然光線和自然通風。這些在今天看來最普通和最基本的設施和條件,在上世紀30年代卻是了不起的進步。如今,“80歲”的馬克思大院仍在繼續為居民服務。
重新成為歐洲中心城市
二戰期間和二戰后的維也納城市建設鮮有可圈可點之處,這與冷戰形成的維也納邊緣化以及東西歐之間文化經濟交流不暢有著很大的關系。
上世紀80年代冷戰鐵幕落下之際,維也納市政廳提出了“不同的維也納”的口號,就是為了讓這個古老的、為歷史所困的城市重新煥發新生,向外界傳達一種現代的、積極向上的信息。
年輕的建筑師們、藝術家們以及一些政府官員開始對年代久遠的老城進行修復,內城更新成為當時重要的城市政策之一。
冷戰后,維也納一直處于歐洲邊緣。但40多年過去后,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維也納重新變成歐洲中心城市,并成為“漢堡——布達佩斯”和“里昂——布拉迪斯拉瓦”兩條發展軸的交點,扭轉了戰后數十年城市發展的劣勢。
維也納由此成為歐洲大型開發商的寵兒,短期內開工或完成了諸多大型項目,如多瑙城、千禧大廈、煤氣罐之城、中心火車站等。但以大型、超高、物業混合為特征的地產開發一度受到維也納人的質疑,因為這與維也納的傳統和生活習慣顯得格格不入。
然而,正如一切舶來的文化和藝術一樣,它們傳入維也納的過程,也是接受維也納式改造的過程,維也納人正把全球化、國際化、冷冰冰的建筑周邊空間,改造成親近人、溫暖的廣場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