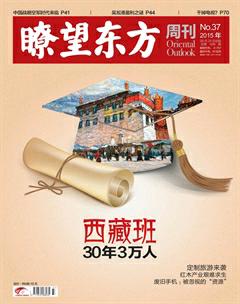馬術俱樂部的小眾式生存
王元元

華天騎著“堂·熱內盧”參加羅金厄姆城堡國際賽( 夏原浦/ 攝)
這是一棟美式裝修的高頂建筑,大廳里擺放著有些年份的鋼琴和黑白照片。剛剛馴馬歸來的王冀豫坐在長桌前,透過落地窗靜靜地看著圍場里成群結隊的馬兒,嘴角不時上揚。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度過的。
64歲,身材依然健碩的王冀豫人稱“黑子”,是國內馬術圈的名人。他身后的這塊占地百畝、坐落在西北六環外的稻香湖馬術俱樂部也是中國第一家馬術俱樂部。在它成立30年后的今天,國內馬術俱樂部數量已經從個位數增加到了三位數。
“這是好事也是壞事。”混跡馬術圈30年的黑子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但對于馬術運動尚處萌芽階段的中國來說,后者的意味可能大于前者。
不是為錢而建
曾為內蒙古知青的黑子在壩上草原見過成群結隊的駿馬奔馳,這樣的場景讓他興奮不已,對于馬的喜愛也深入心底。回京后,他曾四處尋覓能夠騎馬的地方,但始終未能如愿。
1985年5月,一群和黑子一樣的愛馬之人在北京郊區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廣義上的馬術俱樂部——稻香湖鄉村馬術俱樂部(以下簡稱稻香湖)。
當時,現代馬術概念尚在官方理解層面,民間幾乎無人知曉這一運動。稻香湖的成立也并非受馬術運動影響,純粹是一群愛馬之人的自發舉動。
黑子說,稻香湖最初推廣的“馬術”也并不是現代馬術,而是中國的傳統馬術,“說白了就是教人怎么騎馬。”初時的稻香湖更像是一個馬場,而非馬術俱樂部。
不過,稻香湖的意義在于將以往散玩性質的馬術帶到了專業層面,通過俱樂部的形式將這一運動正規化。“以前玩馬都想著去內蒙古草原,而稻香湖則提供了一個場地,不用去草原也能隨時騎馬。”黑子說。
上世紀80年代的稻香湖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的愛馬、懂馬之人。這些人將現代馬術運動逐漸引入民間,成為此后馬術運動在民間興起的關鍵推動力量。
在稻香湖成立4年后的1989年,曾為中國馬術運動立下汗馬功勞的石景山馬術俱樂部成立,創始人正是稻香湖的員工巴納以及曾經叱詫搖滾樂壇的黑豹樂隊主唱欒樹。
和稻香湖不同,石景山俱樂部在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現代馬術。在那個馬術還是一項極其冷僻的運動的年代,幾個執著的年輕人用推土機在山上建起了馬房和宿舍,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傳播現代馬術運動的俱樂部。
輝煌時,石景山俱樂部曾組建一支非專業馬術俱樂部代表北京隊贏得1997年的第八屆全運會馬術團體冠軍,名噪一時。即便如此,它也未能擺脫倒閉的厄運。在贏得全運會冠軍的兩年后,石景山俱樂部終因財力不支而歸于沉寂。
“創立石景山俱樂部的那批人不是沖著錢去的,純粹是喜愛馬術,想把這項運動做起來。”黑子說,正是這種單純的想法讓它在創立之初就沒有考慮商業化,失去了長久發展的支撐,“但它對整個行業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北京市第一個跑馬場——稻香湖跑馬場,1985年5月5日正式接待游人
當初從石景山俱樂部出來的那批人,如今都成了中國馬術圈的名人。比如天星調良國際馬術俱樂部的主力人員王薔、史琪、袁茂升、張可等;燕龍馬術俱樂部的創始人沈青洲;亞薩園馬術俱樂部的創始人任亞克。
在圈里人眼中,石景山就是中國馬術俱樂部的“根據地”。由此發端,馬術運動開始為越來越多人所了解和喜愛,馬術俱樂部也開始在北京乃至全國破土而立。
裂變效應
石景山俱樂部倒閉后,曾帶來一股馬術俱樂部的建設潮。
“很多原本在石景山玩馬術的人突然沒了去處,只能另想辦法。”北京市馬術運動協會(以下簡稱北京馬協)秘書長陳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批中國最早玩馬術的人追求的是單純的馬術體驗,也不差錢,索性自己建起了馬術俱樂部。
1999年成立的天星調良國際馬術俱樂部(以下簡稱天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董事總經理王薔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很多會員都在石景山俱樂部倒閉后成立了自己的馬術俱樂部,同一時期成立的馬術俱樂部差不多有十幾家。這一數量相當于此前15年國內馬術俱樂部的總和。
陳徹將這一增長稱為裂變式,“由一家種子俱樂部裂變成多家俱樂部,原來的馬主變成新俱樂部的所有人,原來的馬工變成了俱樂部的經理或者教練。”
這批在上世紀末興起的馬術俱樂部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仍像石景山俱樂部那樣依靠興趣而建,另一類則開始嘗試商業化運作。
“相同點是都開始朝更專業的方向發展,不同點是因模式不同而遭遇的境遇也大不相同。” 在某馬術俱樂部擔任多年教練的張國棟(化名)告訴本刊記者,前者往往因無休止的巨額投入而面臨倒閉窘境,后者則依靠商業化運作而漸生活力。
他說,一個小有成就的老板曾因愛馬而建立了一個頗具規模的馬術俱樂部,僅每年買馬和養馬的費用就達上百萬元,最終因財力無法支撐而關閉了馬術俱樂部,老板也落了個破產的下場,“這樣的例子在馬術圈很多。”
正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對于那些真正熱愛馬術的人來說,馬術俱樂部所需要的投入遠大于他們的想象。而像天星這樣起初就走商業化路線的俱樂部,如今的日子則要好過得多。
近十多年間,中國的馬術俱樂部數量開始以成倍速度增加,尤其是2008年以后馬術俱樂部發展更為迅速。“北京奧運會之后馬術運動在普通民眾中興起,很多人趁勢進入這個新興市場。”曾為北京奧運會馬術運動項目主管的王薔說。
根據北京馬協的統計,目前全國有500多家馬術俱樂部,其中北京市注冊的馬術俱樂部就有198家,且這一數量還在以每年10家左右的速度增長。“僅2013年就有12家馬術俱樂部開張,有些俱樂部甚至只有幾個人、幾匹馬。”張國棟說。
這樣的增長速度在王薔看來有些不正常,“大家只看到每年新開許多俱樂部,卻忽視了同時也有一批俱樂部在倒閉。”
“太多人是奔著賺錢來的,而不是馬術。”她說,這跟那批對馬術運動抱有情懷的先行者截然相反,也勢必會擾亂市場,“在整個行業還未進入正規時,無序發展可能帶來致命打擊。”
賠本賺吆喝
正如張國棟所言,馬術俱樂部在看似繁榮的背后,其實潛藏著危機。
北京馬協的數據顯示,目前北京70%~80%的馬術俱樂部都處于虧損狀態,真正實現盈利的不足30%,全國也是相同的狀況。
為何會虧損?陳徹給出的答案是多數馬術俱樂部是私人性質的會所,不以盈利為目的。前述北京馬協的數據顯示,北京現有的198家馬術俱樂部中有近百家是私人俱樂部,占到總數的五成以上。
但更多人關注的是那些已經走向市場的馬術俱樂部為何也會面臨如此窘境。
“因為玩馬術的人很少,馬術運動仍然是一個小眾化的運動。”陳徹說,德國馬術運動關注者高達1000多萬,占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而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馬術運動關注者只有60萬,“真正花錢玩馬術的可能更少。”
“這根本養不活如此多的馬術俱樂部。”陳徹說,相比之下,一個馬術俱樂部初期的場館建設投資就達一兩千萬元,建成后還要負擔馬匹飼養和員工工資等固定支出,“如果沒有穩定的客流,根本不可能維持日常開支。”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多數俱樂部的收入來源于學員教學和馬匹寄養。學員教學包括散客教學和會員教學,前者的收費平均每課時(45~60分鐘不等)在300~500元之間,后者的收費平均在每課時200~300元之間。
當然,每家俱樂部因為條件不同,價格也相差較大。比如萬芳亭騎士俱樂部對散客的收費是每小時150元,包括裝備和教練費,且不限時;而天星則是每50分鐘900元至1000元,且不包含教練費,兩者相差5倍左右。
寄養馬匹的收費則相對較高。以天星為例,其對寄養馬匹的收費包含幾大項,其中飼養費用每月6000元,調教費每月2600~3600元,鞍具保養費每月200元,釘掌費每次500元,合計每月至少需要10000元,一年需12萬元以上。
大部分俱樂部還是主要依靠會員收費,馬匹寄養占很少一部分,即使天星也不例外。天星目前擁有5000多個會員,這在國內屈指可數,多數規模較小的馬術俱樂部會員只有幾百人。
“因為提前交付的會費能夠支撐俱樂部的日常運作,如果僅僅依靠散客,估計三分之二的俱樂部要倒閉。”張國棟說,稻香湖能夠長盛不衰的“秘訣”也正在此。
稻香湖在運營過程中也曾面臨巨大的收支壓力,一度入不敷出,但在會員的救濟下得以繼續維持。

天星調良國際馬術俱樂部的馴馬師正在訓練
如今的稻香湖是一個由30多個既是會員又是股東的人組成的合資俱樂部,所有的運營資金都是會員籌集,“連俱樂部里面的桌椅擺設都是會員無償捐獻。”黑子說,稻香湖每年的收入在100萬元左右,“這些費用僅夠俱樂部一年支出,不會有盈余。”
不過,對于依靠會員生存的俱樂部來說,最大的問題在于客流分配的不均。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周一到周五馬術俱樂部多處于歇業狀態,人流極少,甚至空無一人;而周六周日的客流量有時則能超過場館負荷。
“所以馬術俱樂部只能依靠周末兩天的收入來支撐一周的支出。”張國棟說,這往往給俱樂部帶來更大的虧損漏洞,“因為馬匹數量有限,即使周末客人再多也無法滿足需求,也不能賺錢。”
兩極分化嚴重
“市場就這么小,馬術俱樂部的數量已經遠遠超出需求。”張國棟說,競爭不可避免。
越來越多的新生俱樂部開始熱衷打價格戰,希望通過低價吸引更多的愛好者。
如前所述,兩家不同的馬術俱樂部,散客教學收費價格能相差5倍。北京某馬術俱樂部的課時收費已經從剛成立時的300元左右降到150元左右,這一價格甚至低于一堂鋼琴課的收費。
即使是會員收費,不同的馬術俱樂部價格也相差甚遠。天星對會員的收費是不包含教練費每課時430元左右,而另一家坐落在北京南城的西部動力馬術俱樂部(以下簡稱“西部動力”)價格則在200元左右,兩者相差1倍。
“按照正常的成本核算,過低的價格不可能賺錢。”王薔說,一些俱樂部為了賺錢,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不惜通過專業營銷公司來忽悠客戶,“很多客戶交了一年的會費,結果去了才發現俱樂部根本就不能玩馬術。”
在某馬術俱樂部擔任高管的汪華(化名)向本刊記者直言,很多俱樂部甚至不具備開展馬術教學的相關條件,就是圈了一片地、養了幾匹馬而已,“但國內消費者對于馬術了解不多,根本無從分辨,往往只能被動接受。”
其中,馬的貓膩最大。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國內馬術俱樂部使用的馬匹過半以上都是改良馬,即進口馬與國產馬的雜交品種。這種馬在價格上遠低于進口馬,而性能上又遠優于國產馬,因高性價比而備受馬術俱樂部青睞。
西部動力董事長鐵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一匹進口馬僅檢疫、空運、關稅費用就需要10萬元,再加上馬本身的價格多在30萬~100萬元左右,而改良馬價格則多在15萬元左右,甚至幾萬元就能買到。其俱樂部24匹馬中,改良馬占到六成以上,進口馬不到5匹,價格最貴的僅30萬元。
一些小型的馬術俱樂部甚至用便宜的國產馬替代進口馬,而國產馬因體型問題并不能用于現代馬術運動。“這等于喪失了馬術運動的基礎。”汪華說,很多馬術俱樂部為了多接客人,把馬原本正常的每天三四節教學課增加到八九節,使其處于超負荷運動狀態,“完全違背了馬術精神和馬匹福利原則。”
“這樣的現象很普遍。”張國棟說,他所帶的5匹馬每天至少接待6撥客人,教學時間至少7個課時,“人都沒時間休息,更何況馬呢。”
本刊記者走訪了多家馬術俱樂部,“馬匹福利”一說遭到不少負責人的嘲笑。
這還僅僅是硬件問題,軟件更不理想。
以教練為例,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多數馬術俱樂部的教練是從喂養馬匹的馬工轉型而來或者是從內蒙古、新疆等地請來的放馬人,既沒經過專業的馬術培訓,也無專業機構的認證。即使是像天星這樣的高檔俱樂部,經過英國馬術機構認證的教練也僅有十多人,最高級別的為中級教練。
更多的教練還身兼多職。以西部動力為例,其目前僅有的5名教練除負有教學任務外,還肩負照顧馬匹的馬工任務,而在國外這兩個工種是嚴格區分的。
“這些教練都是俱樂部自封的,就是無證上崗。”在汪華看來,原本應在馬術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教練,如今卻成了最薄弱的一環,“這樣的教練訓練出來的馬是不合格的,教出來的馬術更是不合格的,純屬自斷后路。”
如今,馬術俱樂部開始朝著兩極分化的趨勢演進,“好的越來越專業、差的越來越落伍。”張國棟說,這樣的分化是整個行業的拐點,“大浪淘沙的過程是留下最適應市場需要的一部分俱樂部。”
這對于中國的馬術運動而言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