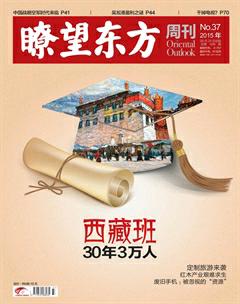馬背上的音樂人
馬莉

欒樹
欒樹工作室的墻上,貼著很多他和朋友們的合影。照片中有他在音樂圈和馬術圈的朋友,有來自他們的祝福,還有他心愛的馬。
大多數人知道欒樹是因為他曾是黑豹樂隊的主唱,或是他制作人的身份。他參與制作了許巍、田震、羅綺、唐朝樂隊等很多歌手的專輯,以及《非誠勿擾2》《私人訂制》等電影的主題曲和電影配樂。
但欒樹還有不為人所熟悉的另一面——在馬術圈,他和石景山俱樂部,是中國馬術早期發展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他們開創了中國私營俱樂部參加全運會的先河,為中國騎手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尋找著可能。
一人一馬石景山
“它就是一匹憨厚勇敢的小母馬。”談起他現在的這匹叫做快樂武士的馬,欒樹充滿溫情。
這匹來自丹麥的溫血馬,在2010年來到中國,開始陪伴欒樹,“它1歲多來的時候,比較虛弱,大家不是很看好它,感覺它碰碰就能倒。”
但之后,快樂武士越來越健康,在哈達鐵教練的訓練下,2013~2015年間,它一直活躍在馬術賽場上,從中國馬術場地障礙巡回賽到浪琴表中國馬術巡回賽。在多場比賽中,它和騎手欒樹、哈達鐵或王允允密切配合,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這匹幾乎完全在中國調教訓練的馬,也展示著中國馬術訓練水平的提升。
快樂武士是欒樹的第三匹馬,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一名騎手在一生當中能夠遇到讓自己記憶深刻、和自己脾氣相投,讓自己覺得天衣無縫,騎乘舒服,互補性又特別強的馬的機會并不多,可能也就一兩匹。”
這幾乎是大部分騎手的共識:好馬難求,但最難的,是遇到適合自己的那一匹。每個人的騎乘習慣,都深刻影響著馬,一人一馬需要長久的磨合。
欒樹從1989年開始接觸馬術。還是小男孩的時候,跟許多看多了《佐羅》這類英雄片的孩子一樣,他也迷上了電影里騎著馬的英雄們。但那時候對騎士,他更多是羨慕和崇拜,“老想接觸馬,但沒有機會”。
直到認識哈達鐵和他的妻子,欒樹才開始接觸馬術。哈達鐵和妻子劉燕是內地最早的一批騎手,那時內地剛剛開始組建現代五項國家隊,練習其他項目的二人被選入國家隊。
也正是1989年,石景山鄉村馬術俱樂部成立,后來的很多馬主都出自這里。組建了俱樂部的欒樹,開始和巴納等人一道,買馬、養馬、不斷學習馬匹知識,直到組隊去參加比賽。
在這里,他遇到了他的第一匹馬——弓箭。這匹一歲多就從東北運來的奧爾洛夫馬,陪伴了他好幾年。1995年,弓箭因病被安樂死,這點也一直讓欒樹很難過。
石景山俱樂部和成立于1985年中國第一家私人性質的馬術俱樂部北京稻香湖馬術俱樂部一樣,開始時相對簡陋,但還是盡量建立起相對專業的馬房、場地和會所。
欒樹也開始不斷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國外馬術的資料、錄像帶、馬具等。他從最基礎的騎術要領、飼養知識和釘掌學起,“那時候我在石景山的家有一個關于馬術的資料館,每天晚上在我家,騎馬的朋友都會去我那兒翻資料、看錄像。”
跟早期大多數馬術俱樂部的創始人一樣,巴納和欒樹等人創建石景山俱樂部也是因為興趣,對市場并沒有太多的預計和期待。“我是完全不懂經營的人,就是喜歡馬。我當時最大的工作就是買馬、訓練,去不斷結識教練和騎馬的朋友,再做一些小型的比賽。”
從私人俱樂部到全運會
1994年,黑豹樂隊在樂壇如日中天時,欒樹卻選擇離開樂隊專心學習馬術。當時樂隊也常常會在馬場排練,但為了更好地備戰,加上比賽都在周末,“那時候會有人開玩笑說我是‘玩物喪志’,而且時間上對樂隊確實有影響,我就選擇離開了樂隊。”
為了備戰比賽,他們的訓練相當艱苦,每天要練好幾個小時。好在從俱樂部到訓練,一切都在慢慢步上正軌。
但這個過程是艱辛的,體系建設從無到有,而資金、教練、馬工、獸醫等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去解決。在這個階段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其他人對馬的不尊重。
馬需要釘掌,當時釘掌都要去農村,先給馬綁起來上樁,防止它亂踢。“他們意識里還是把馬當做牲口,想上樁快點釘完了事,馬折騰的時候,不論手里拿的是什么,還會順手打一下馬。”最后一次去那里釘掌的欒樹最終還是發了很大的脾氣,從此再也不去那個地方。
回來后,他和團隊決定不再上樁,而是用更加溫和的方式讓馬適應釘掌的過程。他們慢慢摸馬,抬起馬蹄慢慢敲打,讓馬對錘子反應不會太激烈。整個馬場的馬,用了一年多時間,才用這種方式讓馬適應釘掌。
那時,石景山的每一匹馬都在資料庫中,記錄著這些馬的年齡、名字等信息。盡管不斷進出,但占地20畝的石景山,馬的保有量當時在40匹左右。
錦標賽奪冠后,石景山俱樂部希望騎手和馬能有更大的賽場,而北京市體育局在關注到他們優異成績的同時,也希望這個偏向冷門的項目,能有更多人參加。

欒樹參加其作為發起人之一創辦的西塢國際馬術場地障礙大獎賽
于是,在1997年全運會的時候,石景山俱樂部有機會代表北京隊出戰。“那時候覺得很興奮,就不顧一切去沖擊,去推介這個項目,每天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馬上。”現在談起這件事,欒樹還會興奮。
最終,由哈達鐵、欒樹、張可,秦光芒4人組成的北京馬術隊,在澳大利亞國家隊教練喬治·桑娜的指導下,獲得障礙團體冠軍。這是當年最出人意料的比賽結果。
這段時期,陪伴他的是他的第二匹馬——凱旋。
1997年全運會后,各路“洋教練”、獸醫、馬術的推廣陸續進入中國。而石景山能夠在1997年順利參賽,“社會上很多人,包括韓小京、黃祖平等這些朋友給了巨大的支持,讓我們可以順利地把馬運回來,順利地打比賽,還有家里對我的支持,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很艱苦了。”
石景山代表北京隊參賽,開了私人俱樂部參加全運會的先河,從這時候起,地方政府和民間馬術俱樂部開始合作。直到現在,在全運會上,大多數馬術隊伍都采用這種模式。
這段時期內,欒樹并沒有徹底離開音樂圈,業余時間,還是和音樂人在一起。那時候,紅星音樂生產社就在石景山,離欒樹的馬術俱樂部并不遠。欒樹也在這段時期,參與了許巍《在別處》專輯的制作。
而發掘了Beyond等人的紅星音樂生產社的陳健添,不僅是黑豹樂隊在國外的經紀人,也是石景山俱樂部的投資人之一。“那時候,許巍、田震、鄭鈞,我哥哥老欒他們,都在紅星,在馬場,很有意思。”
那段時間對欒樹來說,無疑是珍貴的。
重回馬場
盡管1997年獲得了全運會的冠軍,欒樹和石景山俱樂部也被大量曝光,他接受了很多采訪,“但在經濟上,冠軍的獎金不足投入的五分之一”,這對于需要私人買馬、養馬、訓練、支付比賽所有費用的欒樹來說,愈發艱難。
“那時候所有的積蓄都用完了,”在賽前,他的父親欒心愉因肝癌離世。“就3個月,很急,突然離世。開完追悼會我就去了上海打全運會。”
父親的治療、離世和全運會的準備、比賽,加上經濟上的艱難,給了他很大的沖擊。但他依然獲得了團體冠軍。“老天給了一個回報。”他說。
1997年全運會后,欒樹去了歐洲,希望在那里能獲得更多進步的他,深深感受到的現實卻是“除非我放棄一切,給別人打工,但這樣我都不一定有騎上馬的機會。”
不過,這次游歷開闊了他的眼界,讓他接觸到了世界上頂級的教練、騎手和馬場。
“每年巴黎圣誕節都會有一個馬的大型展覽,1998年是我第一次到那個展會現場,看到6~8個足球場那么大的大棚在展覽馬。”
從馬的飼料、壓縮蔬菜、房車,再到看1.60米的障礙賽,歐洲的和世界頂級的標準震撼和沖擊著他。
2005年,重回中國馬術圈的欒樹,心境和經歷都和1997年時不再一樣。他能夠感覺到這項運動越來越難。障礙的高度在不斷提升,而國內騎手也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連續多場0分(不罰分)。
而另一方面,他也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音樂制作上。他一直強調說自己現在訓練的時間太少,“教練也沒辦法,說我參加比賽能下來就挺好。”
“馬是有生命、思想和各種情感的高級動物。”欒樹告訴本刊記者,他并沒想到,這一輩子,他會跟馬結下這么深的感情。